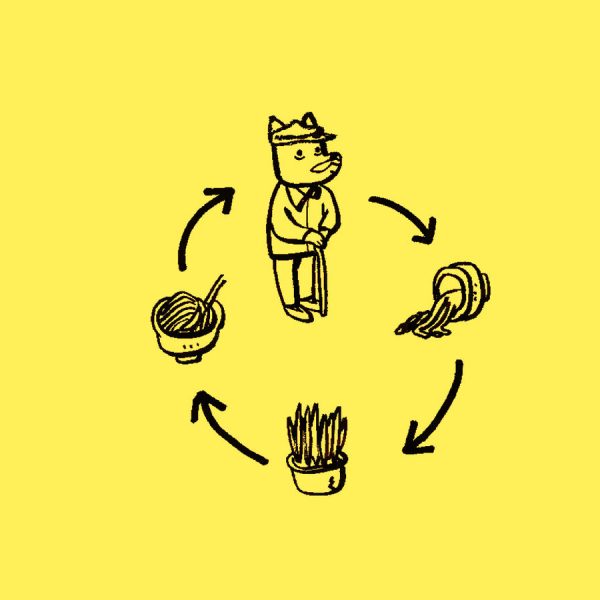垃圾分类只让你觉得麻烦,却砸了他们的饭碗
小李是个90后,住在我们小区的10号楼。如果不是因为垃圾分类,我可能不会知道10号楼其实是个垃圾房,也不会认识他。
因为吃饭晚,我总是赶不上定时定点的垃圾桶,只能提着垃圾到垃圾站来扔。最初这里的垃圾桶还是全天候开放的,但由于附近两栋楼的住户投诉臭味和蚊虫,这里的桶后来也只能摆放到夜间10点 —— 沾上跟垃圾有关系的事,“邻避效应” (Not In My Back Yard) 总是特别明显。
生在安徽,小李和他的妻子一起来上海讨生活。去年11月,他俩开始做我们小区的垃圾清运工,但他更喜欢称呼自己是小区垃圾的 “个体承包商”。他和物业之间的约定是,只要负责整个小区的垃圾清运,他就可以 “承包” 垃圾中所有的可回收废品,卖掉所得的钱都是收入。小两口就住在垃圾房楼上,无需支付租金,只要承担水电费用。挑高的一楼放置着三台用处不同的垃圾处理机,在楼下垃圾房的一角,摆放着一张别人丢弃的黑色沙发,那是小李和他妻子闲暇时刻用手机煲剧打游戏的地方,因为他俩 “要是没洗过澡就不上楼回家”。
带小李入行的是他的老丈人,眼下正承包着隔壁小区2000户人家的垃圾与废品,而我们小区有1000多户人家,分布在30栋楼中。在以前,每栋楼门口都放有两个敞口的240升标准垃圾桶,居民把各种生活垃圾混着一股脑地往里丢。只消半天时间,两个桶就会被塞得满满当当。小李就每天骑着他那辆经过改装的电动三轮车绕着小区转,将满溢的垃圾桶拖去垃圾房清空、洗净再放回。

小李把垃圾车从站里骑出来
全年无休、不分寒暑、臭气熏人,他这承包商赚的都是辛苦钱。在他看来,垃圾分类并不是啥新鲜事,之前并不是不分,只是不由居民分,“那些废品都是我的收入啊,分得可清楚了。把垃圾都收回来之后,我们都会再分拣,就算是以前,干的湿的也都要分开,才给政府的车拉走。”
理所当然地,小李认为小区范围里的废品应该全部归他,然而,同样靠变卖废品维生的拾荒者、收卖佬,也惦记着垃圾桶里的货;不仅如此,住在小区里的退休老人,也会来分一杯羹。
前垃圾分类时代
每当说起这个话题,小李就会流露出四面楚歌、强敌环伺的警惕,“我承包了,他们凭什么跟我抢?”
“14号楼住着个阿姨,我知道她就是捡垃圾的,见到好几次了。有一次当着我面要捡走一个纸板箱,我问她要,她非说是她自己的,现在不想扔了。真要是你的东西就算了对吧,但小区里所有的废品都是我的工资啊,不然你自己来清理垃圾?” 我问小李后来怎么处理,他说只能让那位阿姨捡走了,“又不能打又不能骂,之前也有人抢了一下就把自己关进去了,这我可承担不起啊!”
小李说的,是 “一个饮料瓶引起的血案”。去年10月,在上海闵行某小区内,一位80岁的老太在垃圾桶内捡走了一个饮料瓶,正巧被该小区的保洁员高某撞见,他出手抢回饮料瓶,在争执间推倒老太造成其左手骨折。作为小区的清洁工,高某认为小区所有的垃圾理应由他处理,觉得老人是来到自己的地盘抢废品,但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他提起公诉的检察官可不这么想:“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小区并没有相关的规定”。
公诉人的说法耐人寻味,关于垃圾桶主权及桶内垃圾所有权的争议,没有 “自古以来” 也没有 “神圣不可侵犯”,只能被 “没有相关规定” 一笔带过。
法律鞭长莫及之处,总会长出草根秩序。不能和小区里这些捡点破烂、赚点小钱的老人们正面交锋,小李就发动同情自己的居民做 “眼线”,见到哪里有扔出来的纸板箱就通知他去捡,“不过有时候我赶过去就已经不见了。”

小李的老丈人接手将垃圾车骑出去,小李拖着桶走回垃圾楼
防不胜防,小李只能优先搞定小区外的拾荒者。想不到来小区不久,物业就换走了整批门卫。小李赶紧为他的 “天时” 和 “地利” 补上了 “人和”,“和那帮新来的兄弟打好了关系”,让他们帮着把小区外的拾荒者,拦在了大门之外。
但对街的收卖佬,可没有拾荒者那么易挡,“小区居民打电话叫那人上门来收垃圾,总不能不让人进来吧。” 陷入守势的小李,在每栋居民楼、每个垃圾投放点都贴上了自己的电话,“现在慢慢多点人知道叫我了,有些居民送给我,有些卖给我,虽然要花点钱,但总比没有废品强”。
这位收卖佬姓周,生意就在人行道上张罗,一人、一车、一秤。平时他在废品堆起的小山边上支起一张躺椅,懒洋洋地躺在里头睡觉或者玩手机,夏日的骄阳再毒辣,他也只是往树荫挪挪,从未翘班。我曾问周叔能不能上门收废品,他二话不说递上名片,说你多攒点,打电话叫我去收。我再问他,垃圾分类之后生意怎么样,他摆摆手说,差不多,差不多。
后垃圾分类时代
周叔的话不知真假,但小区里的战局,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往,小区这一千户人家丢出来的废品,每个月都可以给小李两口子带来大约9000元的收入。但自从小区于6月头提前开始施行垃圾分类,他们6月整月的收入就下滑到了6000元。这倒不是因为大家为了避免分类的麻烦,而主动压抑物欲、源头减废,按小李的说法,大家只是减少了废品的丢弃,“现在丢垃圾不仅分类还定时定点,大家就不愿意扔那些大纸板箱了,以前直接放楼下多方便。”
“而且,那些捡废品的大叔和阿姨,原来还要在垃圾桶里翻找,现在扔出来的垃圾已经分得清楚清楚,他们就更方便拿走”,小李还不忘怨怼一下他的竞争者,但事实上,看守定时定点垃圾桶的志愿者郑叔,是小李坚定的队友。郑叔是19号楼的住户,年逾花甲,已经退休,他每天都要到岗4小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大家把湿垃圾“破袋”,“一个月下来嗓子都哑了”。
郑叔不是没遇到过想顺手牵纸板的人,但都当场制止了。深谋远虑如他,深知没了小李不行,“现在如果垃圾分类没分清楚,政府的垃圾车就不把垃圾拉走,小李那里是保证分类最后一关。怎么能让人抢他的废品,他又没有工资,要是不干了小区怎么办?” 这时正是台风过境的次日,政府的垃圾车因此四天没来,一个个硕大的黑色垃圾袋已在垃圾房前堆成了山。
此话不假,小李曾跟我透露过,“如果收入一直这样少,可能就不干这行了。” 说话时,已近晚上9点,月色下的两口子还在忙碌着把塑料的瓶瓶罐罐装进巨型麻袋,麻利地装车,准备将它们卖到回收站去。
以前小区对面就有个回收站,但为了保护旁边的一棵老银杏和400年古迹,回收站被拆了。现在,小李要骑到两公里外的回收站去卖废品,但他只敢在夜色中出发,“因为我这三轮车改装过,没改装过三轮车也不让上牌照,4月份社区民警就跟我说,以后只能小区里面骑,出去警察抓到就罚100。有一次我趁晚上出去,还遇到突击查酒驾的,算自己倒霉,一车(瓶子)白卖。”

李的老丈人把回收点的垃圾倒垃圾车上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罚款和宣传双管齐下,作为前端的垃圾生产者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分类的责任。按上海市政府在7月31日发布的垃圾分类首月报告,“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上月增加了15%,比去年年底增加了82%,可回收物比上月增加了10%,干垃圾则下降了11.7%”,这意味着,原本混入干垃圾里的湿垃圾和可回收物,现在被更好地分拣出来了。而对处在中端的垃圾承包商小李而言,不论是清运还是分拣的活都确实地少了。人是轻松了,但收入也少了,这让小李一直意难平。
后来,小李和郑叔都提到了一笔 “一千多元” 的津贴,说是对他们在投放点监督垃圾分类而给与的补助。所谓 “一千多元” 并非一个概数,而是居委会一直没有明确告诉小李那笔补贴到底会是一千多少。直到垃圾分类施行满月,也就是7月31日这笔钱真的下发的时候,谜底才被揭晓:1800元。
新的竞争
虽然补贴暂时还补不上废品减少造成的3000元缺口,但多少让小李不再那么悲观。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以及做好风险管理,他不再在月黑风高之夜骑车去卖废品,而是把自己这边的废品都并入隔壁老丈人承包的小区,“那边居民多垃圾多,要4个人才能忙得过来。我把垃圾送过去之后,量大,就可以叫回收站派车进小区来收。”
最近,他又砸重金添置了一台压缩机,也是为了提高运输效率。但几乎同时,一台资源回收机突然空降到了小区里,还正好在通往垃圾房的必经之路上。这台 “互联网 + 回收” 的产物,打着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 的名义,扫码、开仓、投物、称重、积分,居民左手投入可回收的废品,右手的手机上就会立即获取可供提现的积分。回收机上还配备摄像头,投入杂物会被拉入黑名单。

小区的垃圾分类回收机,白天有人指点居民操作
这无疑又重创了小李,“这台机器装了一个礼拜,我的收入又少了三分之一!” 之前还是同维竞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对小李而言,则是无法抵抗的冲击,至少在各家科技公司努力占据垃圾风口的短期内。一周之后,小区另一个角落又增设了一台机器,小李远远看着。“饭都没得吃了,我就不做这份工作了”,仿佛为了明志,他又跟我提了一次他的去意。
体力劳动者,手停口停,而现在小李的双手为了分拣干湿垃圾忙个不停,供他去换取粮食的可回收废品却已锐减。而我除了把在X猫购物节剁手时拆出来的纸板箱、整个夏天喝饮料留下的空瓶、以及家中各种看起来有可回收价值的物事,都整理干净交到他手上之外,也不知道还能帮他些什么。
垃圾的物权仍不明晰,而垃圾的市场化已是常态。当垃圾回收从业者无法保障本就微薄的利润,曾经的废品回收链条必然崩塌。旧的平衡已被打破,而新的均势未必能顺利建起,但愿垃圾因无人清运而淹没小区的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临。
小李是个90后,住在我们小区的10号楼。如果不是因为垃圾分类,我可能不会知道10号楼其实是个垃圾房,也不会认识他。
因为吃饭晚,我总是赶不上定时定点的垃圾桶,只能提着垃圾到垃圾站来扔。最初这里的垃圾桶还是全天候开放的,但由于附近两栋楼的住户投诉臭味和蚊虫,这里的桶后来也只能摆放到夜间10点 —— 沾上跟垃圾有关系的事,“邻避效应” (Not In My Back Yard) 总是特别明显。
生在安徽,小李和他的妻子一起来上海讨生活。去年11月,他俩开始做我们小区的垃圾清运工,但他更喜欢称呼自己是小区垃圾的 “个体承包商”。他和物业之间的约定是,只要负责整个小区的垃圾清运,他就可以 “承包” 垃圾中所有的可回收废品,卖掉所得的钱都是收入。小两口就住在垃圾房楼上,无需支付租金,只要承担水电费用。挑高的一楼放置着三台用处不同的垃圾处理机,在楼下垃圾房的一角,摆放着一张别人丢弃的黑色沙发,那是小李和他妻子闲暇时刻用手机煲剧打游戏的地方,因为他俩 “要是没洗过澡就不上楼回家”。
带小李入行的是他的老丈人,眼下正承包着隔壁小区2000户人家的垃圾与废品,而我们小区有1000多户人家,分布在30栋楼中。在以前,每栋楼门口都放有两个敞口的240升标准垃圾桶,居民把各种生活垃圾混着一股脑地往里丢。只消半天时间,两个桶就会被塞得满满当当。小李就每天骑着他那辆经过改装的电动三轮车绕着小区转,将满溢的垃圾桶拖去垃圾房清空、洗净再放回。

小李把垃圾车从站里骑出来
全年无休、不分寒暑、臭气熏人,他这承包商赚的都是辛苦钱。在他看来,垃圾分类并不是啥新鲜事,之前并不是不分,只是不由居民分,“那些废品都是我的收入啊,分得可清楚了。把垃圾都收回来之后,我们都会再分拣,就算是以前,干的湿的也都要分开,才给政府的车拉走。”
理所当然地,小李认为小区范围里的废品应该全部归他,然而,同样靠变卖废品维生的拾荒者、收卖佬,也惦记着垃圾桶里的货;不仅如此,住在小区里的退休老人,也会来分一杯羹。
前垃圾分类时代
每当说起这个话题,小李就会流露出四面楚歌、强敌环伺的警惕,“我承包了,他们凭什么跟我抢?”
“14号楼住着个阿姨,我知道她就是捡垃圾的,见到好几次了。有一次当着我面要捡走一个纸板箱,我问她要,她非说是她自己的,现在不想扔了。真要是你的东西就算了对吧,但小区里所有的废品都是我的工资啊,不然你自己来清理垃圾?” 我问小李后来怎么处理,他说只能让那位阿姨捡走了,“又不能打又不能骂,之前也有人抢了一下就把自己关进去了,这我可承担不起啊!”
小李说的,是 “一个饮料瓶引起的血案”。去年10月,在上海闵行某小区内,一位80岁的老太在垃圾桶内捡走了一个饮料瓶,正巧被该小区的保洁员高某撞见,他出手抢回饮料瓶,在争执间推倒老太造成其左手骨折。作为小区的清洁工,高某认为小区所有的垃圾理应由他处理,觉得老人是来到自己的地盘抢废品,但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他提起公诉的检察官可不这么想:“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小区并没有相关的规定”。
公诉人的说法耐人寻味,关于垃圾桶主权及桶内垃圾所有权的争议,没有 “自古以来” 也没有 “神圣不可侵犯”,只能被 “没有相关规定” 一笔带过。
法律鞭长莫及之处,总会长出草根秩序。不能和小区里这些捡点破烂、赚点小钱的老人们正面交锋,小李就发动同情自己的居民做 “眼线”,见到哪里有扔出来的纸板箱就通知他去捡,“不过有时候我赶过去就已经不见了。”

小李的老丈人接手将垃圾车骑出去,小李拖着桶走回垃圾楼
防不胜防,小李只能优先搞定小区外的拾荒者。想不到来小区不久,物业就换走了整批门卫。小李赶紧为他的 “天时” 和 “地利” 补上了 “人和”,“和那帮新来的兄弟打好了关系”,让他们帮着把小区外的拾荒者,拦在了大门之外。
但对街的收卖佬,可没有拾荒者那么易挡,“小区居民打电话叫那人上门来收垃圾,总不能不让人进来吧。” 陷入守势的小李,在每栋居民楼、每个垃圾投放点都贴上了自己的电话,“现在慢慢多点人知道叫我了,有些居民送给我,有些卖给我,虽然要花点钱,但总比没有废品强”。
这位收卖佬姓周,生意就在人行道上张罗,一人、一车、一秤。平时他在废品堆起的小山边上支起一张躺椅,懒洋洋地躺在里头睡觉或者玩手机,夏日的骄阳再毒辣,他也只是往树荫挪挪,从未翘班。我曾问周叔能不能上门收废品,他二话不说递上名片,说你多攒点,打电话叫我去收。我再问他,垃圾分类之后生意怎么样,他摆摆手说,差不多,差不多。
后垃圾分类时代
周叔的话不知真假,但小区里的战局,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往,小区这一千户人家丢出来的废品,每个月都可以给小李两口子带来大约9000元的收入。但自从小区于6月头提前开始施行垃圾分类,他们6月整月的收入就下滑到了6000元。这倒不是因为大家为了避免分类的麻烦,而主动压抑物欲、源头减废,按小李的说法,大家只是减少了废品的丢弃,“现在丢垃圾不仅分类还定时定点,大家就不愿意扔那些大纸板箱了,以前直接放楼下多方便。”
“而且,那些捡废品的大叔和阿姨,原来还要在垃圾桶里翻找,现在扔出来的垃圾已经分得清楚清楚,他们就更方便拿走”,小李还不忘怨怼一下他的竞争者,但事实上,看守定时定点垃圾桶的志愿者郑叔,是小李坚定的队友。郑叔是19号楼的住户,年逾花甲,已经退休,他每天都要到岗4小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大家把湿垃圾“破袋”,“一个月下来嗓子都哑了”。
郑叔不是没遇到过想顺手牵纸板的人,但都当场制止了。深谋远虑如他,深知没了小李不行,“现在如果垃圾分类没分清楚,政府的垃圾车就不把垃圾拉走,小李那里是保证分类最后一关。怎么能让人抢他的废品,他又没有工资,要是不干了小区怎么办?” 这时正是台风过境的次日,政府的垃圾车因此四天没来,一个个硕大的黑色垃圾袋已在垃圾房前堆成了山。
此话不假,小李曾跟我透露过,“如果收入一直这样少,可能就不干这行了。” 说话时,已近晚上9点,月色下的两口子还在忙碌着把塑料的瓶瓶罐罐装进巨型麻袋,麻利地装车,准备将它们卖到回收站去。
以前小区对面就有个回收站,但为了保护旁边的一棵老银杏和400年古迹,回收站被拆了。现在,小李要骑到两公里外的回收站去卖废品,但他只敢在夜色中出发,“因为我这三轮车改装过,没改装过三轮车也不让上牌照,4月份社区民警就跟我说,以后只能小区里面骑,出去警察抓到就罚100。有一次我趁晚上出去,还遇到突击查酒驾的,算自己倒霉,一车(瓶子)白卖。”

李的老丈人把回收点的垃圾倒垃圾车上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罚款和宣传双管齐下,作为前端的垃圾生产者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分类的责任。按上海市政府在7月31日发布的垃圾分类首月报告,“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上月增加了15%,比去年年底增加了82%,可回收物比上月增加了10%,干垃圾则下降了11.7%”,这意味着,原本混入干垃圾里的湿垃圾和可回收物,现在被更好地分拣出来了。而对处在中端的垃圾承包商小李而言,不论是清运还是分拣的活都确实地少了。人是轻松了,但收入也少了,这让小李一直意难平。
后来,小李和郑叔都提到了一笔 “一千多元” 的津贴,说是对他们在投放点监督垃圾分类而给与的补助。所谓 “一千多元” 并非一个概数,而是居委会一直没有明确告诉小李那笔补贴到底会是一千多少。直到垃圾分类施行满月,也就是7月31日这笔钱真的下发的时候,谜底才被揭晓:1800元。
新的竞争
虽然补贴暂时还补不上废品减少造成的3000元缺口,但多少让小李不再那么悲观。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以及做好风险管理,他不再在月黑风高之夜骑车去卖废品,而是把自己这边的废品都并入隔壁老丈人承包的小区,“那边居民多垃圾多,要4个人才能忙得过来。我把垃圾送过去之后,量大,就可以叫回收站派车进小区来收。”
最近,他又砸重金添置了一台压缩机,也是为了提高运输效率。但几乎同时,一台资源回收机突然空降到了小区里,还正好在通往垃圾房的必经之路上。这台 “互联网 + 回收” 的产物,打着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 的名义,扫码、开仓、投物、称重、积分,居民左手投入可回收的废品,右手的手机上就会立即获取可供提现的积分。回收机上还配备摄像头,投入杂物会被拉入黑名单。

小区的垃圾分类回收机,白天有人指点居民操作
这无疑又重创了小李,“这台机器装了一个礼拜,我的收入又少了三分之一!” 之前还是同维竞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对小李而言,则是无法抵抗的冲击,至少在各家科技公司努力占据垃圾风口的短期内。一周之后,小区另一个角落又增设了一台机器,小李远远看着。“饭都没得吃了,我就不做这份工作了”,仿佛为了明志,他又跟我提了一次他的去意。
体力劳动者,手停口停,而现在小李的双手为了分拣干湿垃圾忙个不停,供他去换取粮食的可回收废品却已锐减。而我除了把在X猫购物节剁手时拆出来的纸板箱、整个夏天喝饮料留下的空瓶、以及家中各种看起来有可回收价值的物事,都整理干净交到他手上之外,也不知道还能帮他些什么。
垃圾的物权仍不明晰,而垃圾的市场化已是常态。当垃圾回收从业者无法保障本就微薄的利润,曾经的废品回收链条必然崩塌。旧的平衡已被打破,而新的均势未必能顺利建起,但愿垃圾因无人清运而淹没小区的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