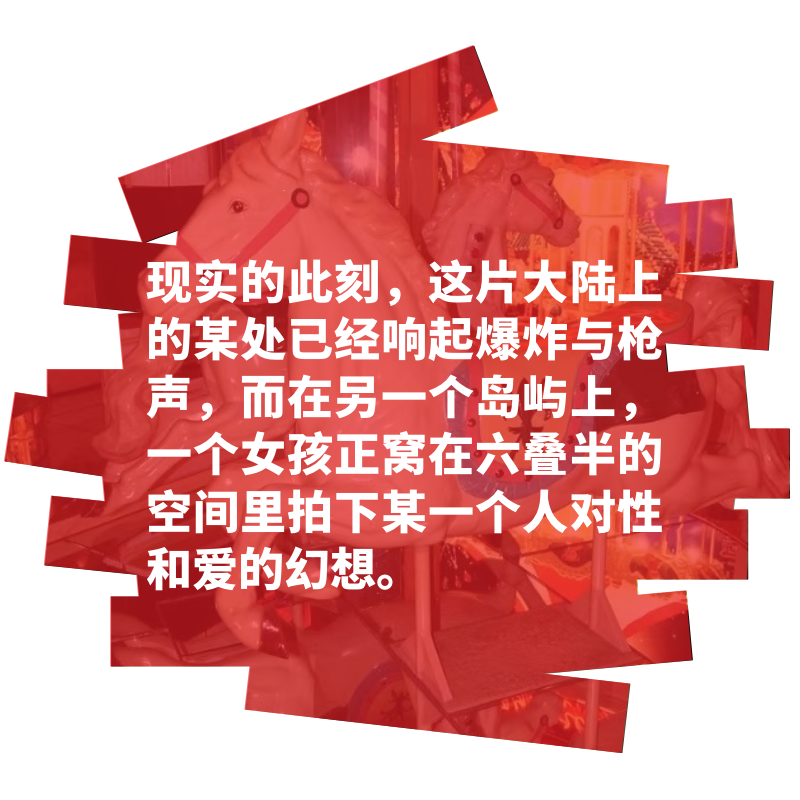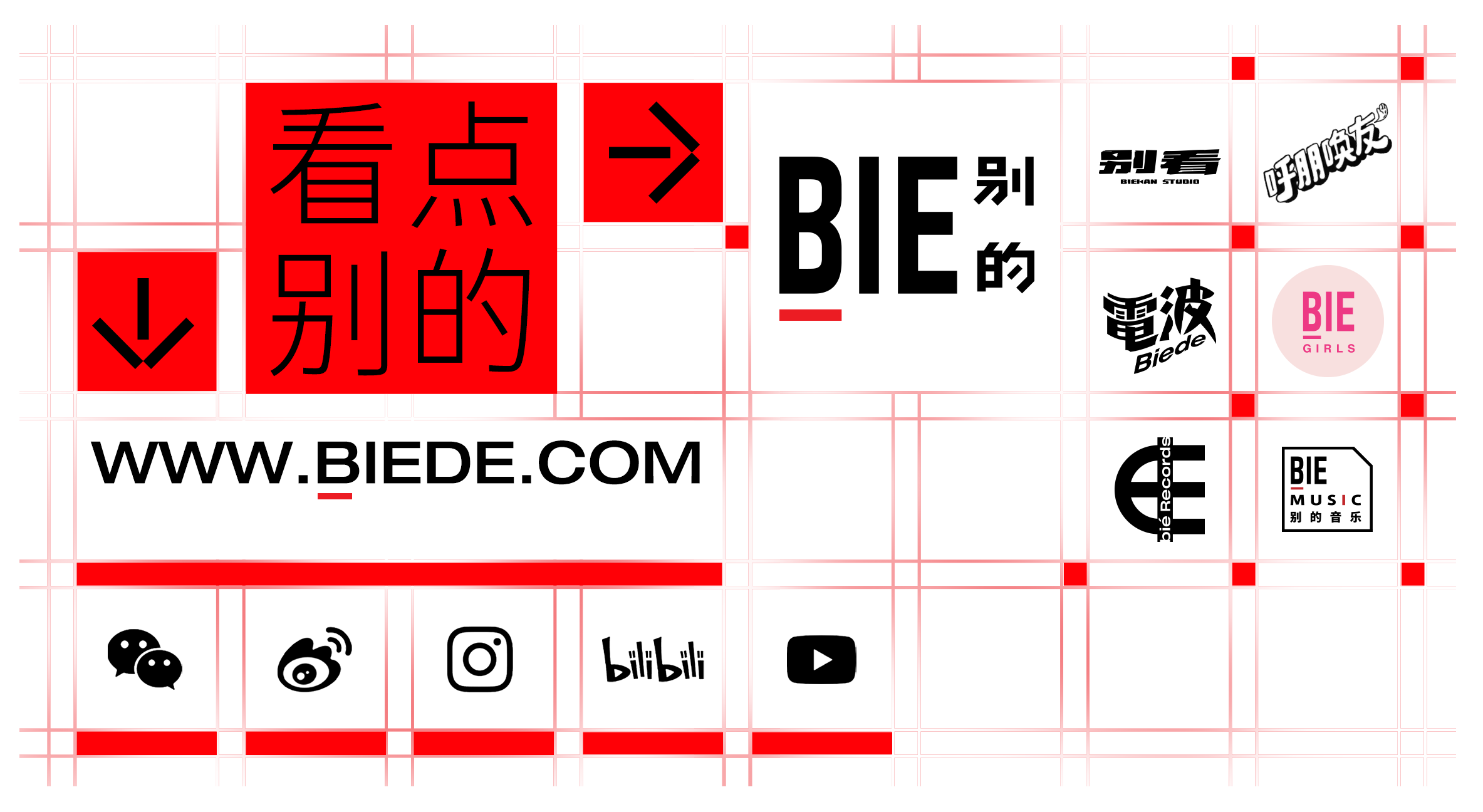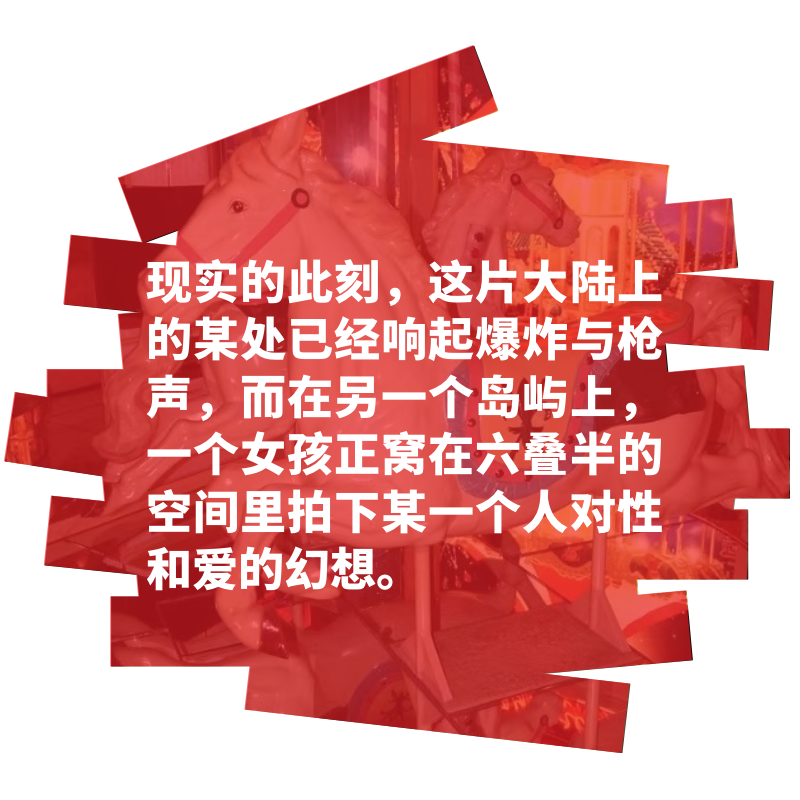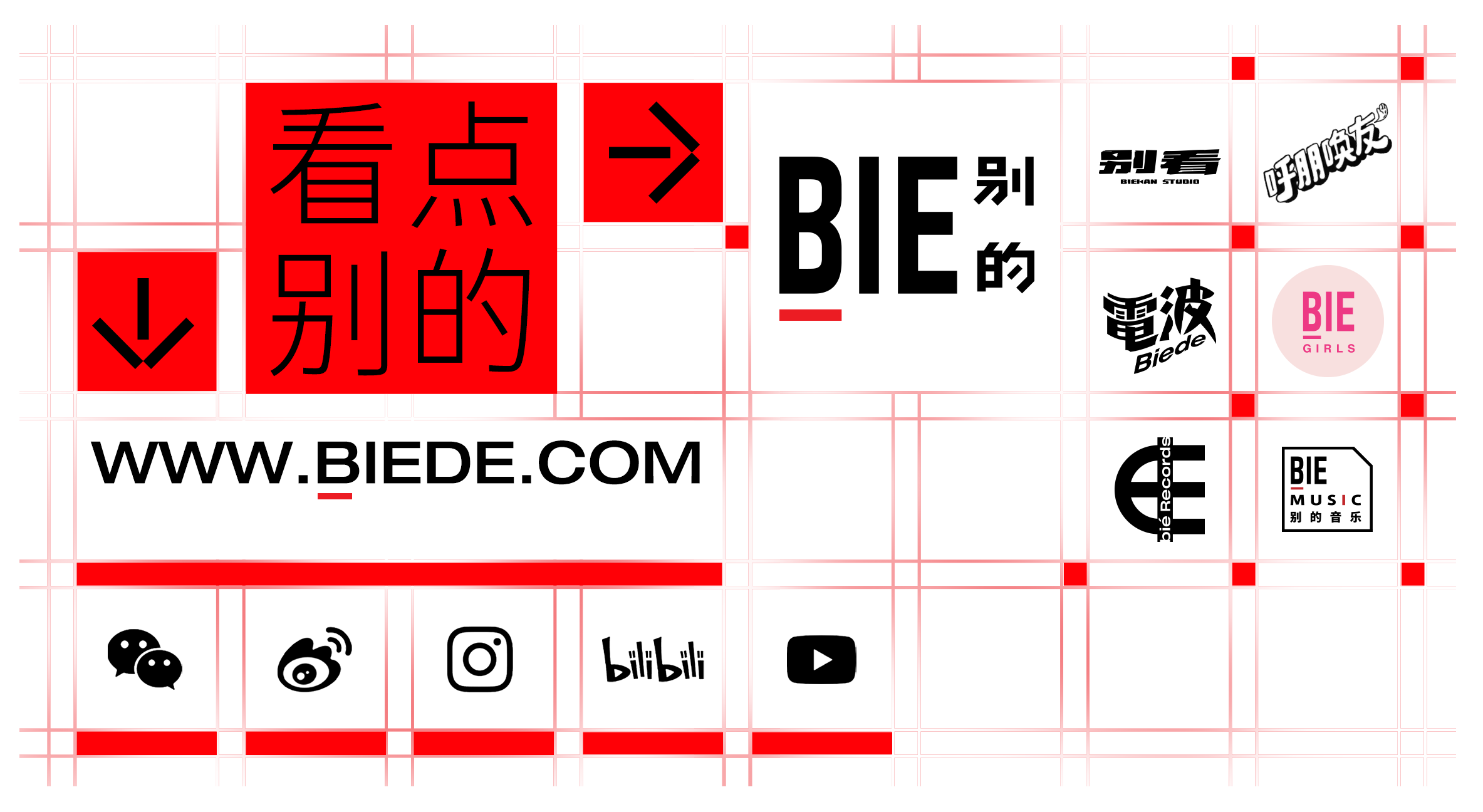上面的这段回忆来自 2018 年,某种意义上,saya 在无意之间成为了当下为数不多的记录者,在她拍下的照片里很少能发现属于这个时代的痕迹,如家具或装潢——那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当时我们热烈讨论的情人酒店正在逐渐消亡。 正在酒店门外发生的变化不会停下,前几天 Vice Japan 重新发了一遍 Shane Thoms 拍摄的关于已经荒废的情人酒店的照片选集,根据一份 2015 年的统计,18 至 39 岁的人有四分之一认为自己的欲望水平低。近年来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情人酒店正在被废弃,如今这个行业的收入的早已仰仗于旅游业。赶上东京奥运会的浪潮,原计划翻新以迎接各地游客的再建计划也因为疫情而被拦腰打断,就像本文开头提及的热海当时面临的情况一样。 也许在这个时代,像情人酒店一样能提供合适的交欢幻境的场所已经过时,而找到能和你一起体验的人则更难。事实是,女仆咖啡厅,按天数出租家人/情人,这些事物的出现已经验证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更加悲观的端点——比起营造与爱人的性爱幻想,造出自己正在被爱的幻想更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 那时靠在人行道护栏上,我和 saya 又沿着别的话题谈了下去。如果走下道玄坂,能看到临近末班电车的时间涩谷站车站仍然人头攒动。其实每当从爬山旅行回到东京时,我都会有点负面情绪:城市其实是更加吵闹又复杂的森林,个人空间其实只是一个个被水泥围起的隔间。 像这种时候,我会希望可以有 10 分钟的透视眼,让眼前的一切变成无数图层叠加构成的剖面,让我看看每个隔间内人的生活——街道上的行人,夹在上方居住层和下方办公层之间的大厦里的酒吧,而在地下是不是还有派对在进行。和 saya 交流过后,这份妄想中又加入了藏在情人酒店街的幻想动物园和电影院。当和能让你感受到爱意的人共处一室的愿望,也变成一种可以出租的幻想时,即使是现在看来会让人尴尬的那些摆设也会显得可爱。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几天后我在她的 SNS 上看到了一张她坐在像秋千一样的木头椅子上的照片,背景是人工痕迹明显的蓝天白云和城市远景,她的双手高高举起,笑得很开心。当我在键盘上敲出这些字的时候:东京都内单日新增感染 10169 人;テレビ東京中断节目查播公布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战的消息。平复心情,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个话剧,《三月的五日间》,在美军轰炸伊拉克的前后五天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六本木的 Livehouse 相识,之后一起去了涩谷的情人旅馆,当他们第三天出去吃饭时,才知道他们亲昵的这几天,伊拉克战争爆发了。然而,他们还是回到旅馆和前两天一样,第五天早晨,俩人 AA 付账后离开旅馆。现实的此刻,这片大陆上的某处已经响起爆炸与枪声,而在另一个岛屿上,一个女孩正窝在六叠半的空间里拍下某一个人对性和爱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