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格格的意思是,还是长大好


桑格格的年龄焦虑起始于小学一二年级,结束于小学五年级。那会儿,年方七八岁的她想,天哪,五六年级该是多大的人了,她们太大了。完完全全就是大人了。更不要说初中生高中生,那都是些很可怕的“社会上”的人了,挎个包包抽根烟干架,隶属“天棒”、“街娃儿”和“二流子”大军。
后来她发现,到了五年级自己没啥感觉,到了高中也没啥。她想明白了,时间就是连贯着滑过去的,你在今天和昨天没有区别,在五年级、高中毕业、26岁或是40岁,都用不着自己来制造节点“砍下一刀”。有时候她自己都想不起她现在多大了,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大概不小了。
不小了的桑格格最为人知的身份是畅销书作家、成都人、电台主播、辍学北漂的记者、酒后表演艺术家……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她写了4本书,定居过的城市有5个,一起生活的猫“老三”今年11岁,畅销作品《小时候》也15岁了。

54.结婚就是和一个男的坐一桌吃饭,然后一直看着他吃,吃啊吃天天吃,一直吃到老。

58.我长大了要和大老白结婚。大老白是只美丽的公鸡。我和大老白第一次见面,我永远不能忘记:它那双小小的圆圆的眼睛,一边一个,惊讶地看了我很久,眨都不眨,好像久别重逢一样。我也看着它,觉得有点想哭,走过去,它居然没有跑,呆呆地让我抱住,我也就比它高一个头。我大舅说,鸡眼睛都眨得慢。屁,他不懂我和大老白之间的感情。
关于《小时候》这本书,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每一个成都小孩都曾读过”,那是桑格格最早亮相在世人面前的样子,它记录了匪里匪气的“成都瓜娃儿”桑格格的成长故事,成了一两代人共同的童年百宝口袋。书是用成都话写的,词条一样散点排列,2007年出版时有1686条,最近全新再版时这个数字变成2258条,后半部分删减10万字又新添15万字,书里的男朋友九色鹿成了她的先生九大师,他们搬来杭州6年,近两年她开始痴迷绘画和毛笔字。
去年疫情,她参与了好友巫昂所在的宿写作中心发起的民间互助组织,志愿者从11个发展到3000个,她们为700多个武汉家庭沟通登记,帮助400多个得到床位;今年7月20日河南暴雨受灾,她在凌晨时再次加入救援互助,转发求助信息并整理提炼。一夜过去,她在朋友圈里说,“中国人经历了一次,不一样。加油。”
诗是生活或人生的剩余部分

最近几年,桑格格开始写诗了。诗集《倒卷皮》在今年3月上市,到7月已经售出2万多册,据她本人说,可能是口语诗里头卖得最好的一本。她记得一个读者反馈,“这本你写的东西很有意思很有趣,有的也打动我了,我愿意买。但是我不愿意承认它是诗。”她挺开心的,因为她就不愿意按照读者内心的“是诗”去写诗,那不是她理解的诗,也不是她要的、想写的诗。
桑格格的诗很有辨识度,她称之为口语诗。诗干净短小,读起来很有“抓地性”。官方简介中写,“在《倒卷皮》中,一首诗就是一个小故事。语言既干净又生动,叙述上则又偏离一般抒情诗的写法,更接近小说。”
诗里的一些瞬间依然能让老读者捕捉到那双熟悉的眼睛。从前她写:“《雪孩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见小兔儿它爸,包括最后它们家着火烧起来了,它爸都没有出现过。它们家,是不是妈老汉儿也是离了婚的喃?”现在她写:“看星球大战/配乐太响了/吵得我难受/简直要吐了/电影一结束/我就跑回家/立刻上床/用被子盖着/受了委屈/我就这样的”;
从前说“白雪公主每次都不听小矮人的劝,上了黑心皇后的当,差点遭整死,简直是活该,不长记性。尤其是最后一次,人家吃过一口的苹果都要吃,还‘白雪公主’,十分不讲卫生!蠢得像猪一样,死了算了。”现在是“哈哈哈刚才有只鸟,嘴上叼了个豆子掉了,掉我脚边了哈哈哈,我停下来看它,它不敢飞下来捡,自己停在树上生闷气,肥墩墩的!脖子缩起来/我肯定不要它的啊。/我好多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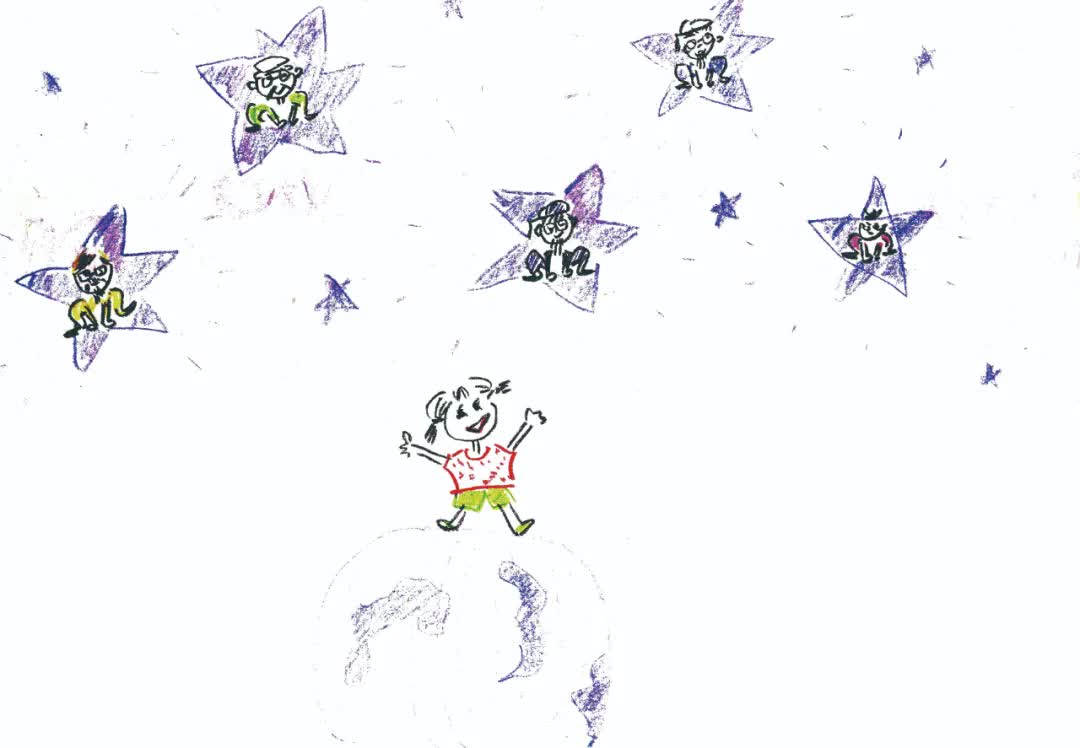
125.每当听说天上的哪颗星星儿又以某某某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时候,我脑壳头就浮现出这样一副图像:这位科学家像只青蛙一样蹲在外太空,他的旁边还蹲着其他科学家——那是以前命名的科学家行星,他们一起用智慧又慈祥的目光注视着蔚蓝的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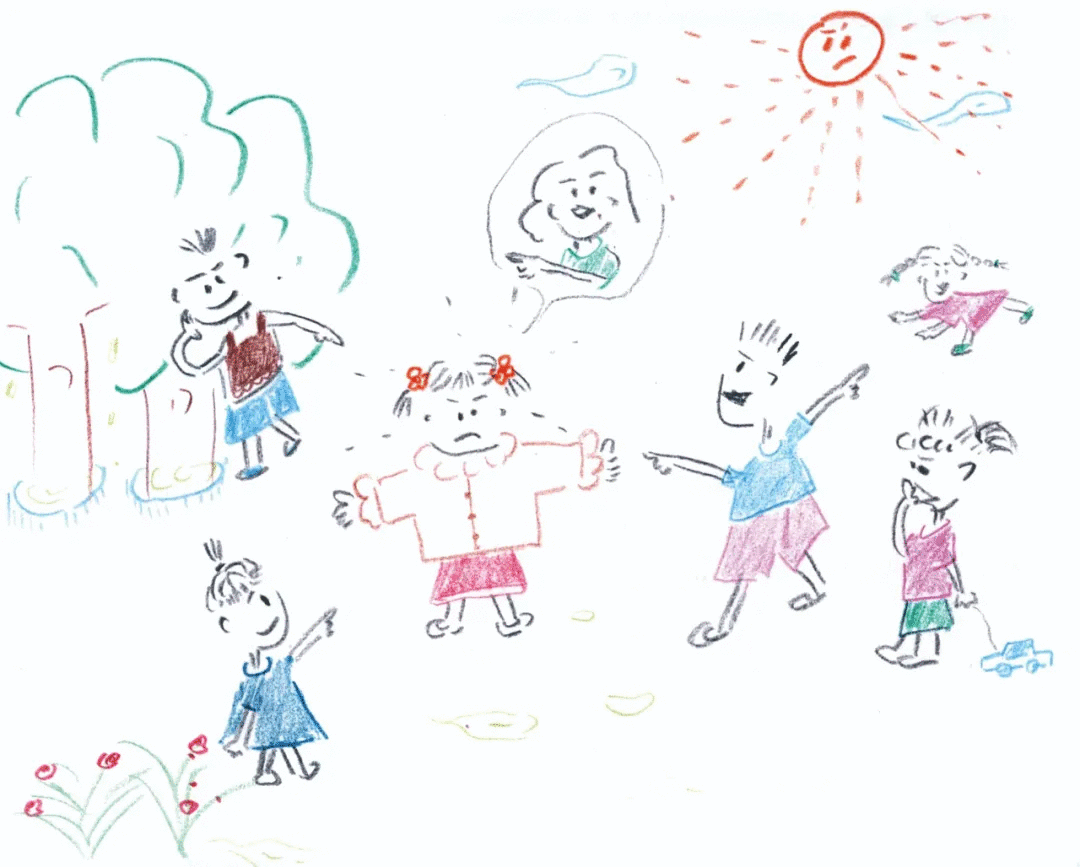
126.夏天,下了一场雨。在寄宿幼儿园,我想起妈妈说,自己要知冷知热,酒吧棉袄翻出来穿上了。
她的朋友、画家李中茂的观点是,“口语诗”这样的称谓比不上“汉语诗”来得确切。因为上一代诗人们一直是用翻译体写诗的,从句套上从句,夜莺匹配玫瑰,格律齐整且押韵,那并不是我们真正日常使用的汉语。桑格格觉得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整体水平比小说要高很多,但是诗歌没人读。“大众虽然不读不看也不研究当代诗,但是对于诗是什么、长什么样子,有一个特别分明的认知。超出这个认知,他绝不认同你这是诗。”
至于为什么开始写诗,她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那段时间她常读王维,有一首叫《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一次偶然她读到诗人何小竹的《石榴》:开春的时候/一树繁花/到了夏天/我数了一数/才四个石榴。讲一个少为人知的基本事实,裹住巨大的宁静和自然纯真。某种相通的东西把她定住了。
后来在何小竹的引导下她尝试写了一首,何小竹说,“你很有感觉,但是在断句和分行上还没有太多经验,我帮你稍微动一下。”他调整一下,她听到脑子里有个东西嗡了一声。“那段时间茶饭不思,通宵就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兴奋里头,你随时都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惊奇,完全是两个人、两个世界了。”她类比,就像是刚学会打麻将的虾虾儿(新手),全新世界打开,手气壮到不行,把把都能自摸下轿(胡牌)。她是一个容易痴迷的人,于是痴迷进去,直到现在。
诗歌是被写进我们的基因里的。都是平头老百姓,亲戚摆酒席,孩子考上大学,做爸妈的腾地端起杯子站起来说,来,今天高兴,大家都在,我来赋诗一首!就像兴致到了就唱歌跳舞一样自然。大家也把诗人看作一种“又严重又崇高的职业”,桑格格说,只是到了当下,诗的节奏和生活节奏不匹配,脱节掉队了。
那天她在家写毛笔字,一卷宣纸一百米,边用边展开,用到最后那一点时,在最里侧的纸上发现一道抓痕。“抓痕就像一道伤口一样,它藏在最深最里头。”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它隐喻了一些生命状态和感受,但也没有超出日常具体的事情。“诗一定是生活或者人生的剩余部分,它是偶然地在一个必然的地方长出来的。”
容器和棱镜

桑格格所提到的“剩余部分”是我见到她前最好奇的地方。写作《小时候》时她28岁上下,书从0岁开始写起,幼儿园到大学,北京广州到上海,她几乎一口气写到了自己站立的当下,笔尖追到了真实生活的脚后跟,那之后她的打算是怎样的?之前的那些将自我作为材料的内容,真的不会打扰到生活本身吗?
我对格格说,小学那会儿读你的《小时候》,好笑的地方是真好笑,但是读完了并不见得心情轻松,尤其是后半段。在新编版的《小时候》里她追加了一篇后记,里面写到前些年经历的严重抑郁。那时候她感受到“有别的东西来要求我”,而“我可写的东西,越来越少”,最初写字的快乐兴奋没有了,她开始躲避写作,爱哭,哪儿也不去,总是悲伤,后来她住院,出院,复发,自我疗养,搬家,在环境和内心都趋于宁静的杭州定居,抑郁症逐渐再没有复发过。
后记中她写,“诗歌对写作者的要求,我模糊地感觉到,就是冥冥中那个折磨过我的东西曾经对我的要求。有点神秘,但是又实实在在。我现在不那么怕它了。”
“你能描述一下当时怕的是什么,以及那个要求是什么吗?”我坐在桑格格对面问她,她一秒没停顿就答,“纯粹和准确。”
某种程度上,这也能回答她对新编《小时候》的重写与修改。人物有了后续,故事有了新的支线,物理距离让发生过的事情更加清明,她把那些再读时觉得稚嫩和煽情的都删掉了,她说,那会儿毕竟距离太近了,现在觉得煽情比幼稚严重得多得多。

2258.我就金梅塞金梅塞金梅塞金梅塞金梅塞,念了一路,直到来到哲蚌寺脚下,看见晨曦中,上山的人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头,眼泪就啪嗒啪嗒滚落下来。
书里的桑格格依然停留在27岁,没有再续写下去。结尾依然是那个结尾,“一个是告别,二一个它又是往上攀登,又说忘不了(金梅塞),又说忘记了(金塞隆),它是一个可能性特别大的结尾,我没有必要去更换它,就像修一个古董,修旧如旧。”
她也提到了最初一些避无可避的瞬间。有时候忽然又想起一丝趣事,分享出来后总有人说,格格,这个我都知道,你在书里写过。她会恍惚和奇怪,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往事被别人全探知了的透明人,但是同时心里又有点轻松,因为这也意味着,有些东西她不会再背着了,它们被人知道了,就再也不会消失了,对她施加的紧迫和焦虑感也就消失了。
她像看别人的回忆那样看着,逐渐发现越不存事越开心,以往自己像一个容器,带有某种现在装东西、未来倒东西的任务意识,现在她希望自己更多像一道棱镜,透明的,空的,让所有的事情穿过自己,别人对她好时她会赶紧地、双倍地还掉,因为很快,不管好的坏的,她的记忆会擦除,事情怎么开始的,连带这个人都会被她不小心忘掉。

394.父母终于离婚了,爸爸要领走一半家产,他开了辆东风货车来,院子里好多人围着看,我也围着看,还很高兴,嘻嘻地笑。看着那辆东风车越装越满,我开始着急了,那是我的家阿!我爬上东风车,把拿得动的小东西一件一件丢下来,一边丢一边仰头往楼上喊:妈——快下来阿!我帮你又抢回一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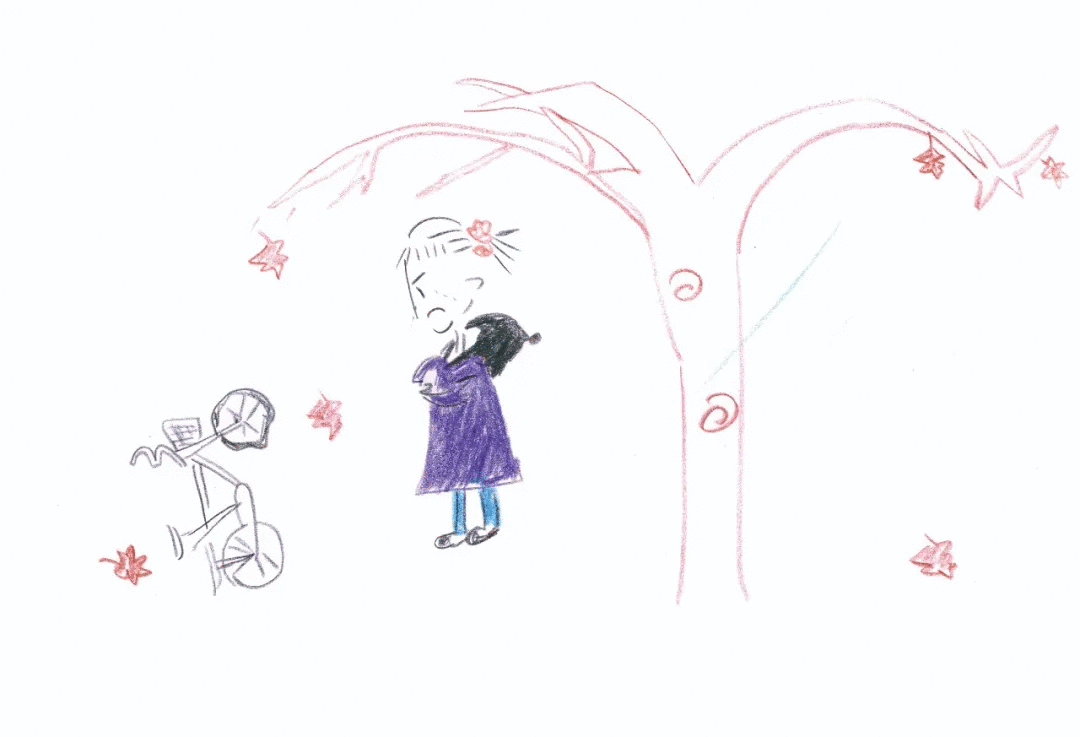
2083.看见一辆小小的自行车,破旧地躺在冬天里,死了。
在这之前,她驮着一段啼笑皆非的小时候,还有四座灯火辉煌的城。千禧年跨年夜,她跟几个朋友在府南河边喝酒跨千年,后来去了北京,她记得北京的干燥,住在酒店里需要把淋浴头打开,水雾腾起时才能够正常呼吸,但那座城市的胡同、灰墙、大馒头和秋冬苍劲的树她依然迷恋;上海要总结出性格或者形象会比较难,广州更像是一个穿着香云纱梳着大辫子的阿姨,总是笑眯眯的,有一点粗壮,能做各种美食,但是性情保守,逆来顺受。在广州时桑格格住在九平米的闷热小房间里,兼职给汽车和珠宝品牌写过广告文案,能回忆起的关键词是“至尊”和“璀璨”。
“格格”是格格不入的“格格”

对成都的感情是最复杂的。成都有她最多的读者,每次回去,她们围坐在一起抱着她哭,她也跟着一起哭;最想待的地方只有文殊院,因为那里有她爱吃的甜水面。走出机场前往双桥子,每一步都会觉得自己在慢慢苍老,一种失去掌控、任谁都能欺负摆布的感受腾起来。
很多事情像沉积岩一样盖在她身上,越压越紧实,母亲是其中一环,家门之外的420大院也是。辛酸的片段看过笑一阵自然是好的,但她也总在想,为什么人生下来会这样苦,没有办法选择生在哪,父母是谁,即使每个人在当时的处境下已经拼了全力。在幼小得无法认知“悲哀”或“愤怒”这种情绪的时候,遭受很多细小但庞大的事情,没有条件去后知后觉,所以首先学会的是接受。
“委屈的前提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更好。但我其实是一个很讲道理的小孩,我会问自己一句,你想过很好的生活,你想被这个世界善待,为什么?谁负责给你这一切?你凭什么得到这一切?为此你付出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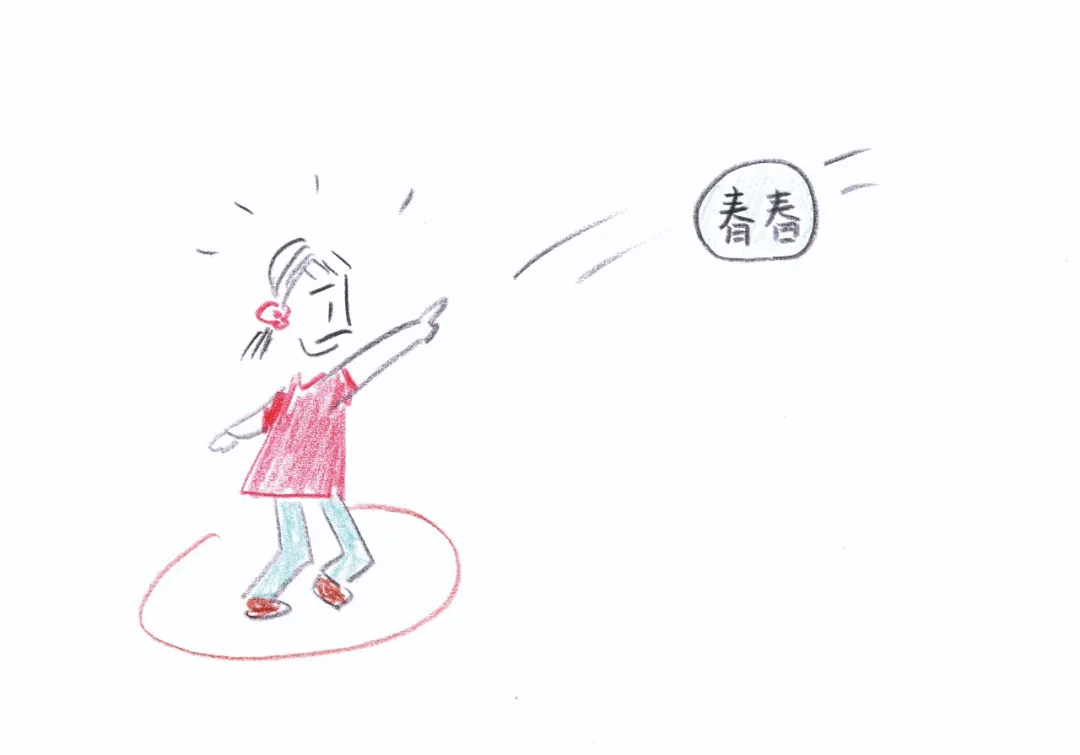
1491.每次说起“浪掷青春”这个词,我就想象着自己把青春像扔铁饼那样扔了出去。
本质上来说,桑格格相信人是生来受苦的,没有什么可延续。那种书里随处可见的莽撞和天不怕地不怕,以及因此发生的诸多趣事,她把它归结为一种接受现实的行动力,“就是不愿意委屈或者哭哭啼啼,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做点什么,让这些有点改变。真的是会改变,但是前提是,你做什么都不会把你想要的东西真正固定下来,什么都会变化。去做的时候就接受自己彻底的失去,把这个想清楚,心里就会安定下来。”
她问我,你也是成都人,不知道你怎么去总结成都的特质?我还在斟酌时,她自己把话接了下去,“从个性来说,我的性格没有一样是和成都相同的。成都人爱耍爱得理直气壮,但我不是一个爱享乐的人,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本质上的差距。我知道它的好,但是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东西,我只能离开它,这样我跟它还有一种纯粹的情感上的连接,属于故乡的。但我在那时,时时刻刻都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她觉得最能代表成都性格的一句方言是“不存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暗示性的、暧昧的,而且还自我彰显的,似乎这个事情我能化解,有什么困难我都能做到,对我来说不是个事儿…这种劲儿特别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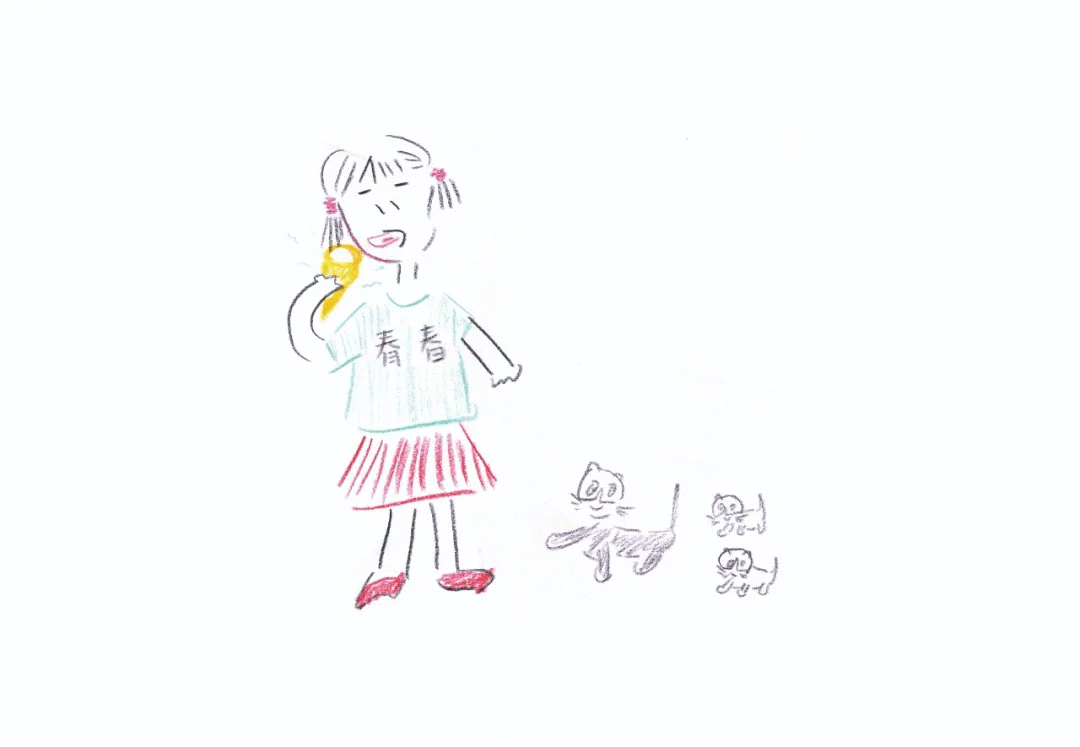
2058.认真地舔一只甜筒,一圈一圈转着舔,看着它越变越小,觉得青春消失得真快。
而在她自己的讲述里,无论是书里还是现实中,她身上的劲儿和这段描述都是相反的。桑格格是一个杂糅了“很成熟”和“很瓜”两种特征的人。她说,知道要什么、怎么去做、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成熟而清醒的。即使是在小时候,第一次被妈妈抛下时嚎啕大哭,第二次也会坦然接受现实,只是心理上和母亲就这样疏远了。不过在好友豆豆的眼里,她一直是那个不会使用外卖优惠券、电脑使不利索的“瓜娃子”,她觉得豆豆也没说错。
知道自己的界限好像也就知道了自由

九大师对格格的评价一直都是“又没文化又可爱”,她欣然地接受,她说自己就是喜欢没文化的人,活得鲜活用力、“我们工人阶级”的人 ,比如她的好友、作家李娟。她回忆起有一次她们在新疆的街边吃着凉皮,远远来了一支接亲的队伍,李娟突然站起来就开始跳舞,在当地的风俗里,跳舞拦下队伍可以获得一个小红包。“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和她在一起我反而变成慢条斯理的那一个,她会用焦虑、急躁和啰嗦来掩盖羞涩,她很可爱,跟她的交往会让我感觉不是在跟一个作家交往。”
至于她自己,写东西写得开心了会不自觉蹲在椅子上,喝醉酒后的表演可以让羞愧期长达两年,说起最近在做的事情看的书并不会吝惜表达,她说,现在的很多作家都太爱惜自己了,文学自觉太足,但诚实和纯粹程度总是差了一点,不是靠生命撞击出来的东西。她还说,最近在读黎紫书,写得太好了,整部作品的文字完全地和生活风貌缝合,句子和句子编织在一起,说不出什么金句,这样反而是更好的,从这个角度,黎紫书是好于张爱玲的。
我们也聊到了疫情期间她参与的志愿者活动。桑格格没有全职上过班,这是她难得的体验社会化分工和团队协作的经历,真实地参与了生死,也真实地帮到了人。对接上一个患者后,她们会根据患者情况建一个小群,群里有医生,有志愿者,有负责外联的人,还有心理医生,小团队会针对患者的家庭情况和日常需求来想办法解决具体问题。时间在过去,有的人会因此被救回来,有的会因为年纪过大或并发症离世。爱退群的桑格格从没有退出过这些“已经走了”的小群,大家不约而同都保留着群聊,“就是想要多陪他们一会儿。”
她也遇到过所谓的骗子或骗局,人是复杂多面的,救人的同时也骗人,出力同时也获利,桑格格曾和这样一个人一起参与了多次救援,后来事情被查出、舆论涌起时,那人发微信来问她,“你觉得我是个骗子吗?”
她对我说,其实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总是同时被人看到的,但是走向暧昧的事件会因为一句话而改变,所以看得到的人可以选择怎么去说,她记得自己当时想起王阳明,那句话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她想要回答那人,“我觉得你可以不是。”

1495.阳光里站着,看着自己的影子,不知为什么,突然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
疫情过后,志愿者们不愿意就这样解散,这些群被拆散成无数个小群,大家根据共同话题成立兴趣小组,有摄影、毛笔字、钓鱼、咖啡、诗歌等等,桑格格加入了其中的一些,又很快退出了一些。退群的理由到最后大多是相似的,她会害怕其他人过于喜欢和依赖自己。
还是回到容器和棱镜的问题,就像是在被因缘追着跑,她一直在朝“不用存在”的方向努力着,将自己倒空,希望平和地被一个安宁世界所遗忘。自己和自己的精神世界直接对话,生活里也不再需要更多的朋友,没有太多主动的社交,提醒自己每种感情准确而不要过度,也不想亏欠任何人。

1842.我们开车走了,婆婆站在乡村竹林边,单薄衰老的身影越来越小,小得很,然后就消失了。
有朋友来拜访看望她欣然接待,老三会懂事地招待客人,是一只“响鼓不用重锤”的完美猫咪,经常把客人美到眩晕;夏天来了分享一些自己的食谱,不舒服的话就多喝藿香正气水;诗集出版后,当了几个月的诗人心烦了,就连续好几周不再写诗;妈妈最近也搬来了杭州,老太太年纪虽然大了,依然很有自己的性格和想法,在周围制造小型龙卷风;桑格格依然无法在自己的写作世界里找到直面阴暗和苦难的命门,她说自己对非虚构的依赖还是很强,黑暗的东西写不了,但是转念想,知道自己的界限了好像也就自由了。不要自由时你就自由了。
她描述了一个梦。那会儿她还在广州,有天梦见了自己的前男友黑社会。她说自己从不跟前男友联系,还联系的人要么是爱得不认真,要么就告别得不太认真。一向认真的桑格格梦见在一个海滩上她们相遇,黑社会想要留住她和她多说几句话,而她急于离开,她记得自己梦里无厘头地说,我有事走先,家里火上有汤。她还记得自己说,我刚才在海滩上看到一只蝴蝶,我确定你也看到了。黑社会说,我看到了,是这样的。
关于我的小说,我想这样,找一个本子,麻制的,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黑色的碳素墨水或者纯蓝的英雄墨水,还要用彩色蜡笔画些小画,然后送给我最爱的人。他也许不会看,一直放在他箱子里,落满了灰尘。我呢,从此也不再提起这件事情,照常生活。
文中配图、图注文字授权自新编版《小时候》;
题诗《还是长大好》引自桑格格诗集《倒卷皮》;
文末文段引自桑格格《小时候》原版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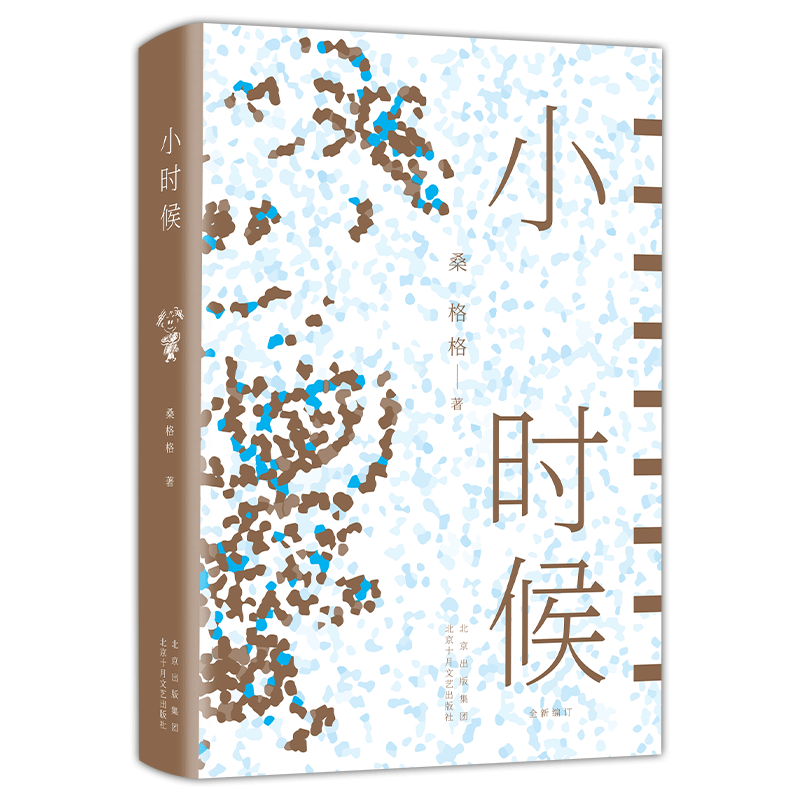
全新编订版《小时候》现已由新经典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