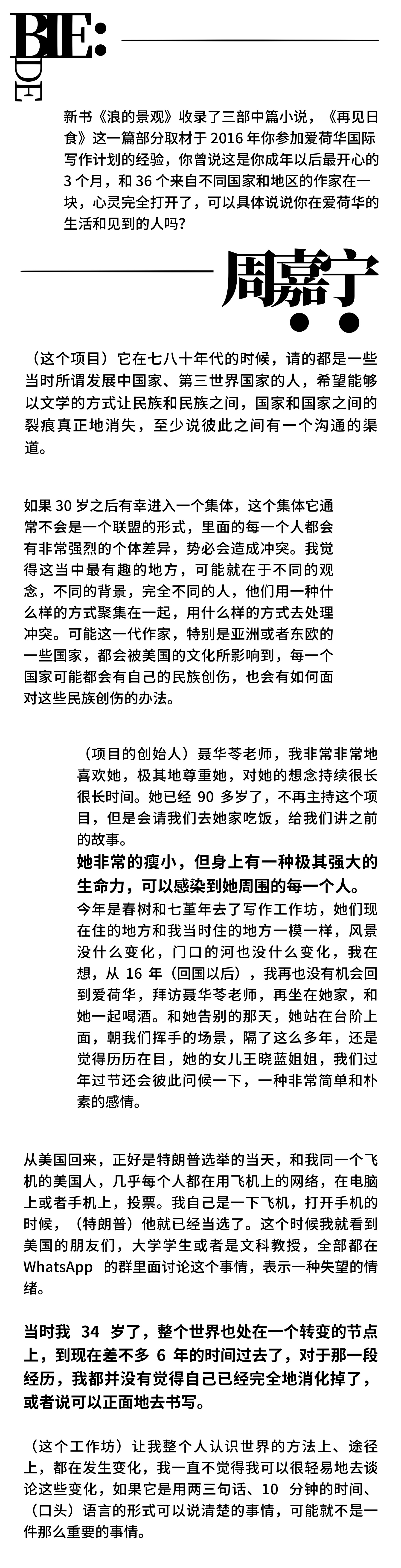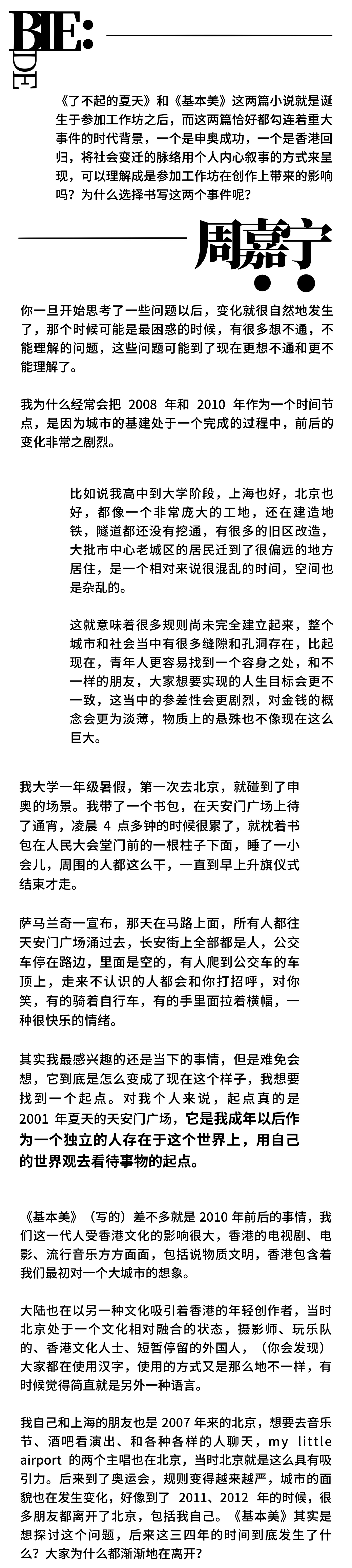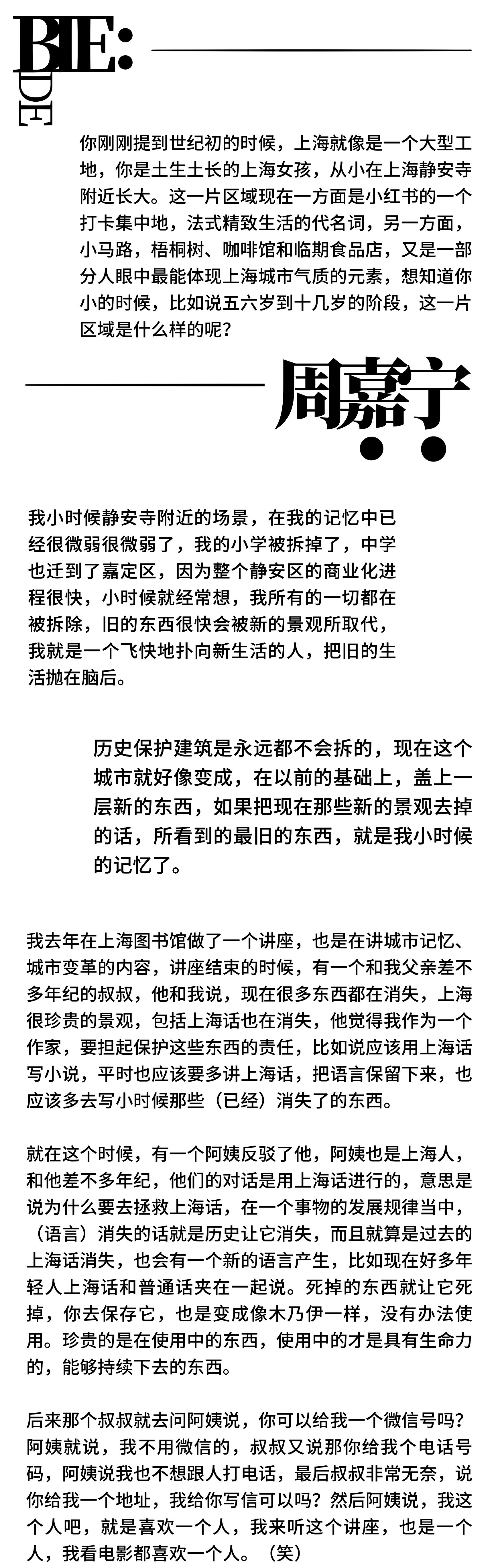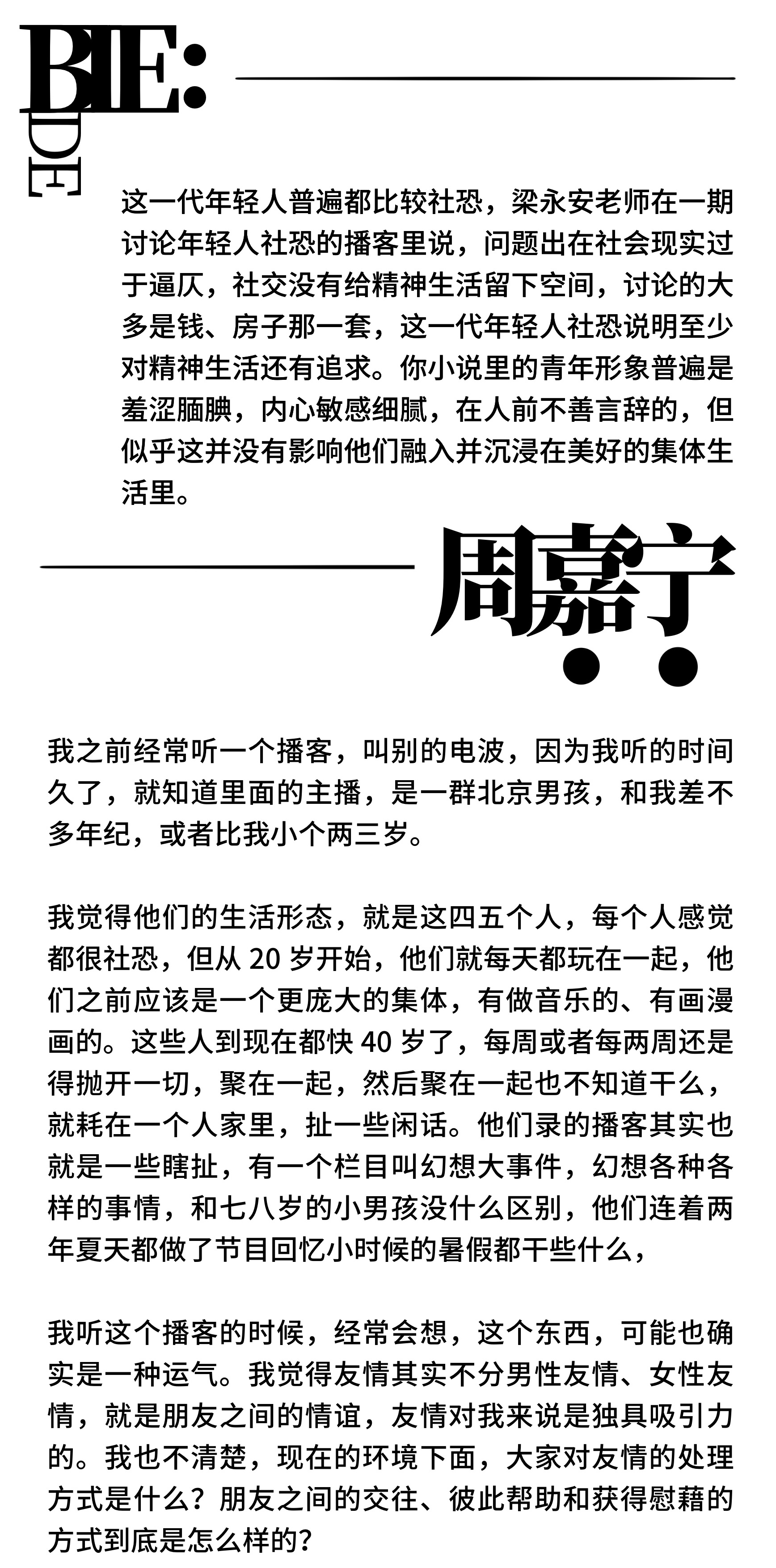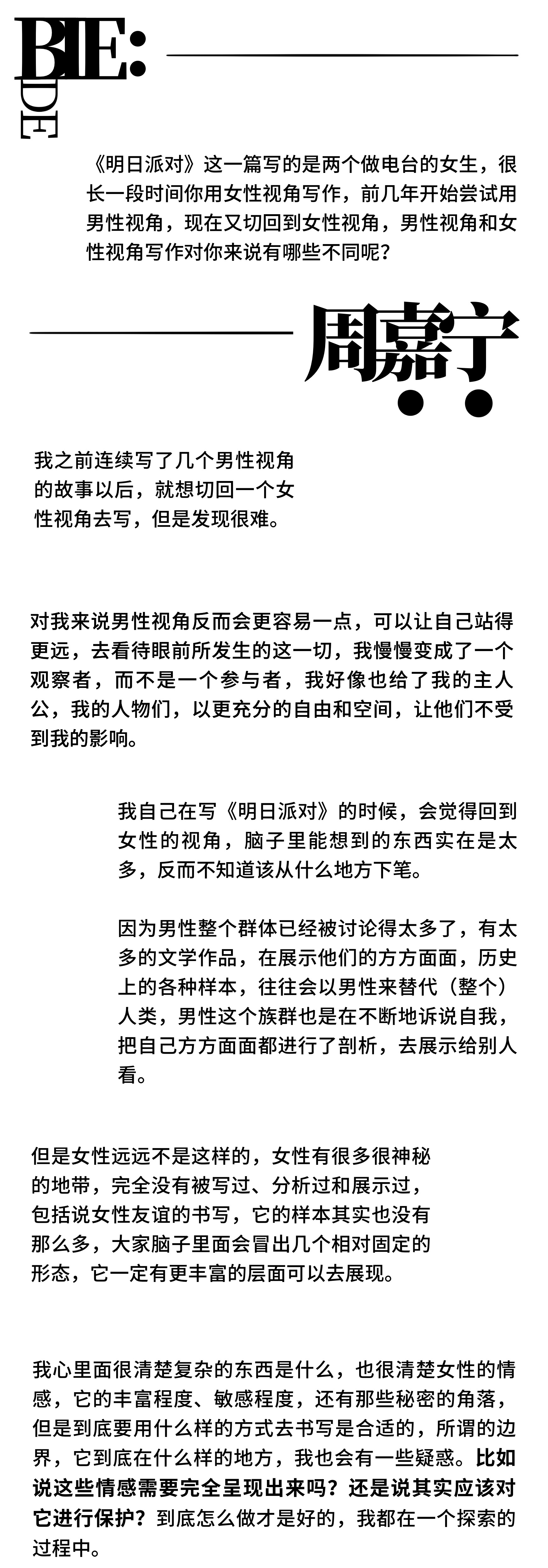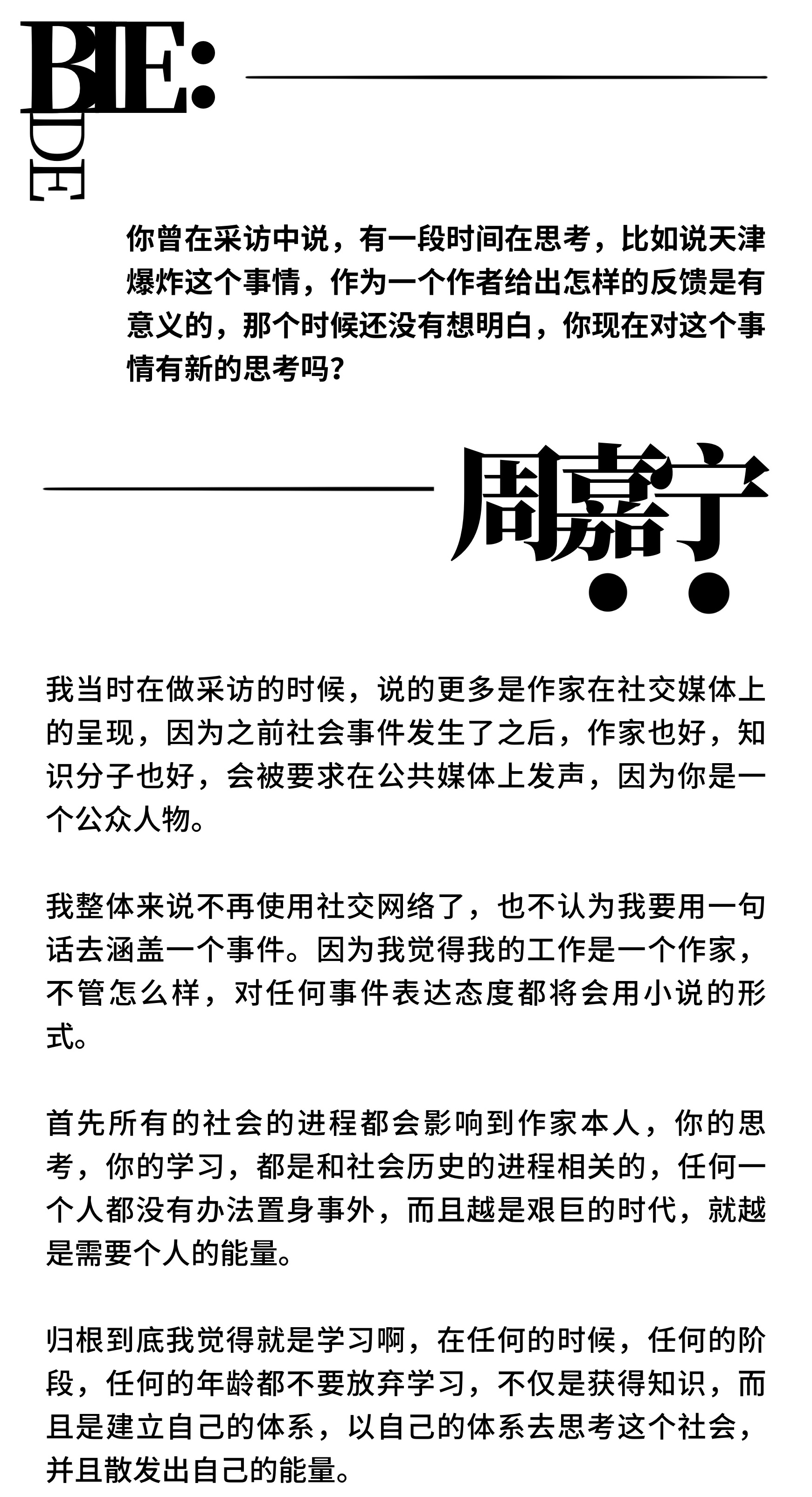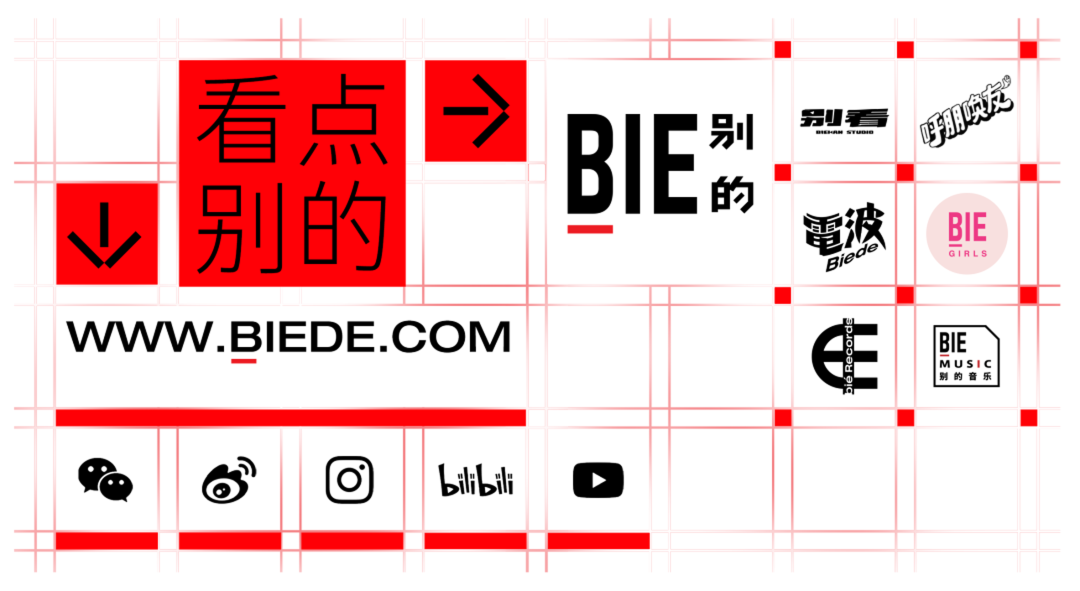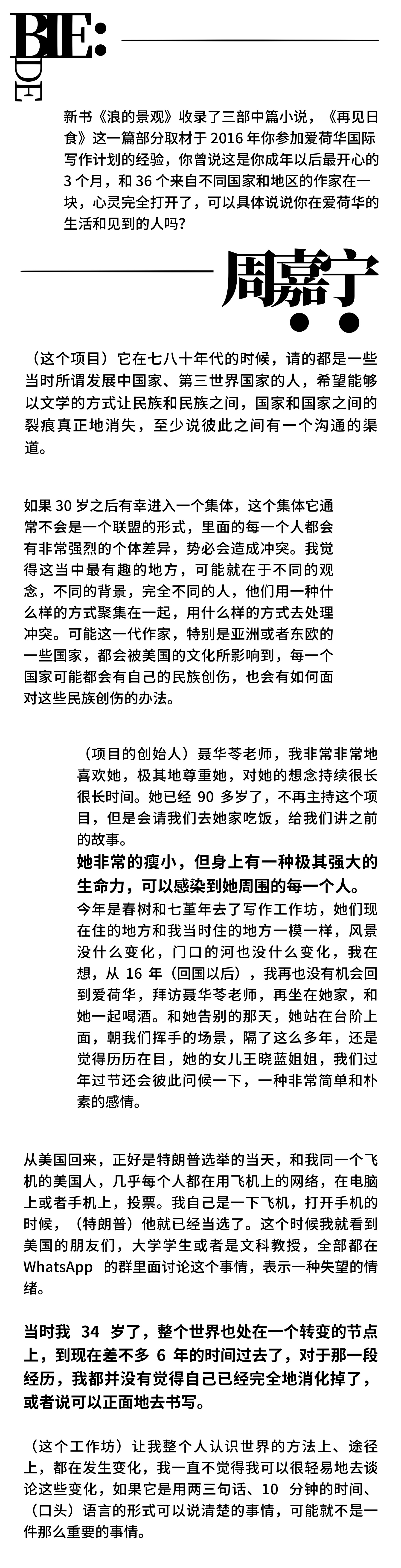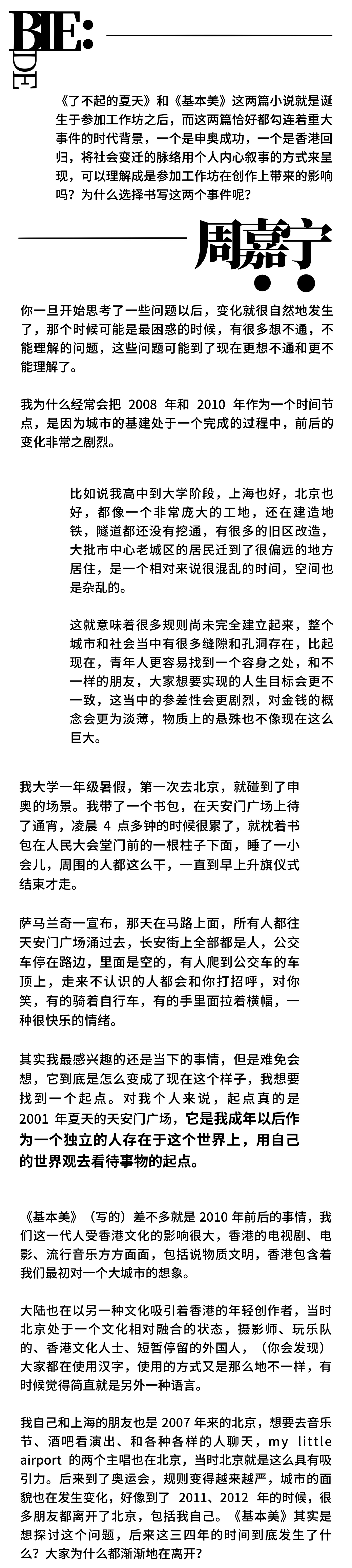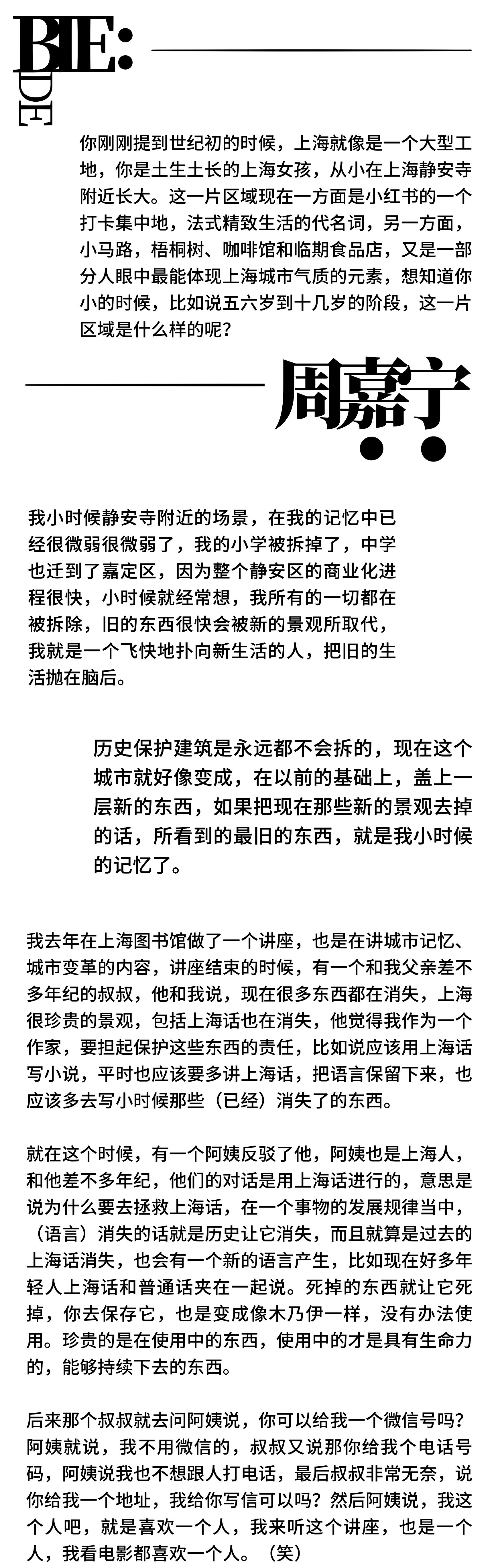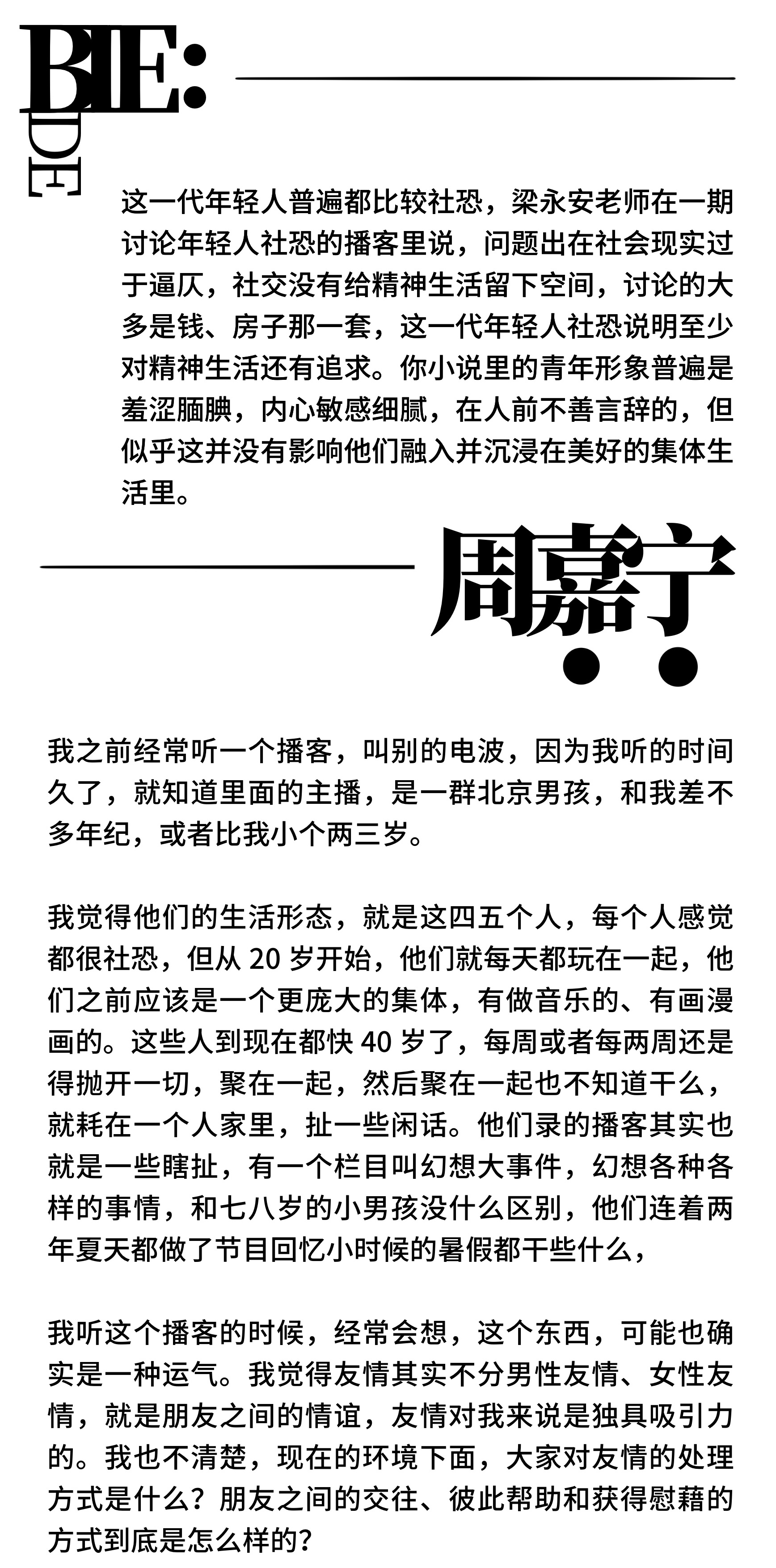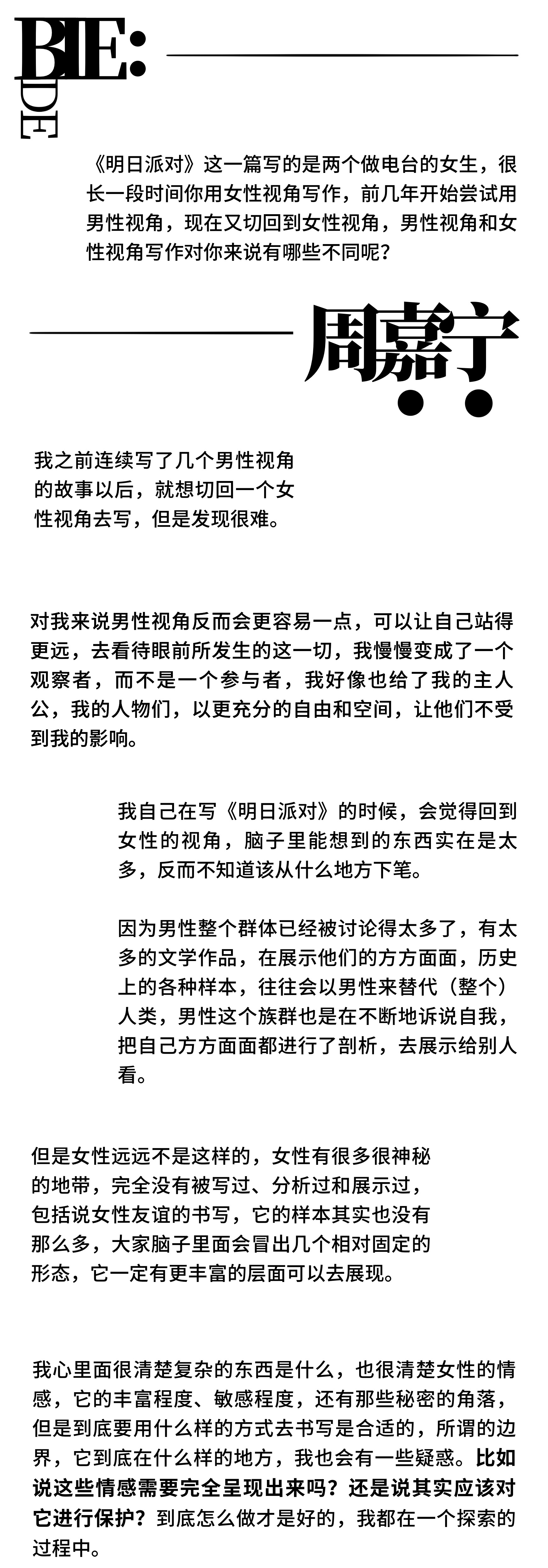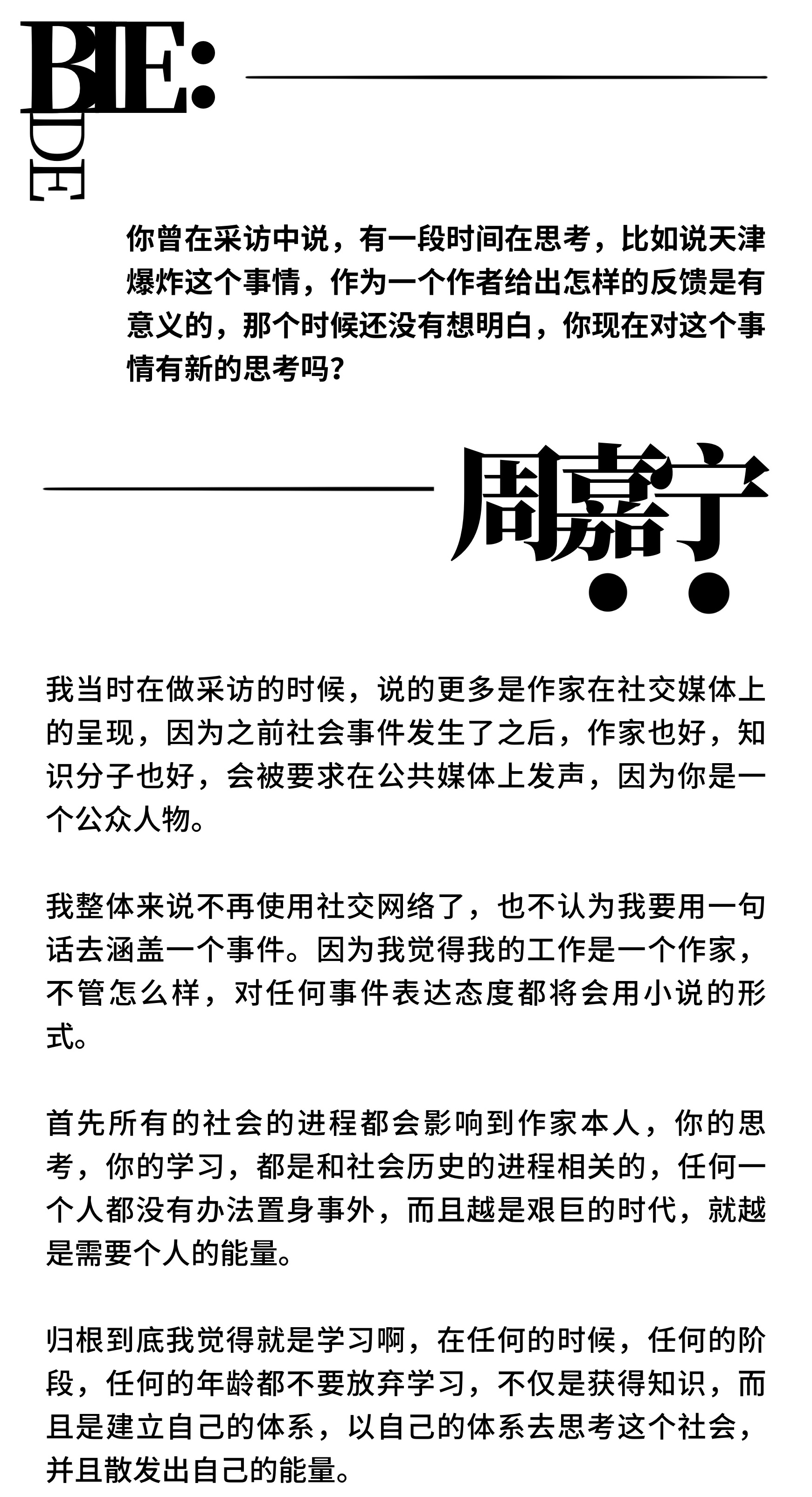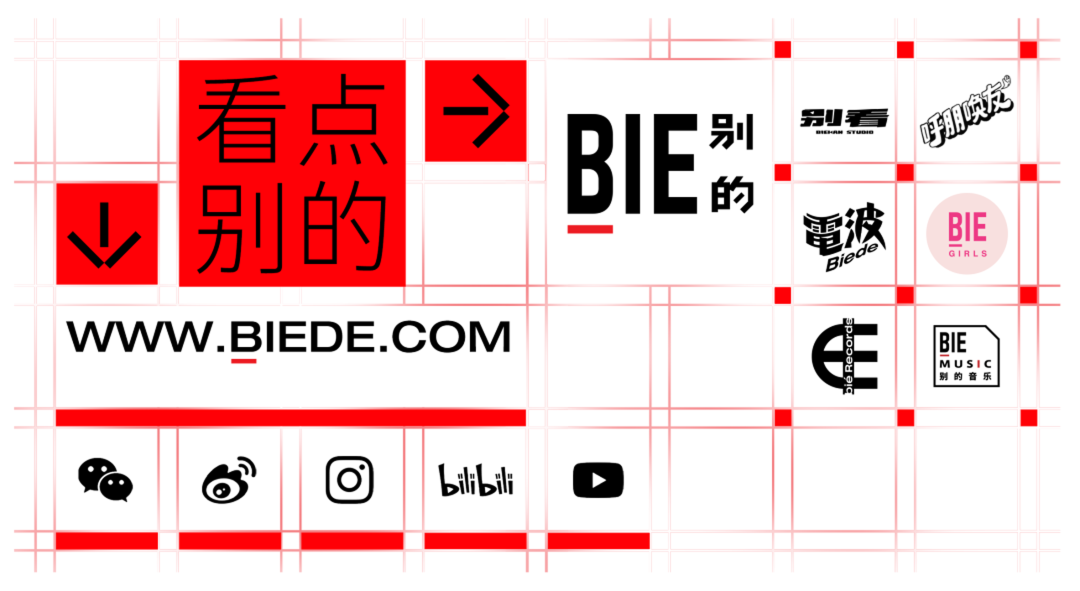“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一向是作家周嘉宁热爱描摹的对象。新作中篇小说集《浪的景观》,开篇即讲述了一群不同国度的文学青年同吃同住,滋生出莫名情愫的故事,遣词造句营造出一种波拉尼奥式的异域气息。作家、诗人、摇滚乐手、记者和电影导演所形成的精神共同体,几乎贯穿了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基本美》呈现了一个 2010 年前后、文艺大杂烩时期的北京,来自香港的摇滚乐手和外省青年歌迷之间真挚而复杂的友谊,被认为带有自传性质的《密林中》刻画了千禧年前后活跃在文学论坛上的文学青年群像,《荒芜城》则描述了聚集在上海小马路旁一家咖啡馆的年轻人们。大学时,我成天独来独往,穿梭于偌大的图书馆和落灰的住处间,第一次读到周嘉宁的《密林中》,内心的震动在“This is not my life”和“I wanna try”间不断往复。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经历的集体生活制式、刻板而压抑,同学间的谈话因乏善可陈而记忆寡淡,以至于我认为大学赋予我的最珍贵之物就是自由,纵使它的代价是孤立。很长一段时间,我真诚地怀疑,这种美好的文艺集体生活是否是真实存在之物,而周嘉宁告诉我,她所书写的,正是自己年轻时的生活和见到的人。出生于 80 年代初的她,文学启蒙很早,高中因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她因此结识了一群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每周一起吃饭,来谈彼此的小说”,直接地指出、谈论对方小说中的问题。大三大四她就搬出了复旦校园,一边写、一边玩,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了 25 岁。她将这段时间称为自己的青春期,就像是一片平原,总能找到小伙伴携手并进,后来面前出现了一片密林,一个群体慢慢变成一个人的状态。我不确定,我们中是否仍有人过着“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那些我在读书时结交的文学青年,彼此都像孤岛,有的在做新媒体,有的进了体制内,还有的像我一样,成了灵活就业的“自由人”,除了偶尔问候一句“最近在写什么”,得到对方“什么也没写”的回复后,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外,交流极少。和周嘉宁交谈的两小时,很难不被她对文学的虔诚和认真所打动,其中包含着她对作家身份的自觉。她的好友,作家荞麦曾在一篇评论中说,有三年的时间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这期间,周嘉宁出版了两本长篇一个短篇集,还翻译了几本书,又练瑜伽又跑步,“要不是被她这股干劲所激励,我大概除了躺在沙发上怨天尤人外将毫无作为。”这些年来,周嘉宁每天的安排都很规律:早晨写小说和翻译,下午看书,晚上出门做喜欢做的事情。她基本不再使用社交媒体,希望能用人物在小说里的行动,去表达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采访中,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周嘉宁习惯以问号的方式来结束。每当触及她认为过于重大而无法概括的事情,都会诚恳而坚定地拒绝谈论,正如她在《一种越过树冠的青天白日》里面写:勤奋也好,才华也好,美也好,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写作的意义也不能被夸大。而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呢——比如彼岸的冒险和滩涂——由于意义过分重大,却无法再轻易地谈论。因为谈论是充满误解的,谈论造成损害。而描述(至少此刻的描述)也是不负责任的。我原本带着对千禧年前后文艺生活的好奇发问,采访终了,“彼岸的冒险和滩涂”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像是一句咒语。这或许就是一个写作者身上迷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