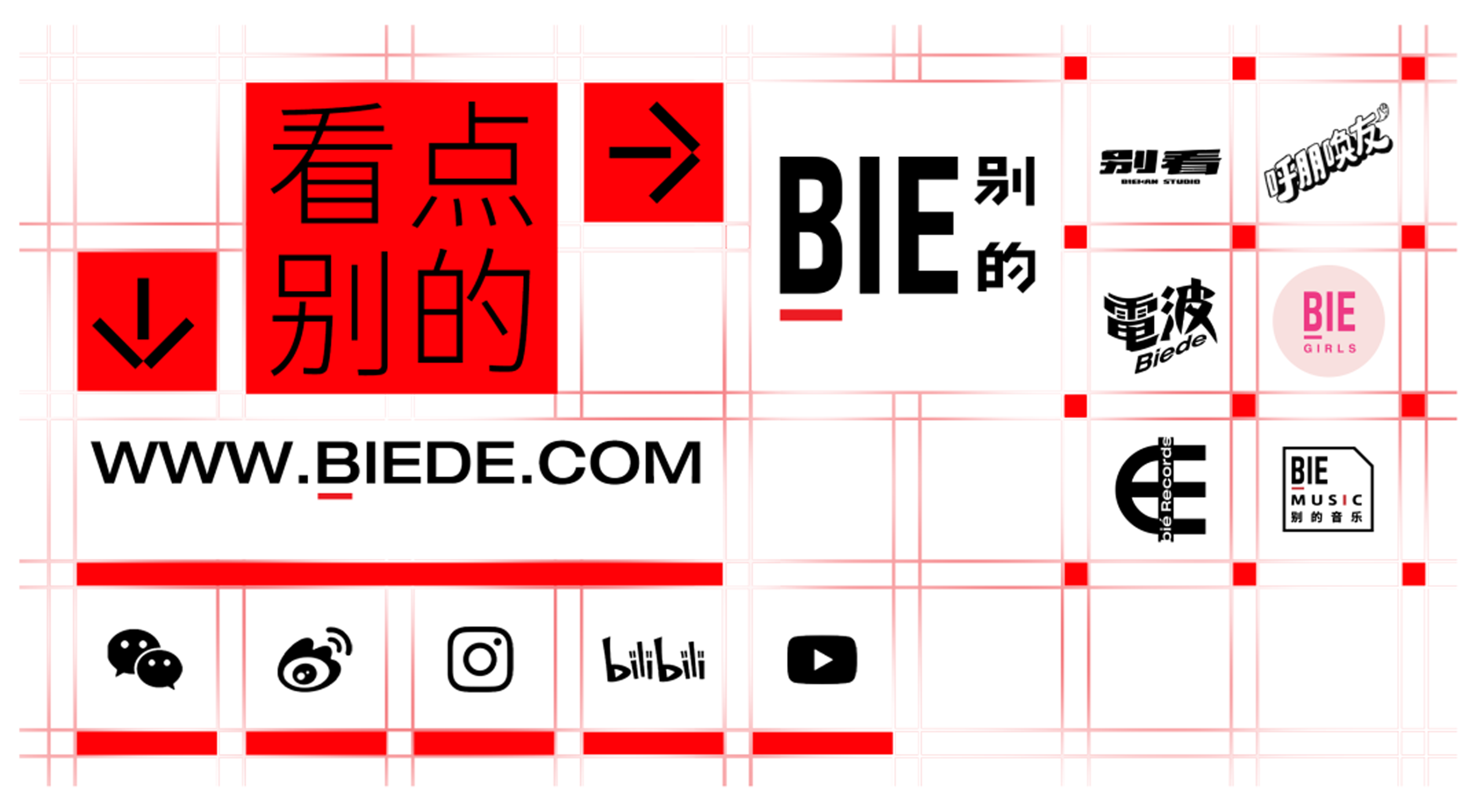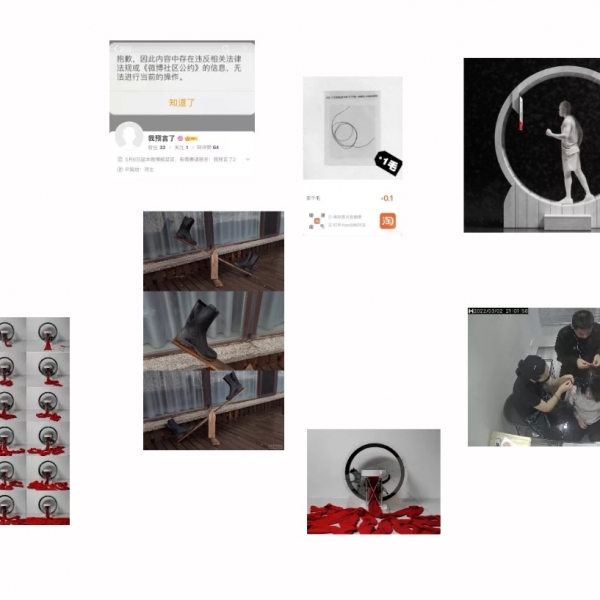40年前的下城:贫穷的年轻人,自由的爱情与行动


2022 年 9 月底,百业萧条,万籁俱寂。一场关于地球另一端文化首都 40 年前之艺术场景的展览即将开幕。去往发布会的路上,心情就像垂死之人赴约十八岁少年的葬礼,更希望是自己躺在坟墓里。这么说有点刻意悲观了,我的意思是,过去几年的艺术萎靡无力,人们正渴求一些真正的能量。展览名为“下城往事”(Somewhere Downtown),讲的是 1980 年代纽约下东区一段无法复制的艺术与文化历史,里面尽是过早燃尽的灿烂生命。当然,还有很多人在世,不知道他们是否像我们一样迷茫。虽说无法复制,但这段另一时空中的往事与今日景象仍然有一些至少是表面上的相似性:当时的美国经济衰退,文化保守主义盛行,环境污染问题与核武器竞赛令人忧心,同时还在经历艾滋病毒的肆虐。而与今天明显不同的一点,大概就是纽约下城这一带的城市景观了。

彼得·于亚尔(1934-1987),《垃圾,纽约》,1985,©彼得·于亚尔档案/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图片由彼得·于亚尔档案和纽约佩斯画廊提供。
第一次见到“downtown”这个词是在中学英语课本上,翻译成“市中心”。彼时我以为它指的是城市里最繁华热闹的一块地方,商铺密集,人流如织。实际上,还是“下城”这一直译更得其神韵。纽约曼哈顿岛靠近南端尖角的一段因为在地图上位置偏下而得名“下城”,再往北就是“中城”与“上城”。至少到 1980 年代末,这里都是纽约最鱼龙混杂的一块地方,三教九流,泥沙俱下。不仅不是中心,还是绝对的边缘之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者漂洋过海,经过自由女神像后在此处登陆,同老纽约的工人阶级们一起居住在这一带密布的穷街陋巷之中。体面人士避之不及,法外之徒求之不得。它之所以能演变出“市中心”的含义,成为日后文艺青年造访纽约时的膜拜打卡之地,正与展览所展现的这一段历史不无关系,那也许是它最后的自由时光,此后便让位于资本的繁荣。
展览场馆 —— UCCA 北京所在的 798 艺术区,曾经也多少是这样一种偏居一隅、无人关注的萧瑟所在。如今已从艺术的诞生地逐渐变成了产品的销售点。经济萎靡时,它也萎靡,与当年的下城恰恰相反 —— 废墟之中,一贫如洗的艺术家们快乐如在天堂。

黄马鼎, 我的秘密世界(My Secret World, 1978–81), 图片来自网络
1978 年,32 岁的华裔艺术家黄马鼎(Martin Wong)从旧金山来到纽约,在下东区 —— 下城东边的一块 —— 一家廉价旅馆里做夜间门僮以换取免费住宿,并在这里度过了纽约的最初三年。日后他画了一幅画来纪念这个简陋的小房间,将之称为“我的秘密世界”。这幅画并未在展览中展出,但画面中透露出的丰富信息恰好能为当年那些艺术家们的生活境况提供一个缩影。黄马鼎喜欢将自己的创作动机小心地嵌入画面,观看时能获得一种在侦探小说或中寻觅线索的紧张乐趣。透过裸露的红色砖墙上的两扇窄窗,我们从外部看向房间,里面有他当时已完成的一幅画作,许多骰子与黑色的 8 号台球,以及一排混合着科学与神秘主义的书籍,其中还夹着一本《无敌李小龙》,和一本《如何赚钱》。这些书目显然经过了精挑细选,我们得以借此了解房间主人的族裔身份、经济状况,以及显然是来自旧金山嬉皮文化的影响。根据窗框上的字,我们知道他正是在这个房间里第一次发明了“听障”绘画,指的正是画面左侧露出半边的由一连串奇怪手势组成的画。这是一种美国手语,每个手势代表一个字母,连缀成词句。将墙上的画中的手语拼读出来,含义是“理疗师证明:恶魔之犬引人杀戮”,说的是 1977 年夏天纽约市一名连环杀手的事。这一幅小小的画足以显示当年纽约下城的疯狂,猖獗的犯罪不仅激发了《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电影,也激发艺术创作。这些经过高度风格化的手势日后反复出现在黄马鼎的绘画中,既像法术秘籍,又像行动暗号。

黄马鼎作品,“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 。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此次展览包含多幅黄马鼎的绘画。海报上那一幅《夏普和多蒂》位于展厅入口,是 KAWS 的私人收藏。纽约典型的褐色砖墙再次出现,左下角,小小的一对情侣正在废墟中相拥,墙面上的窗子似乎也形成了浪漫的节奏。他们是墙上的涂鸦还是真实的人?无论如何,他们本身都是一幅画。
原住民诗人戴安·伯恩斯(Diane Burns)必然也曾从这面砖墙前经过。据说她当年做过模特,总在下东区的街道上游荡,充满魅力,像个明星。在作品《字母城小夜曲》的录像里,她一边溜达一边歌唱自己落魄的景况,声音却无忧无虑。“如果在家里……我会喝着草本茶吃鹿肉……可我在却在 D 大街的街头。” 字母城指的是下东区以北,四条以单个字母命名的街道所围成的区域,像一个乐观的诗人会喜欢的文字游戏。伯恩斯不会在家里,否则她就不会来到这块自由的土地,她为下东区的听众朗读自己的诗歌,下东区正是她的家。然而,在她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这个新家,如同原住民的家所经历过的一样,开始面临被铲除的命运。
第一次遇到“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这个词,我才意识到整饬的街道为什么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也是展览中许多艺术家的朋友卡洛·麦考密克(Carlo McCormick)在一篇关于今日纽约街头艺术的文章中,有更为有力的表述,他说:“我们这么快就忘了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明确教给我们的事情吗?‘有一种比直接的丑陋或混乱更为恶劣的特质,这就是假装有序的虚伪面具,它忽略并压制了正挣扎着想要浮出水面的真正的秩序。’”
同为少数族裔,伯恩斯经常在波多黎各移民的文艺据点“Nuyorican Poets Café”朗读自己的诗歌,波多黎各裔艺术家在下城艺术场景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一定在那儿见过一个一身牛仔装束的亚洲面孔,那就是黄马鼎。从廉价旅馆搬出来以后,黄马鼎在另一个空间 ABC No Rio 认识了波多黎各裔诗人米格尔·皮涅罗(Miguel Piñero)并与之相恋,同时,他也完全爱上了这块在西班牙语发音中被叫做“Loisada”(即“Lower East Side”)的地方。此后,皮涅罗的诗句经常以手语形式出现在黄马鼎的画中。今天,人们只能用“跨界”来生硬地形容这种合作,而当时,界限根本不存在,文学与艺术自然地相互结合,像爱情一样。
在与波多黎各社群密切接触的同时,黄马鼎也怀着极大的热情收集街区墙壁上正大量涌现的涂鸦,在纽约市政清除地铁涂鸦的同时奋力保存这些作品,并将涂鸦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场伟大的艺术运动”。多年间,他积累了来自 Rammellzee、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富图拉(Futura 2000)和李·奎诺尼斯(Lee Quiñones)等人的诸多作品,这些涂鸦艺术家也悉数参加了此次展览。从黄马鼎一个人的经历中就能提炼出下东区艺术场景的诸多关键词:废墟、涂鸦、移民、同性恋、社群、另类空间、爱情、“跨界”、贫穷、自由、行动……而这也正说明这一场景的丰富多层。
第一次遇到“场景”(scene)一词的这种用法,可能是在工作以后,评论家们用它描述特定地方发生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一个场景像一棵树,很难被刻意培育,却经常不可预料地破土而出,展开自己的生命周期。它在生长阶段不断汇聚大量养分,形成无法被人忽视的炫目景观和鲜明特征。孕育纽约下城场景的土壤,是这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大熔炉”特质和无人看管的街区。一种反复被人提及的陈旧观点在此处显得毫无意义,即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奢侈的精神生活发生于温饱之后。破烂不堪的下城恰好证明,贫穷与危机孕育巨大的创造力。下城的艺术家,或者说那些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们,尚未被任何一种“舒适”收买,什么也不怕失去。今日在日益工业化的艺术世界谨小慎微地积累声明与履历的艺术家无幸获得这样的勇气。

查理·阿赫恩(生于 1951),《<着迷>音乐录影带拍摄现场的黛比·哈利和金发美女乐队成员,以及背景中正在创作的李·奎诺尼斯和“妙手佛迪》”,约 1980,艺术微喷,30 × 42 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大概有一个核心词汇能串联起下东区场景的诸多特质,就是“DIY”。第一次遇到“DIY”这个词,可能是在本地报纸的生活版块上,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有助于开发儿童智力的亲子活动。被开发后,我开始改造从表姐那里继承的不太合身的旧衣服,并遭到了同学们一定程度的取笑。从此我便不再这么做了,转而开始学习拼读一些外国品牌的名字。许多年过去,在关于英国朋克文化的介绍中重新见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些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 DIY 跟反抗权威有一定的关系,原来 DIY 的过程让人建立自我。
下城艺术家们某种程度上跟没有新衣服穿的小孩一样,他们没有美术馆空间,没有画廊代理体系,没有策展人和评论家的关注,甚至连创作材料都没有。但同时他们有满街的红砖墙面、废弃的楼房、随处可见的垃圾和疯狂的创作热情,后者让一切闪闪发光。“没有就自己做”,这一简单的想法中包含着将人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魔力,他们因此也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创作自由。
当搞涂鸦的那一批小孩拿起喷枪对准墙面时,没有哪个藏家与权威的声音能决定他们的线条走向。他们是无名之辈,靠着有识别度的图案和图案的出现频率,创造自己的声名。至少当地铁车厢带着他们“狂野风格”(wild style)的签名呼啸而过时,或每一次经过那面被他们标记过的墙面时,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存在。纽约布朗克斯和哈莱姆一带黑人街区中的涂鸦与下东区的艺术场景碰撞出更大的火花,涂鸦四处蔓延,城市景观被自下而上地夺取。

李·奎诺尼斯的手球场壁画《The Lion's Den》, 1982,摄影:Martha Cooper,图片来自网络

“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左侧为伊丽莎白·默里受城市涂鸦启发的作品。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当十八岁的李·奎诺尼斯第一次站在下东区一座手球场中央,面对画布般竖立的球壁燃起喷涂冲动时,他难道不像一个天生的明星来到舞台前吗?促使他完成这一从未有人做过的举动的,不可能是任何策展人的建议,只能是他对自身才华的彻底肯定。手球场涂鸦继而构成下东区景观的一部分,成为黄马鼎的画中画。而地铁车厢的涂鸦甚至为像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urray)这样的学院派艺术家提供了抽象绘画的养料,这一切只会发生在没有界限的城市熔炉里,一万次彬彬有礼的工作室互访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效果。马里珀(Maripol)制片的电影《下城 81》(Downtown 81)中,年轻的巴斯奎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过街区,随时抬起一只手在墙上漫不经心地写下文字,像一个贫穷的王子。影片最后,他说要“到没有光的地方去与自己相遇”,却在角落里亲吻了一名脏兮兮的无家可归者。她变成了仙子,“噗”地一声消失,给巴斯奎特留下一手提箱的纸币。这一百分之百的童话段落在此处却有一些现实主义的色彩:下东区的天才们哪儿也不用去,运气就在自己耕耘过的陋巷里。

查理·阿赫恩(生于 1951),《<着迷>音乐录影带拍摄现场,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和黛比·哈利、“妙手佛迪”等人》,约 1980,艺术微喷,30 × 42cm。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巴斯奎特作品,“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当然,事情本该如此,城市本该如此,只有当资本碾压过来以后,一切才开始变成规则缜密、需要精心计算的游戏。展览中的另一位艺术家大卫·沃纳罗维奇(David Wojnarowicz)将种种社会规范称为“预先安排好了的世界”(pre-invented world),我们都生于其中,而他要做的则是从零开始发明一切,或者也可以说是绝对的 DIY 精神。
沃纳罗维奇在此次展览中占据了重要篇幅,他极其瘦削的身体可能发出了下东区场景中最有力量的声音之一。这名十几岁便在街头做男妓拉客的艺术家,在下东区度过了自己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符合常规的一生。高中毕业以后,他写诗和小说,拍摄电影,组建了一支名叫“3 Teens Kill 4”的乐队(队名直接取自《纽约邮报》上的一则新闻标题,意为“三名青少年杀害四人”),在乐队中演奏儿童玩具并播放现成的磁带采样。他用一切捡来的现成品创作,无论是不规则的木材,还是压瘪的垃圾桶盖,还在广告传单上画露骨的同性色情场面。1980 年代,沃纳罗维奇与其他几名同性恋艺术家一起占领了下城西边一座废弃的码头建筑,把它变成艺术家的狂欢乐园。那些年,下东区的另类艺术空间几乎都跟俱乐部结合在一起,许多场所都像这样靠强占而来。1985 年,沃纳罗维奇入选惠特尼双年展,并开始在主流艺术世界声名鹊起。然而他从未在意过权威的肯定,一次受到委任在藏家努钦(Mnuchin)夫妇家里创作一件装置,他竟然将一堆带着虫子的垃圾搬进这间上流社会的地下室。

大卫·沃纳罗维奇作品,“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在今天看来,如果还有什么能比这些艺术家的“不在乎”更为可贵,就是他们的“在乎”了。无论是城市士绅化,还是开始迅速掠夺生命的艾滋病,下城的艺术场景始终处于巨大的威胁之中。但他们不是渴望与世界共同毁灭的虚无主义者,而是不断抗争的行动派,是 DIY 的第一个大写字母 D。
他们首先在乎的是人,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共同创作的伙伴。当时场景中的艺术家都有强烈的社群意识,相对于鼓励少数富裕精英的虚荣心,他们更在意让艺术通达每一个普通人。约翰·埃亨(John Ahearn)选择为街区的普通人翻模塑像,将之命名为“南布朗克斯名人堂”。戴安·伯恩斯说“哪怕在一个观众面前读诗也胜过所有的一切”。靠着在地铁站里的标志性涂鸦,凯斯·哈林在当时就已经享誉世界,他可以将自己的画卖出高价,但他却选择开设商店售卖 T 恤等商品,此次展览中还能看到他当年为这间商店手画的简朴海报。“让艺术尽可能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将作品)从底座上拿下来,还给人民”,在生命的尾声接受采访时,他曾这样说。

约翰·埃亨作品,“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凯斯·哈林(1958-1990),《无题(长腿的电视)》,1983,木板上迪高荧光颜料。©凯斯·哈林遗产,Artestar 授权,纽约。图片由私人收藏者提供。
主动拒绝权威也使艺术家们更紧密地结合成社群和艺术家小组。当主流艺术世界受富裕白人操控时,少数族裔、女性与局外人艺术家们正是在相互支持的社群中获得了创作的自信,形成与主流相抗衡的声量。1977 年,下城 SOHO 地区“艺术家空间画廊”(Artist Space)的一场群展催生了日后被称为“图像一代”的一批艺术家,包括此次也参展的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劳丽·西蒙斯(Laurie Simmons)、路易丝·劳勒(Louise Lawler)等人。这是美国第一场由女性主导的主要艺术运动。时尚与装饰,报刊杂志和商品广告等大众媒介,以及来自非西方文化的视觉元素开始自由进入作品,打破了艺术的“高低”之分,也为在“极简”“纯粹”“有力”等关键词的笼罩之下散发死亡气息的西方男性艺术世界带来全新的生命力。从展览中看,当年这批女艺术家的创作信息极为明确,却没有沦为干涩口号,反而诙谐生动,散发出前卫的时尚魅力。

萨沙·查尔斯沃斯作品,“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劳丽·西蒙斯作品,“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此次展览中许多艺术家都曾参与的 Colab 艺术小组也是当年场景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在 1980 年占领时代广场,举办了著名的“时代广场秀”,凯斯·哈林、巴斯奎特、大卫·沃纳罗维奇等都在参展之列。相对于今日具有某种自上而下“筛选”性质的展览,“时代广场秀”和当时的诸多同类展览一样,目的是集聚更多的力量,据说,只要听说了就能参与。如果说这些在当时都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日后成为了传奇,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瓦砾中踩出了道路。
1980 年代中期,在席卷而来的艾滋病危机的威胁下,人与人的结合显得更为迫切。许多艺术家加入了力图终止艾滋病危机的组织 ACT UP,靠直接行动或创作来奋力争取公众注意,逼迫官方采取行动。其中,当时已经确诊的沃那罗维奇做出了一系列勇敢的激进行动,他参与抗议时穿的一件夹克在二十多年后再次成为人们的发声武器,在夹克背后,他写道“如果我死了,别管什么葬礼,直接把我的尸体扔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台阶上”。如果他们没有在过去十几年间形成的对人与社群的关爱,对行动的训练,对表达的渴望,对合作力量的确信,以及抛弃一切的勇气,这一场危机会如何结束?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我们面临同样的危机呢?我们不得而知。这次展览令许多逝去的生命重聚,在明亮的展厅里,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作品中的许多也曾肩并肩地在另一时空中出现过。

吉米·德萨纳作品,“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皮特·于亚尔,“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展览现场。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摄影:孙诗
在所有的一切之外,此次展览背景中尤为打动我的是大卫·沃纳罗维奇与另一位参展艺术家皮特·于亚尔(Peter Hujar)之间的关系。于亚尔比沃纳罗维奇年长 20 岁,两人相识之后,逐渐发展出一种如师生、如父子、如爱人的难以名状的感情。一切成熟的工业或理论都喜欢归纳与分类,但真实的生命里只会诞生以往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下城往事:1980 年代的纽约艺术现场” 将在北京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至 2023 年 1 月 29 日。记得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