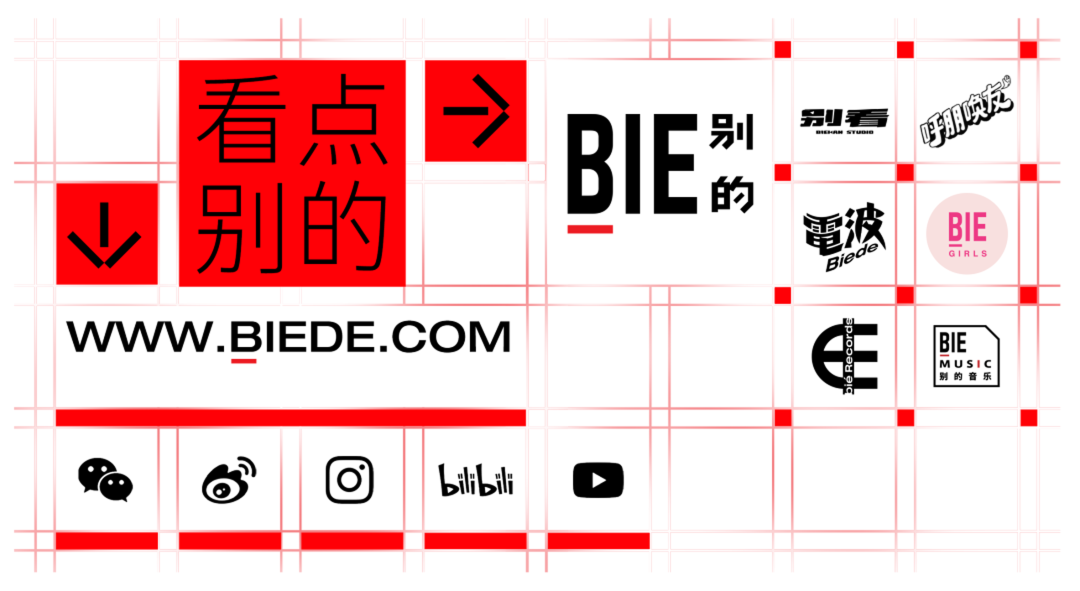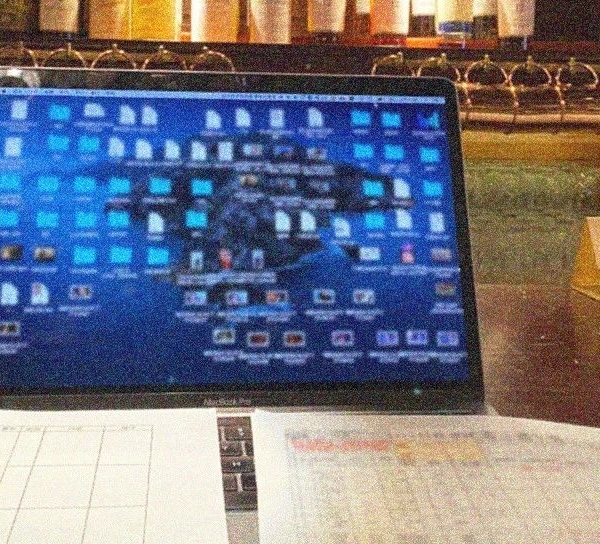导演李睿珺:告诉他们,爱是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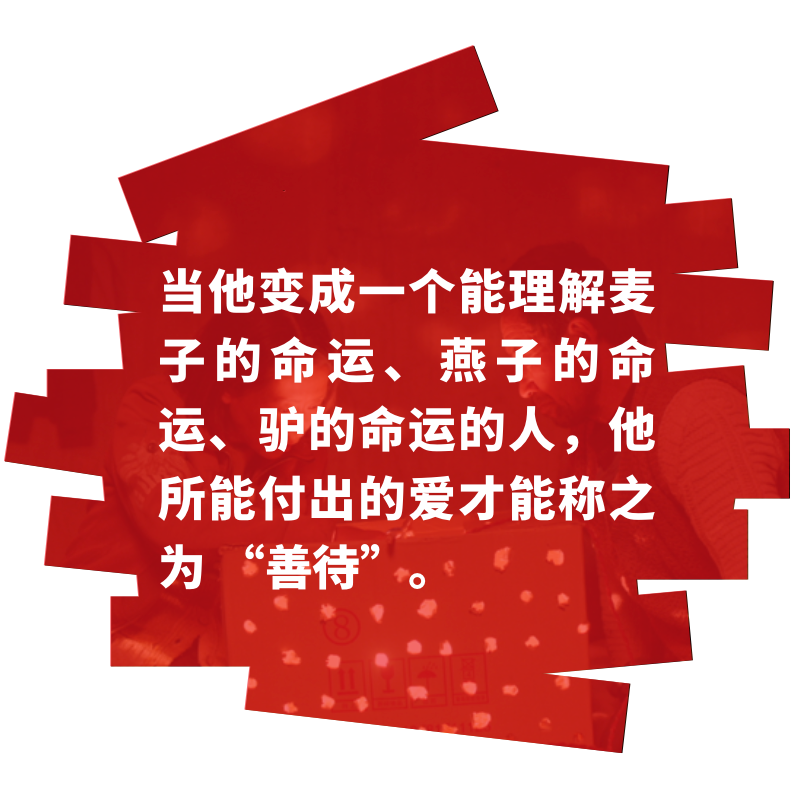

在经历了电影院线漫长的静默期,我们几乎忘了院线还有国产电影可以看、值得看。如今,我们终于等到了李睿珺的《隐入尘烟》—— 这是自2019年后,再度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的唯一的华语声音。几经波折,这部电影终于定档,将于明天(7 月 8 日)正式上映。

《隐入尘烟》海报
李睿珺,这个名字绝非横空出世,从2007年执导第一部电影开始,他的成长轨迹似乎诠释了一种从小镇文艺青年走向电影殿堂的理想路径:一个从甘肃大漠里走出来的青年,受过一些专业教育,拍过几部电影,去过鹿特丹,也去过戛纳,拿过奖,进入过院线,很自然地被纳入艺术电影的第一创作梯队,接受着电影爱好者和影评人们最严厉的审视和期待 —— 毕竟在艺术院线,没有了票房这样的直观评价体系,各种形而上的标准才是最难搞的。
比如人们常常对导演这一职业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创作者的表达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是不断挑战自我的,李睿珺显然对此不买单,纵观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不仅没有离开甘肃,甚至可能没有离开他的家乡高台县。
他往往将他的摄影机放得低一些,让镜头的视野和演员的目光齐平,总是有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招人喜欢的老头,说着铿锵的西北方言,后来我们得知,那可能是他的舅爷爷,可能是他的姨夫,他们当了一辈子农民,又在电影中饰演农民,顺手喜提国际电影节影帝奖杯……李睿珺和他的高台县,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理想的元叙事。

导演李睿珺

《隐入尘烟》中除了女主角启用了专业演员海清,其他角色包括剧图中这个长得和导演有几份相像的男主角,都是导演在老家的亲人和乡里乡亲们

李睿珺是一个很特别的 “凝视者”,他的作品总是少不了对西北农村的临摹。不过他的 “乡土” 没有阴郁的现实质感,而是一种场域 —— 人被置放在其中,和风中的一粒沙也没有多大区别。人与人之间的交手往往利落脆生,他好像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想看的,是人和土地、死亡、神明的关系。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一样,他好像望向人的目光开始变得温和了起来,他开始注视爱情。
“两个被抛弃的人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在彼此身上唤醒了爱和被爱的能力”,李睿珺向在我们讲出这段和不同媒体都反复讲过的故事时,仍旧会沉浸在这样的表述里,仿佛用语言勾勒出画面一般娓娓道来,“他们俩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把那些最复杂的东西全部都扒拉掉,清澈见底的、平静如水的生活情感,一条小河流在静静地流,每遇到一个石头就画一个波纹,每遇到一个树枝就画一个波纹,它起了波纹,起了褶皱,流露出了情感和情绪,这就是生活本身。”


电影中,刚刚在一起的马有铁和曹贵英一起制作孵小鸡的保暖箱,是全片最温暖的画面
电影里有一个小细节:男主角马有铁从兜里掏出小麦,在曹贵英手背上拼出图案,然后摁压了一会,抖落小麦,手上出现了一朵花。看到这样有如孩童游戏般的示爱画面,观影现场所有早已为爱麻木的都市观众却集体心跳漏一拍。一种纯粹的爱意,被童真浇灌的浪漫,就这样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生发出来。
在和导演聊起这一刻的心动体验时,李睿珺导演说,这其实不是他的浪漫小花招,不过是小时候父亲这么给他做过而已。他想说的是,城市里的人们彼此赠送鲜花表达爱意,和马有铁的小麦花本质上没有区别,“生活中看似有很多不公平,但又有很多东西是公平的,比如说爱的能力、爱的可能性。”
平心而论,即使李睿珺有意在克制感情外放,但在电影中马有铁和曹贵英一起亲手制作孵小鸡的保暖箱的那个夜晚,满屋的星光泄漏,那一刻,《隐入尘烟》贡献了年度院线最高明的糖水时刻之一。
麦子不会说话,被践踏了被收割了也不会说话,但土地绝不会厚此薄彼,这是故事主人公从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获得的道理,当他变成一个能理解麦子的命运、燕子的命运、驴的命运的人,他所能付出的爱才能称之为 “善待”。

海清饰演的曹贵英开心地看着手上丈夫送给她的 “小麦花”

在开头我们提过 —— 李睿珺的电影如果可以被总结的话,除了偏执般的地域性,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一位看起来不太好惹的老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一个配合度很高、善于表达的创作者,但几乎可以推断,他和那些老头一样带着某种倔劲,电影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他坚持用素人演员,“用人唯亲” 这个词在他的身上可以说是一个褒义词。对了,一直没有提到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海清 —— 唯一一个专业院校出身的优秀演员,她甚至为了这部电影留出了一整年的档期随叫随到,为了满足导演真实记录麦子在一年里自然生长的样子 —— 何况开机时恰逢疫情肆虐,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李睿珺和海清一开始就摊牌了,戏里男主角要搭非职业演员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对于一个成熟的演员来说,要改变外貌和口音并非难事,难的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她需要抛弃过往的一切专业表演经验和技巧,从下地劳动开始成为一个西北妇女。某个电影节上,海清曾经呼吁 “给中年女演员多一些机会”,很高兴故事的走向很开朗。


海清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不仅学做农活,更是逐字逐句和村子里的女人学习每一句台词的方言说法和发音方式
剧组并不是 365 天都在工作的,而是按照四季的流转顺序拍摄,这一整年的档期,李睿珺做了什么呢?成为他的第二步,是徒手盖房子。片中孤立在荒漠中属于主人公的砖房子,就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在片场一砖一瓦地砌起来的。在电影里看,这个活好像只需要力气,实际上它也很需要技巧。导演在这个过程中一度劳动过度,导致肌肉淤青。至于种庄稼、收获庄稼,所有我们将在电影里看到的劳作,都有他的汗水在里面。

盖房中的李睿珺导演

从零开始造房子
李睿珺坚持,这两个人的故事是从一个寒冬开始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他需要让观众从视觉上看到天气逐渐转暖,他们俩的情感生活也在变好。“开春播撒种子,郁郁葱葱的炎热的夏天,有了肢体袒露和接触对方的机会;到了深秋,收获了满一年的金黄,一切都在变得更好,趋于成熟稳定的状态。稳定之后马上就有一种不稳定,进入到冬天,危险会来临,滑向了另一个枯萎的阶段,生命终结的阶段,这些都是严格的剧情的绘画”。
候鸟的到来、麦子长到什么程度,观众不一定注意到背景深处的日历,但李睿珺严守这个时空的延续性,毕竟,演员在真实的情景里对这一空间的感受和表达,是特效或绿布无法取代的。

他们二人的故事在一场大雪中开场

在盛夏的大雨中达成默契
《隐入尘烟》中大量篇幅都集中在四季劳作中,金色的麦垛堆得高高的,人们弯腰劳作,是一种带着仪式感的日常。有人在其中看到小津安二郎、贝拉塔尔、阿巴斯的影子,都和这种时空感有关,在极其严苛的时空顺序中,长镜头和凝滞的静态,既是叙事,也是反叙事,时间本身会凸显成主题,这反而是这部电影非常激进的一点。

实际上,李睿珺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对他来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以通过太多媒体路径进入公众视野,未必需要他的表达,而理解故土和故土里生长的人,则是一种血脉里的本能。
高台县,通过百度百科可以了解到,这是一个土地面积和成都市区差不多、却只有不到十六万户籍人口的地方,但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这里无意间培养出了中国最好的艺术电影观众,以及非职业演员,当然这必然是李睿珺带来的一种文化上的 “士绅化”。
如果有朝一日你到李睿珺的家乡造访,或许你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公交车上放着他的 DVD,人人都知道那个村子里拍过电影;如果有幸赶上拍摄现场,一个坐在路边抽烟的叔叔,都能给你说上好一会这一幕的 “走位” 和 “出画”。

李睿珺导演在讲戏
一个村子里的小孩,小时候还在寸头光屁股到处乱跑,有一天突然跑去学了电影,然后再回老家就声称要拍电影 —— 一个普通人的电影梦大多起步于此,也可能在众人的冷嘲热讽中,也就很快梦断于此。但在李睿珺的故事里,接下来的走向却充满温情,那些一开始拒绝出演的、看热闹的老乡,偶然间发现原来他说拍电影不是在闹着玩,这个年轻后生真的拍出了名堂,还带着舅爷爷去国外领了奖。电影未必能立竿见影对当下村子里生活产生什么直观的影响,但对他们来说,却是种心理上的慰藉。
“原来我们不难看,我们讲的话也挺好听,我们的村庄真漂亮,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形象在银幕里还能留下来,这一刻就是永恒。”
—— 这才是电影最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