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选择的孩子打棒球|不退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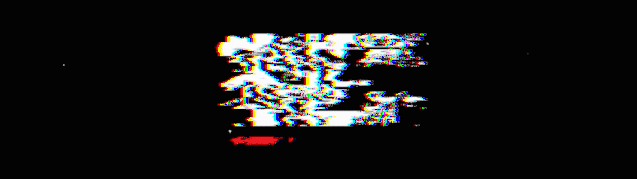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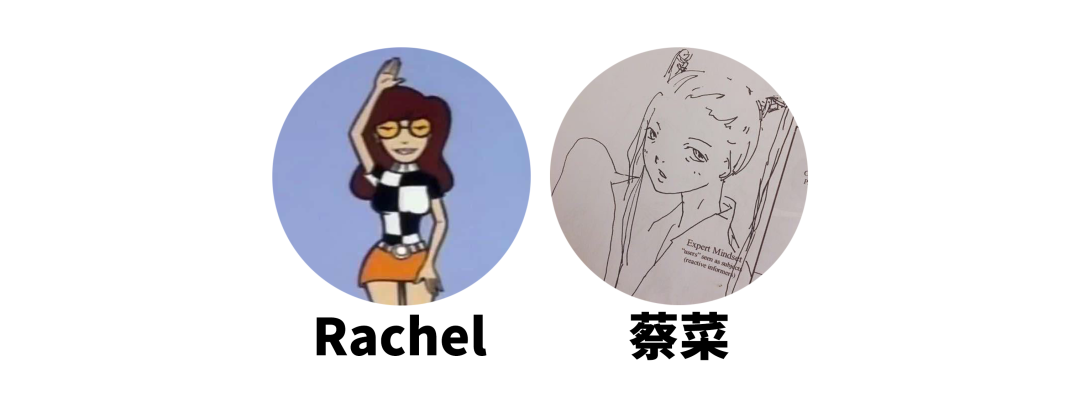
就像很多被滥用的热词一样,“原生家庭” 这个词也难免因过于包罗万象而渐渐失焦,社交网站上八成的使用场景,全是那些热衷于将自己现在的失败往童年往事上归因的城市青年们贡献的。
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总有一些孩子的经历让你不好用 “原生家庭” 这四个字做简单总结,于是你不禁想象:一个来自云贵川村寨的苗人少年、一个来自四川西部自治州的藏族孩子,或者一个来自于任何偏远地区从未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孩子会经历什么?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山高地远的贫穷无力,摧枯拉朽的城市化浪潮将他们的村镇迅速抽成只剩孤寡老小的真空状态,而日夜不休的东莞电子零件工厂早就等着磨平他们长大后养成的性格的各异 —— 造成这种局面的问题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早就超过了家庭单位的范畴,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寂寞的、没有转身空间的命运里,任何能逃离原来生存坏境的可能性 —— 或者只是是虚幻的逃离 —— 都值得全力以赴,他们进入八角笼,成为绞杀别人的战士;将全部青春投入于打出一个全垒打,又或者,仅仅蓄起夸张的杀马特发型,感觉这样,就离那个流水线上穿工服的自己远了一些。
没选择的孩子打棒球
《棒!少年》
北京市郊,棒球场地突兀地坐落在稀疏的楼房中间,一位年逾六十的退休教练坐镇,看着自己面前奔跑着的孩子 —— 他们大多来自贫穷的农村,没机会接受教育,双亲去世、失踪,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令父母缺席,如果不打棒球,这些孩子过剩的精力大多会被消磨在到处游荡、打架和寻衅滋事上。
”如果没有棒球,我现在就是个流氓“,棒球基地的年轻教练们也走过相似的路,这项在国外带有精英意味的运动,对棒球基地的少年们来说,却是孤注一掷的选择。
”我来自十字路口。走丢了,然后就被棒球爱心基地捡到了”。这是主人公马虎的自我介绍,而实情是:马虎的母亲在他儿时就逃离了这个家,至今杳无音信,马虎与爸爸也并不亲密,奶奶讲起这个孩子,只说得出 “可怜”。
另一位主人公小双失去了双亲,自小与伯父生活在一起,缺少关注的成长坏境让两个孩子一个脾气暴烈,初来时跟每个人找茬;一个内敛多虑,不打球的时候喜欢静静坐着,摆弄自己的恐龙玩偶。
跟热血的体育题材电影不同的是,《棒!少年》是一部历时三年完成的纪录片,因此始终蒙着一层现实的灰度。马虎和小双的球技在不断被打磨,但儿时的经历和养成的性格却如影随形,成为埋伏在每个小挫折后的那颗绊脚的石子。
孩子们也没有得到一个甲子园漫画般的结局,在那场他们远赴美国参加的世界级少棒比赛中,一场比分都没有拿下。汗水和泪水并不能带来命运的翻盘,这是他们在沉默中学到的东西。
心事重重的小双受到了打击,回了老家,即便教练几次探访,也不愿重新拿起球棒,而马虎似乎被天不怕地不怕的粗糙和倔强救了一命,仍在不断练习、参加比赛。
该片在 FIRST 电影节首映时,马虎也出现在了映后交流的环节,来西宁玩是训练之外难得的放松机会,可这个平时安分不下来的男孩一直站得笔直,手中捏着自己的棒球帽。
赛博朋克的一曲悲歌
《杀马特我爱你》
你应该不会猜到眼前的这个人是杀马特的创始者,他轻言轻语,满头黑发,纯黑的装扮,只有胸前佩戴的哥特式四角链条透露了些许不同。很难想象这就是传说能号召 20 万杀马特的人。
2006 年,11 岁的罗福兴第一次上网。他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乐手弄了个爆炸头,染成红色,配上铆钉衣、低裆裤,拍了照片。把 smart 翻译成中文,P 到自己的照片上,被千千万万人看到,从此被冠上了杀马特创始人的称号。

杀马特创始人罗福兴 剧组提供

2018 年 10 月,罗福兴(左)和李一凡(右)在东莞石排镇 图片:梁健华
而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三岁起就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打工,但因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他先后寄居在外祖父和祖父家,父亲很少联系他。
杀马特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如同罗福兴一样,成为杀马特的大多是留守儿童,他们十多岁被迫离乡打工,过早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相对于他们五彩、夺人眼球的发型而言,他们的真实生活是灰色且隐形的。


纪录片里的他们坐在工厂内塑料制品流水线上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些机械的动作,高强度 12 个小时连轴转,一不小心就会被机器吞噬掉手指头。麻木的表情和单调的长期工作使他们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而打造杀马特的造型是他们寻求自由、别人关注的方式。
有个女孩说,玩杀马特会碰到很多关心她的大哥,跟她说,“小妹妹,玩这个没有前途的。” 因为缺少正常家庭里应有的关注与关爱,哪怕陌生人嫌弃的眼光也是一种温情。
杀马特那三尺高的头发也是拒绝外界侵入的城墙,他们不欢迎外界人以窥探猎奇的眼神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家族感极为强烈,入 QQ 群前需要视频审查发型满足不满足要求,打字也多半是火星语,就连创始人罗福兴有的时候也读不懂。但这些群成了他们的家,在里面建立兄弟姐妹的纽带,可以互相倾诉,甚至能借到一些小钱来解救窘迫的生活。
“(他们的经历)把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全给翻出来了。“ 早前采访中导演李一凡谈及自己拍摄感想。杀马特是这些受创伤孩子们的保护机制,让他们尝到了家庭般的归属感。幕后的媒体远程采访里,导演李一凡在宾馆里,右手举着一根烟,烟雾缭绕里回答着记者的问题,他语调平静,这个 54 岁的人在好像是通过纪录片表达他对这些杀马特孩子们深沉的关切。
“不管怎么说,都不会比现在好了”。
《年轻人们:铁拳突围》
恩波格斗是一家公益性的综合格斗俱乐部,位于成都郫都区,恩波资助了近百个来自阿坝州藏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孤儿,将他们训练为站上 UFC 舞台的职业格斗拳手。
”你 18 岁,什么特长没有,家里牛没有,地没有,你往哪走啊”,如果不打拳,少年们的一生也许是可预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穿上耐克、顿顿能吃上肉的孩子们会叫恩波 “干爹”。
在 MMA 中拿下五战四胜战绩的班玛夺基无疑是俱乐部里的新星,意外的机会也降临在他身上 —— 任达华导演看中他的眼神,希望班玛能在新片中本色出演一名拳击手。

刚来恩波格斗的时候,不会汉语的班玛因为听不懂公交司机讲话被赶下车,当时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学不会汉语,现在,已将金腰带缠在身上的班玛说,如果不格斗,他可能会去放牛、放羊、做小生意、偷东西,但 “不管怎么说,都不会比现在好了”。
新的妈妈和家
《活着唱着》
因为家里的几辈子人都是学川剧的,川剧流淌在她的血液里。丹丹的家庭穷困潦倒,亲生爸爸差点将她以 1000 块的价格卖给别人,但丹丹从小天赋异禀,光盘上名家的表演,她看一遍就能演下来。

幺妈监督丹丹上妆 图片:《活着唱着》剧组
于是,川剧团团长赵利开始照顾丹丹,丹丹亲切地称她 “幺妈”(四川人指爸爸最小的弟弟的妻子)。两个人的关系不是亲生母女,却胜似亲生母女。一次,丹丹被幺妈发现晚上在酒吧卖唱,挨了三个大嘴巴,一个比一个重。丹丹咬着牙不出声,为得是守护自己的尊严,幺妈打在脸上疼在心里,“你要是不使劲打,就得一直拍,一直打。”
10 年后的今天,电影外,丹丹有了她自己的蜕变。她 18 岁离开剧团,揣着 100 块钱离家出走,现在开设了自己的婚庆公司,有车有房。虽然全职做川剧演员是不可能了,但是剧团成了她分不开的家,她的幺妈,赵利对草根班子的执着劲却像个孩子,始终没变。采访里我问她:“不做剧团去哪儿?” 她操着一口川普说:“没想过,走不动的时候再说吧。”

在电影中扮演幺妈的赵小利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图片来源:trash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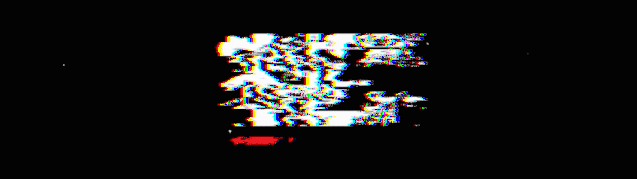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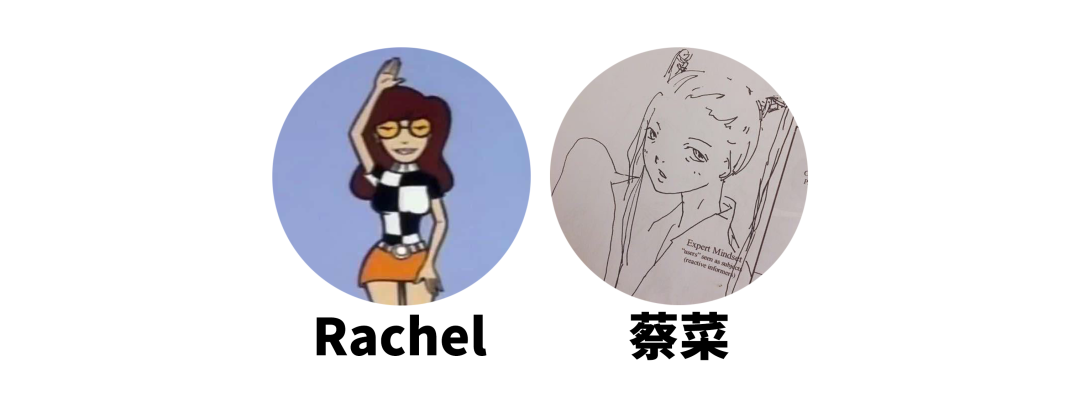
就像很多被滥用的热词一样,“原生家庭” 这个词也难免因过于包罗万象而渐渐失焦,社交网站上八成的使用场景,全是那些热衷于将自己现在的失败往童年往事上归因的城市青年们贡献的。
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总有一些孩子的经历让你不好用 “原生家庭” 这四个字做简单总结,于是你不禁想象:一个来自云贵川村寨的苗人少年、一个来自四川西部自治州的藏族孩子,或者一个来自于任何偏远地区从未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孩子会经历什么?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山高地远的贫穷无力,摧枯拉朽的城市化浪潮将他们的村镇迅速抽成只剩孤寡老小的真空状态,而日夜不休的东莞电子零件工厂早就等着磨平他们长大后养成的性格的各异 —— 造成这种局面的问题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早就超过了家庭单位的范畴,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寂寞的、没有转身空间的命运里,任何能逃离原来生存坏境的可能性 —— 或者只是是虚幻的逃离 —— 都值得全力以赴,他们进入八角笼,成为绞杀别人的战士;将全部青春投入于打出一个全垒打,又或者,仅仅蓄起夸张的杀马特发型,感觉这样,就离那个流水线上穿工服的自己远了一些。
没选择的孩子打棒球
《棒!少年》
北京市郊,棒球场地突兀地坐落在稀疏的楼房中间,一位年逾六十的退休教练坐镇,看着自己面前奔跑着的孩子 —— 他们大多来自贫穷的农村,没机会接受教育,双亲去世、失踪,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令父母缺席,如果不打棒球,这些孩子过剩的精力大多会被消磨在到处游荡、打架和寻衅滋事上。
”如果没有棒球,我现在就是个流氓“,棒球基地的年轻教练们也走过相似的路,这项在国外带有精英意味的运动,对棒球基地的少年们来说,却是孤注一掷的选择。
”我来自十字路口。走丢了,然后就被棒球爱心基地捡到了”。这是主人公马虎的自我介绍,而实情是:马虎的母亲在他儿时就逃离了这个家,至今杳无音信,马虎与爸爸也并不亲密,奶奶讲起这个孩子,只说得出 “可怜”。
另一位主人公小双失去了双亲,自小与伯父生活在一起,缺少关注的成长坏境让两个孩子一个脾气暴烈,初来时跟每个人找茬;一个内敛多虑,不打球的时候喜欢静静坐着,摆弄自己的恐龙玩偶。
跟热血的体育题材电影不同的是,《棒!少年》是一部历时三年完成的纪录片,因此始终蒙着一层现实的灰度。马虎和小双的球技在不断被打磨,但儿时的经历和养成的性格却如影随形,成为埋伏在每个小挫折后的那颗绊脚的石子。
孩子们也没有得到一个甲子园漫画般的结局,在那场他们远赴美国参加的世界级少棒比赛中,一场比分都没有拿下。汗水和泪水并不能带来命运的翻盘,这是他们在沉默中学到的东西。
心事重重的小双受到了打击,回了老家,即便教练几次探访,也不愿重新拿起球棒,而马虎似乎被天不怕地不怕的粗糙和倔强救了一命,仍在不断练习、参加比赛。
该片在 FIRST 电影节首映时,马虎也出现在了映后交流的环节,来西宁玩是训练之外难得的放松机会,可这个平时安分不下来的男孩一直站得笔直,手中捏着自己的棒球帽。
赛博朋克的一曲悲歌
《杀马特我爱你》
你应该不会猜到眼前的这个人是杀马特的创始者,他轻言轻语,满头黑发,纯黑的装扮,只有胸前佩戴的哥特式四角链条透露了些许不同。很难想象这就是传说能号召 20 万杀马特的人。
2006 年,11 岁的罗福兴第一次上网。他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乐手弄了个爆炸头,染成红色,配上铆钉衣、低裆裤,拍了照片。把 smart 翻译成中文,P 到自己的照片上,被千千万万人看到,从此被冠上了杀马特创始人的称号。

杀马特创始人罗福兴 剧组提供

2018 年 10 月,罗福兴(左)和李一凡(右)在东莞石排镇 图片:梁健华
而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三岁起就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打工,但因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他先后寄居在外祖父和祖父家,父亲很少联系他。
杀马特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如同罗福兴一样,成为杀马特的大多是留守儿童,他们十多岁被迫离乡打工,过早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相对于他们五彩、夺人眼球的发型而言,他们的真实生活是灰色且隐形的。


纪录片里的他们坐在工厂内塑料制品流水线上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些机械的动作,高强度 12 个小时连轴转,一不小心就会被机器吞噬掉手指头。麻木的表情和单调的长期工作使他们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而打造杀马特的造型是他们寻求自由、别人关注的方式。
有个女孩说,玩杀马特会碰到很多关心她的大哥,跟她说,“小妹妹,玩这个没有前途的。” 因为缺少正常家庭里应有的关注与关爱,哪怕陌生人嫌弃的眼光也是一种温情。
杀马特那三尺高的头发也是拒绝外界侵入的城墙,他们不欢迎外界人以窥探猎奇的眼神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家族感极为强烈,入 QQ 群前需要视频审查发型满足不满足要求,打字也多半是火星语,就连创始人罗福兴有的时候也读不懂。但这些群成了他们的家,在里面建立兄弟姐妹的纽带,可以互相倾诉,甚至能借到一些小钱来解救窘迫的生活。
“(他们的经历)把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全给翻出来了。“ 早前采访中导演李一凡谈及自己拍摄感想。杀马特是这些受创伤孩子们的保护机制,让他们尝到了家庭般的归属感。幕后的媒体远程采访里,导演李一凡在宾馆里,右手举着一根烟,烟雾缭绕里回答着记者的问题,他语调平静,这个 54 岁的人在好像是通过纪录片表达他对这些杀马特孩子们深沉的关切。
“不管怎么说,都不会比现在好了”。
《年轻人们:铁拳突围》
恩波格斗是一家公益性的综合格斗俱乐部,位于成都郫都区,恩波资助了近百个来自阿坝州藏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孤儿,将他们训练为站上 UFC 舞台的职业格斗拳手。
”你 18 岁,什么特长没有,家里牛没有,地没有,你往哪走啊”,如果不打拳,少年们的一生也许是可预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穿上耐克、顿顿能吃上肉的孩子们会叫恩波 “干爹”。
在 MMA 中拿下五战四胜战绩的班玛夺基无疑是俱乐部里的新星,意外的机会也降临在他身上 —— 任达华导演看中他的眼神,希望班玛能在新片中本色出演一名拳击手。

刚来恩波格斗的时候,不会汉语的班玛因为听不懂公交司机讲话被赶下车,当时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学不会汉语,现在,已将金腰带缠在身上的班玛说,如果不格斗,他可能会去放牛、放羊、做小生意、偷东西,但 “不管怎么说,都不会比现在好了”。
新的妈妈和家
《活着唱着》
因为家里的几辈子人都是学川剧的,川剧流淌在她的血液里。丹丹的家庭穷困潦倒,亲生爸爸差点将她以 1000 块的价格卖给别人,但丹丹从小天赋异禀,光盘上名家的表演,她看一遍就能演下来。

幺妈监督丹丹上妆 图片:《活着唱着》剧组
于是,川剧团团长赵利开始照顾丹丹,丹丹亲切地称她 “幺妈”(四川人指爸爸最小的弟弟的妻子)。两个人的关系不是亲生母女,却胜似亲生母女。一次,丹丹被幺妈发现晚上在酒吧卖唱,挨了三个大嘴巴,一个比一个重。丹丹咬着牙不出声,为得是守护自己的尊严,幺妈打在脸上疼在心里,“你要是不使劲打,就得一直拍,一直打。”
10 年后的今天,电影外,丹丹有了她自己的蜕变。她 18 岁离开剧团,揣着 100 块钱离家出走,现在开设了自己的婚庆公司,有车有房。虽然全职做川剧演员是不可能了,但是剧团成了她分不开的家,她的幺妈,赵利对草根班子的执着劲却像个孩子,始终没变。采访里我问她:“不做剧团去哪儿?” 她操着一口川普说:“没想过,走不动的时候再说吧。”

在电影中扮演幺妈的赵小利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图片来源:tras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