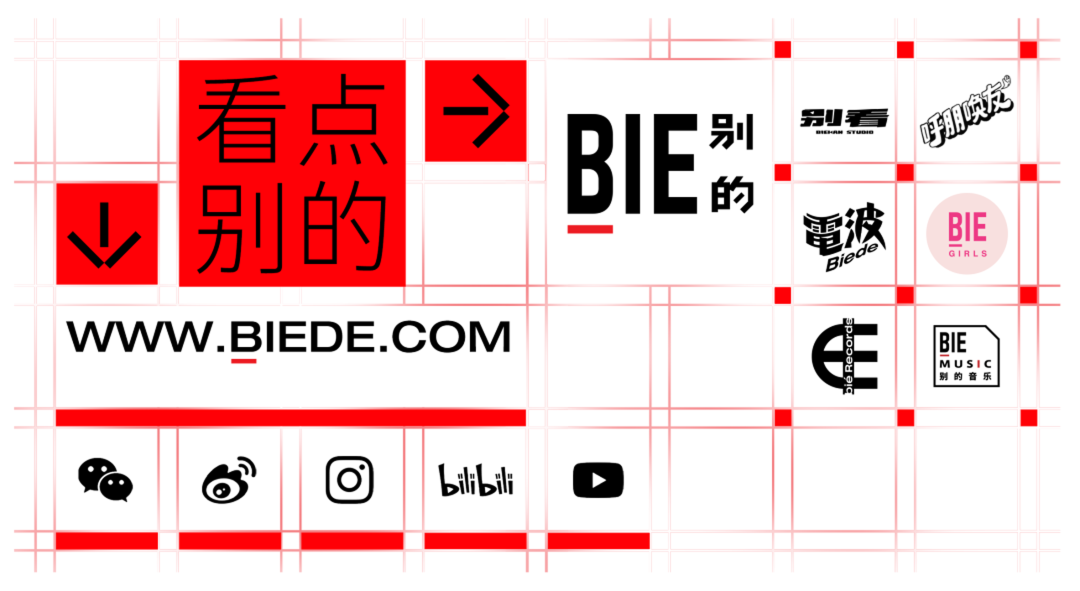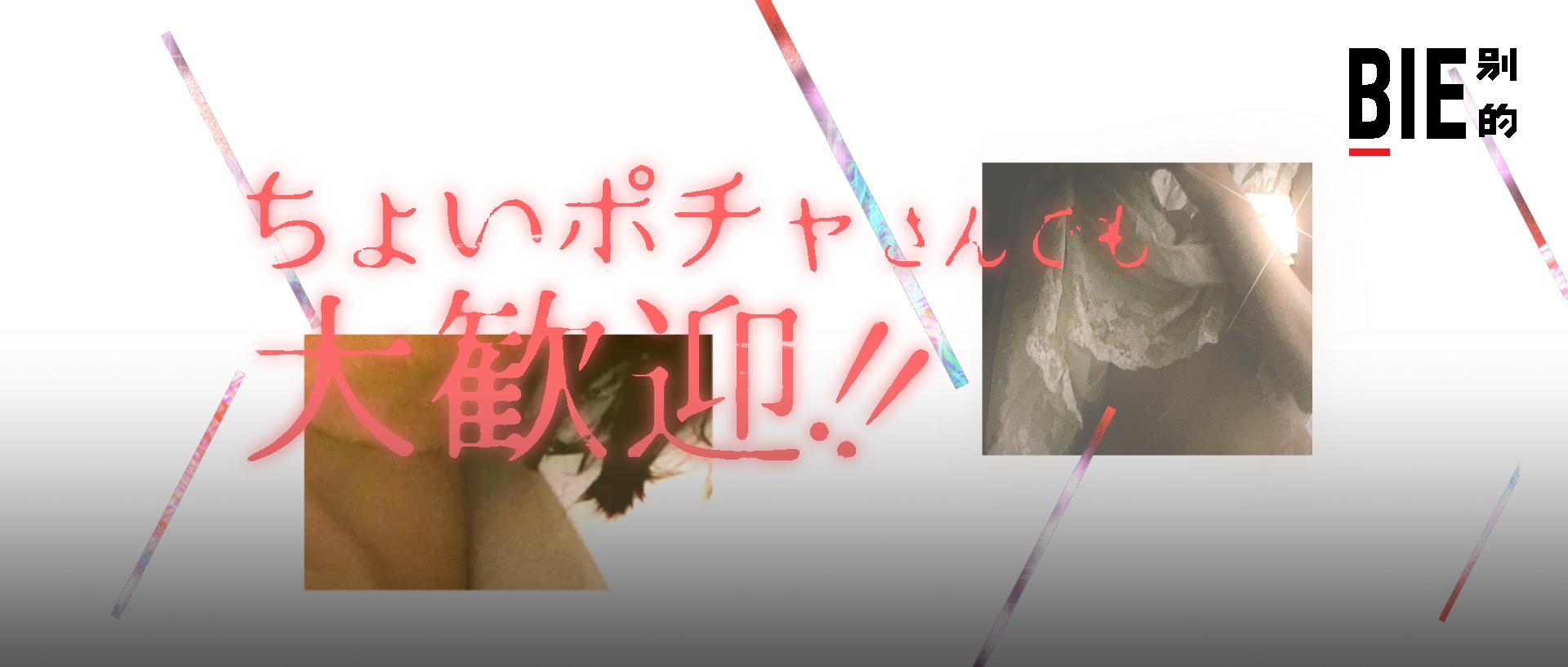
去日本风俗店应聘后发生的事,和我想成为风俗女的理由


编者按
这是「红灯区打工日记」的第二篇。在上一篇文章中,作者记录了她第一次去摸摸酒吧面试时经历。当时的店主在拒绝她时,提醒道:“如果有愿意让你去的店,也不会是正规店,去那种店工作很危险的。” 只是没想到时间距离第一次面试还没有过去 24 个小时,这句话就得到了应验。今天的故事,就从当天晚上要迎来的那场风俗店面试开始。
注意,本篇内容可能触发创伤性记忆,请酌情阅读。

因为某种理由而一心想去日本的风俗店打工的我,现在正站在樱花小道的中央。这里即使在歌舞伎町也算是红线地带。
周围都是招揽着客人的风俗介绍所,泡泡浴店,以及如今已经不多了的店铺型风俗店,偶尔还有中餐馆掺杂其间。顺带一提,这里有一家非常好吃的中华料理,是池袋以外为数不多能做出味道正宗的毛血旺的店。
彼时是晚七八点,我按着邮件里给我的地址走去,停在一座规模颇大、一层看上去像是小钢珠赌博店的建筑面前。墙上到处是花哨的贴画和电子屏幕,向来胆子很大的我突然不敢多看这里一眼,只是埋头朝着昏暗的电梯间走去。
楼上是一片事务所模样的地方,门的左侧有沙发茶几,右侧是一条走廊,里面有好几个女性正在匆忙往哪走去,她们中有日本人也有东南亚人。走廊靠近我的一侧还有两个男性正在一个半开放式的房间里,有人在接电话。听起来像是客人预约风俗服务的的电话,男人正对着电话那边询问您想要定多长时间的服务。
我朝着那个没有在接电话的男性说明了来意,对方看看我,说,哦,是预约了面试的 xx,这边的房间请坐。这样说着,把半开放房间里的帘子拉下来了。
我们简单交流了我的年龄,称呼,这时接电话的那人也结束了通话,在一边坐着看我们。
和之前几家陪酒的店不同的是,我并没有立刻接到需要填写的表格。负责面试的男性询问了我的基本状况后,便看着我,点点头,对我说:“那么脱吧。”

“脱吧。”
“唉?”
樱花小道一处风俗事务所内,用布帘隔开的房间里,负责面试的男子,用并没有在开玩笑的认真表情对我说,脱吧。这让我吓了一跳,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
愣了下,我又想起来,对哦,这里是风俗店,贩卖身体的地方,如果身上的肉不够性感的话是卖不出钱的吧。考察商品质量……或许应该这样称呼这场面试。
我至今也没有几次在别人面前裸体的经验,突然被说 “脱吧” ,确实是在这几天的求职经历里第一次被吓到了。虽然非常不好意思,但仔细一想,这也是自然的事。
“就在这里脱吗?” 过了一会儿我缓缓问道。
对面点点头,转身帮我把布帘子又拉紧了一些。于是我站起来,开始脱衣服,今天穿的是短袖的上衣,下半身是蓬蓬裙,我先把上衣脱了,这才想起来,虽然穿了可以显胸型的漂亮内衣,下半身却是不成套的旧内裤。
我脱掉裙子,对面的人却没有什么反应,像打量超市里的肉一样平静地看着我。我问,“还要继续脱吗?”
“是的,内衣和内裤都要脱掉。然后请慢慢转一个圈。” 面试官的语气依然平静又柔和,公事公办地说道。
所以我脱掉内衣,露出不太好看的胸部,脱内裤的时候,动作很奇怪又笨拙,毕竟我也实在不知道如何脱内裤脱得好看,只是尽量把旧内裤脱下后立刻叠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藏进脱下的衣服里。
唉,裸体的感觉好奇怪。但不知为什么,并没有什么羞辱感,也没有想到这是刁难或者欺负。那时候我脑袋懵懵的,光是想着自己的身体很丑了,接着才能想到现在在被异性观看裸体。要说不舒服的感觉,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基本被脑袋一片懵着的呆滞感盖了过去,尤其是布帘外面还有熙攘往来的人声。
头脑里净是 “自己一定看起来脏兮兮的,到处都很丑吧” 的想法。我发了一会儿呆,可能也就几秒钟,然后按照对方的指示慢慢转了一圈。

再次面对两个男性面试官,我呆着,刚想起来是否应该面露微笑的时候,对面那个刚刚接电话的光头胖乎乎男性说道,“你身材挺好的呀。”
“啊?什么?”
“说你身材挺好的。style,style 不错。”
“呃……请问 style 指的是……?”
因为对方的话太过不可思议,一下子我都忘了日文,或者说日式英文里的 style 是什么意思,像个笨蛋一样呆呆地重复问话。这下搞得对面的光头面试官都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烦躁地挠了挠光头,然后用手凭空比划,身体曲线的样子。
“你个子高又很瘦,style,身材不错。”
“真,真的吗?!谢谢!!”
我突然大声起来,一下子差点忘了还光着身体,第一时间对人道起谢。真是不敢想象,我居然会有被人说 “身材不错” 的一天,而且还是真心实意的!我高兴地连怎么在这个场合里重新穿上衣服的过程都忘记了。
在我原本的预料里,我大概会因为胸太平,或者肤色不够白而被直接 pass 掉。可结果出乎意料。这句 “身材不错” 好像是我人生中收到过的最高级别赞美。我可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说身高高是优点。他们会夸一个女孩可爱,另一个漂亮,还有一个不可爱也不漂亮的就说是模特气质,这点似乎到处都通用,我在国内也是被这么评价的。但现在这句 “ style 不错”,肯定不是虚假的恭维。
因为他们是风俗店的面试官,他们在打量商品。没有价值的商品对于这风俗店来说,并没有去勉强吹捧的必要。在这个场合下说出的话,只有这句,是绝对没有在骗我的。
这一幕于我来说犹如梦想成真一般令人欣喜。夸张地讲,我一下子感到我至今二十多年灰头土脸的人生变得闪闪发亮了。一定会有读者看到这,觉得我很可笑,或者怀疑我智力有问题。
我当然也知道世上比外貌更有价值的事物多了去,即便是我自己在选择尊敬的人和友人时,我首先考虑的也是公正,良知,诚实,冷静,正义感。我认为只有那样的人才是很好的人。但是我并没有想成为很好的人,我想要的只是……
对我自己来说,现在无论如何我就想要这个,我知道我想要的就是这一句肯定本身。
我想成为风俗女的原因,就是期望得到肯定。即使那本该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肯定才对。

我迫切想要外貌上的肯定,和我从小因为相貌被嘲笑,这好像并不矛盾。别说被夸奖外貌了,一直以来因为太丑,我简直没过过所谓 “普通” 的人生。
我皮肤黑黄,眼睛又细又小,高颧骨,全身骨关节处处比人明显,天生头发少。加上比别人早读书两年,自小学起,不佳的外观和笨拙的性格,使得我成为了每个班级都会有的那个被欺负和霸凌的对象。我被当成脏东西,其他孩子走路绕着我,路过操场可能被树的果实、石子,或者足球篮球故意朝着脑袋丢。我说话会引起怪笑,或者被无视,所以没有人敢和我对话,尤其是男生,这会让他们成为全班人嘲笑的对象,一起被打入霸凌对象的行列里。
当时班级里欺负地位最低的男生的法子是,几个男生按着他,然后几个男生按着我,用尺子强行捣进嘴里取我两其中一人的唾液,再混在另一人嘴上。意思是和我间接接吻了,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大的屈辱和惩罚。
对于那时的霸凌,老师和家长都不予理会,再加上那是一所寄宿制学校,能躲的地方都没有。我有时候被锁在阳台过夜,有时候在厕所里洗漱,不允许使用外面敞亮的洗脸台。因为我是丑八怪,不能和其他女孩用一个洗脸台 —— 看同寝女孩们的说法和表情,就好像我会在洗脸池大便。我过不下去的时候,哭着给家里打电话说求求接我回家,但是没有人理会,我就只能在这里继续过下去。
现在的我当然知道这些事不对劲,这是不公平的,但凡有大人愿意介入,我立刻就能得到公道和正义。但那时我是孩子,只要没有人愿意伸手保护我,“这里” 就天然是一个几近不可撼动的封闭世界,在小小的学校里孩子们自发建立的扭曲规则,就主宰了其中所有孩子的命运。
率领其他学生欺负我的是几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带头的女孩有着微卷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像个小天使一样。不管是老师还是同龄人都喜欢她,即便当她率领其他孩子打我,争夺我的点心,推着我的头往墙角上撞时,也不会有人阻拦。
其实,不该打人,不该抢人东西,这些道理哪怕是孩子也明白,比如最早些时候我还会试着反抗,推开他们时,他们也记得用我打人了的名号将我状告给老师。不只是狡猾或者恶人先告状,他们真的觉得我打人,很坏,惊讶于我居然敢把人用力推开。但是一旦打我的是那个漂亮女孩时,这些刚刚萌芽的善恶标准又好像突然从他们脑中被本能的好恶所根除了,他们不会觉得她很坏。
于是,当时我的心里懵懵懂懂留下一个想法,“可爱就是正义”:原来只要长得好看,又受人喜欢,就可以干任何事,然后依然受人喜爱。这里的“喜爱” 不只是狭义的恋爱,也不只是广义的好意,还有人本该拥有,但我那时未能得到过的被平等和公正对待的权力。是那些基本的,保证一个人在这世上幸福地活下去所需要的一切。
中学以后我换了一个环境,努力读书,考不错的成绩,来取得 “学校规则” 里属于老师的那部分偏爱,好避免被欺负,一边又悄悄学习穿衣打扮。即使成绩再好,我还是会不安,我觉得不够。在我心里,取得幸福的唯一保证,仍然是被人所爱这一条。
在证明自己确实值得得到更多人的爱之前我不会停下。哪怕我知道童年时代的 “恶” 大多会在他们长大承担起生活的重压之后得到驯服或伪装,但是我不敢停下来。再后来我去大学,已经不会再有人对我的外貌评头论足,我也因穿衣打扮得到过同寝室女孩的小小夸奖。但是这也不够。此时我已并不相信那些夸奖是真实的,即便是过去因为真心觉得我丑陋而欺凌我的孩子,在成人后依然可以随口对任何人抛出赞美。
我不相信人,所以我不相信任何口头上的赞美,顺口一说的东西谁都会。我需要一个夸奖者付出作为筹码的代价,那就是钱,真金白银的钱。

钱是世间通用的用来衡量价值的贵重之物。所以只有当有人愿意为我的脸,或者我的身体花钱,我才能确认自己是真的值得被人所喜爱。
虽然,现在我只是被风俗店的面试人员说了身材不错,但是我还是为此高兴不已,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了好几次谢谢。
虽然,最后的面试结果依然是因为考虑到雇佣留学生的风险而决定不采用,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么失望了。毕竟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一小半,接下来只要继续去找其他店……继续寻找可以承认 “我值得” 的地方就好了。
光头的员工说要送我下楼,我也没有多想,被陪同的路上只是思考下一家 girl's bar 的面试,心里多少更有底了。
第一次得到的认可让我骄傲到有些飘飘然,以至于开始在心里不着边际地想着 —— 如果有一天,有客人愿意出钱买我一个亲吻,就算只出价五十人民币,不,就算只给五块人民币,哪怕是五角,我也想答应这个人。五分可能有点困难,怕不是在笑话我。
我想着这些漫无边际的事,但意料之外的是,送我走下楼梯到门口时,那位光头的员工突然小声对我搭话:
“因为你是留学生,所以像我们这种大规模的店没法雇佣你……” 他示意我凑过来,小声对我说道,“但是我还在做其他店的中介,如果是规模小一些的店,我可能能帮你介绍一些门路。”
我一听这意料外的话眼睛就亮了,对,我就想着既然是风俗业,总有那种不守规矩的店才对,只可惜我一个外国人找不到门道,没想到机会就在眼前。听到这样的邀请我如获至宝,“真的吗?唉,没事吗?那可以拜托您帮我问问吗?真是太感谢了!”
我说得颠三倒四,同一个词义重复了好几次,对方点点头,没有对我兴奋起来就很糟糕的日语做什么评价,一副依然很冷静又职业的样子,对我说道:“那你加我的 line 吧,然后明天有空吗?我们再来面试一次,我也找几个店介绍给你。”
我们交换了 line ,约好了明天再在新宿的咖啡厅见面,之后就解散了。那天我好开心,就连夏天的晚风都好像比平时多了些快活和令人期待的味道。走出几步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隐晦地在 sns 上宣布:不愧是我,我好像要有新人生了。
我好像马上就可以清算以前的不公,变成 “值得” 的人了!
为了庆祝,我还去了新宿西口的青梅小道里常去的那家小烤串店,急匆匆地对熟识的客人们报告喜讯,我很可能 —— 这是我的自谦 —— 即将出道成为 “闪闪发亮的歌舞伎町新人”。夏夜的半露天烤串店里十分热闹,我拿着冰啤酒和认识不认识的人碰杯,为了庆祝一下,还点了平时不舍得点的葱烧烤肝。
最后,我不好意思地说还要准备明天的面试,比平时更早一些,在最终电车到来的很久之前就结账回家,好好睡了一觉。睡前不忘确认 line 上光头男子发来的联络,并且感谢了对方今天的关照。

第二天早十点,我按照对方的联络,来到了新宿车站碰面。因为搞不懂日本人惯用的形容车站出入口的好几个标志性名称,我一边和光头男子 —— 就叫他阿吉吧 —— 打着电话,一边找了十多分钟的路才找到。
我早上八点便起来化妆,早饭只吃了营养果冻,照样穿着昨天面试时的白色蓬蓬裙洋装,我自认为拥有的最可爱的一套衣服。尽管后来才知道,对于风俗女来说,这种着装品味太 “二次元” 了,不像一个具有魅力的 “现充”。风俗女的标准着装是名媛风连衣裙。
因为迷路而迟到了,我连连道歉,但是对方随意地挥挥手表示没事,对我说,“我们走吧。”然后带着我又进了车站。
“咦?不是说在咖啡厅面试吗?”
我困惑起来,并且第一次开始起疑。有些奇怪的是,除了阿吉之外,也没见到其他风俗店的人员。
“店铺那边有点变动,你的情况确实有点困难……”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所以结果怎么样?”
“没事,我们先两个人面试,完全搞清楚你的情况之后我也比较好和店方沟通。风俗有很多业种,比如店铺型和派遣型,还有服务流程啊,各种额外付费服务啊,也得先搞清楚你能做哪些。”
我点点头,表示大概了解这些,跟着对方进了车站,又去搭乘新干线。路上阿吉说了一些新宿车站周边的趣事,大概和我聊了些日本人遇到外国人时的常用话题,旅游,饮食云云,我一边回应,一边留着心眼,抬头看列车开到哪里。
就在下一站,新干线停靠新大久保站时,阿吉便对我说,下车吧。
新大久保,我对这里的印象便是满街的中华物产店和韩国料理店,街上飘的更多是中文和韩语,而非日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相比新宿没有那么高档,鱼龙混杂的风俗店,与隐蔽的各处情人旅馆。日后我与一个交友 app 上遇到的 “潜在客户” 男人约见面地点时,我提起新大久保,对方立刻装模作样地说,我不去那种脏兮兮的地方。
只不过我一直生活在留学生圈子之外,彼时对于新大久保远没有更多在日华人或留学生来的熟悉。
阿吉问我,“你是第一次来新大久保吗?”
我立刻说,“不是。”
然后又装作很熟络这里地形的样子说了句,“您不知道吗?这里到处是中国人,我也经常和朋友们来这玩哦。”
这自然是我说谎了,就好像去到在陌生城市时,绝不会说自己是第一次来,以防宰客,又或者那种在晚上上出租车之后给朋友挂个电话,佯装有人来接自己一样的惯用伎俩。现在说来可能没有人信,我的防人心没有那么轻,有的时候我确实有不对劲的预感,而且这种预感往往只多不少。但是意识到是一回事,意识到有危险之后,我采取怎样的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我看着新大久保车站边的街道,继续借着话题说道,“我有几个朋友,也是中国人,在这附近开纹身工作室,我的纹身就是在那做的呢。”
我说笑一般指指自己胳膊上,昨天面试脱衣服时也曾露出过的花臂纹身。我的小伎俩就到此为止了。
阿吉沉默了一些,打量着我的纹身点点头,换了话题,和我聊起来新大久保的一些琐碎事情。然后对我说,接下来去那边的旅馆,他是那边的长住客,在旅馆开了个房间,当做自己家来使用。
特别提示:以下内容有可能会引起强迫性行为相关的创伤反应,请在可以保证自己完全安全的情况下再选择是否阅读。

走进旅馆里,果然如阿吉所说,他不用和前台打招呼,就径自上楼了。自然不是什么连锁上午旅馆,但一眼看来也不是过分夸张的情人旅馆,普普通通的。
进门后阿吉脱鞋,我也脱鞋,想了下,把两双鞋都摆好了。这是我以前自己去女性向风俗学到的。于是阿吉转过头来,有点惊讶地看看我,笑了,说我一看就家教很好,有做接待业的天赋。
我也只好笑着,然后问,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接下来应该帮客人挂衣服,就像这样。” 阿吉说着面不改色,开始脱自己的衣服,一下子就有别人淡淡的体味传了过来。然后他把还热乎乎的衬衫交给我,指导我该怎么挂上。然后对我说,你也把衣服脱掉吧,我就脱了上衣和短裙,阿吉像是他教我的那样把我的衣服也挂好了。
“这时候可以问问客人,今天天气如何啊,空调的温度怎样,一类的话。毕竟是接待业嘛。—— 哦,对了,空调这个温度可以吗?”
他打开空调,我点点头说可以,没问题。
阿吉继续道:“接下来,虽然各个业种有点差别,但总之都要先一起洗澡,你帮客人洗澡。”
他说着脱掉内裤,我看到一个东西在眼前晃荡,稍微别开视线,视线一角看到阿吉把裤子放在床上了,然后走进浴室。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传来阿吉调节着水温的声音。我想到我应该也得脱吧,然后就听见阿吉对我说,“你也脱好了衣服然后进来,实际上是得你先进来调水温的。”
“对不起。” 我说着又慢慢脱掉衣服,在完全封闭的房间里,只有自己和陌生人的情况下脱光衣服,当然会让我充满恐惧。比起昨天的面试,我现在非常清晰地有不好的感觉。我自然在网上,一些风俗女的推特里看过风俗店员会借着新人指导的名义干的破事,但是又想万一我真能得到这份工作呢,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性,我现在也会努力试试看。所以我把脱掉的衣服放好,然后也进了浴室,尽量把视线保持在干净的位置,目光只追着阿吉的脸。
莲蓬头在一边放着水,阿吉手上涂满沐浴露,打起泡沫,然后糊在自己身上,又伸手糊到我身上。滑溜溜的,我心想这不必要吧,又不会有客人给风俗女洗身体,一想倒也不绝对,但是依然掩盖不了这个场景的荒唐。
他问我身体哪里感度如何,我就像答记者问一样报备,其实全都是没感觉,没感觉。我说老实话,对面又看我的脸,又低头看我的身体各处,涂着沐浴露泡沫,嘴巴张着,好像一个烟囱,只露出两片嘴唇间一个洞,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阿吉问,“你要摸摸这里吗?”
我说,“呃,为什么?”
于是阿吉作罢,换了个话头,“总之,洗澡的时候应该像这样先在自己身上涂泡沫,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去洗客人的身体。” 阿吉还在继续指导着,并且还用实践模拟出来。重复了一遍对我说,“你试试看。”
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在想什么。这是业务训练,我对自己讲道,想象自己是个搓澡巾。我带着身上的泡沫贴着阿吉,然后在浴室里像个裸体青蛙一样做上下蹲起,起立,蹲起,起立的流程。视线装作无所谓地看向浴室角落,尽量不让自己在脑中想象贴在一块的地方。滑腻的皮肉黏在一块。我也不记得那天的旅馆长什么样,不记得浴室的窗子里又是从哪个角度,如何透进来夏天中午的太阳光的了。
最后冲洗完毕后,我们回到卧室里。就这么开着灯,开着窗帘,两个人裸体坐在床上。阿吉说,一般风俗店都是用手和口服务,本番是禁止的,但是经常需要 “素股” (指用大腿根)。阿吉问我,你会用嘴吗。我想了下还是说了会,虽然唯一一次经验是在女性向风俗那边突发奇想和从业员学到的。阿吉的目光停在我身上,我想了下说,这个就不实践了吧?总之我会。
“好,那么素股你知道是怎么做吗?”
我不知为何老实地接了一句,“怎么做?”
于是阿吉让我躺下,然后人撑上来。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奇怪,这不就和真的性行为看起来一样吗。事实证明没猜错,后来才知道素股在风俗业里确实是出现 “本番强要”(强行要求女性从业员提供本番服务)的高发地带。因为觉得不对劲,我说能不能姑且用保险套,阿吉愣了下,从床边的抽屉里拿出保险套戴上。果然还真是情人旅馆啊。
等他准备了一会儿,阿吉就开始给我示范素股了。说实话,虽然我一边是真的不知道,一边是警惕地尽量低头看着,但是怎么也没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在哪,但是突然地就觉得很痛。大腿根怎么会痛呢,我也搞不明白。
阿吉看到我皱眉的样子,问我,“你是不是痛?”
我说嗯。
阿吉好像在叹气,又换了姿势,反正我还是没看清他在干什么。他试了一下,这次我还是非常非常痛,他看着我问,现在还痛吗?
我点头,说非常痛。
于是阿吉就作罢了,他说,“那就算了吧,我也不是想强迫你。”
然后我就被放去洗澡了。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是否经历了什么糟糕的事?我自己也不清楚。然后我想,我是不是没法拿到这份工作了?
我洗了一遍澡,换好衣服出来,看到阿吉在看自己的手机。我飞快瞥了一眼,是一些风俗店的招人,虽然从画面的布局看来,只是一个综合招人网站。尽管没看过这个网站,还是和我预想里中介手握的特别资料不大一样。他看到我出来了,便把手机关上。
“店铺那边……怎么样,有我能工作的店吗?”
我假装没看到他的手机画面一样说道。
“嗯,这个情况我还得再找找。我会帮你找的,今天辛苦了,你可以先回去了。”
“好的。”
“之后 line 上再联系。”
“好的。”
我平静地回答。抱着,“大概是被骗了” 的预期,安静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和阿吉道别,然后就离开了旅馆。

出旅馆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多,我看到车站附近有一家咖啡厅,便慢悠悠走了过去。在店门口踌躇了一下,心里不确定地想 “现在来咖啡厅吃好吃的合适吗”。太阳光洒在身上,才意识到暑假的中午,东京还真是好热。太热了,我便一头钻进咖啡厅,点了我最喜欢的蜜瓜苏打,一看是午饭时间,还加了份意面。
我很喜欢蜜瓜苏打。是绿色的哈密瓜汽水上面放着一个香草冰淇淋球,讲究一些的店,还会加上一个红色的糖樱桃装饰。外观看起来非常可爱,有的读者大概在动漫里看到过同款吧。
我突然特别想看到朋友们说话。当然不是说我刚刚经历的事,但是突然间特别想看人说话。我拿出手机,打开 qq 群。啊,好幸运,正巧,最近玩的游戏的好友群里,一个朋友突然比平时更早出现,提起今天晚上要不要群友一起玩游戏。
我真是太高兴在现在看到这条消息了,立刻加入了对话,在咖啡厅一边喝蜜瓜苏打,吃着香草冰淇淋和意面,一边和朋友们开心地说起晚上要玩的游戏相关的话题,说着新剧情预测,至今的展开,游戏相关的玩笑话之类的。
突然间回过神,我看着咖啡厅的窗外想到,我真是个奇怪的人呀。为什么毫无反应呢?是不是因为我天生很贱啊。其他女孩子遇到这种事,这时候应该被吓到,或者很难过很悲伤才对吧。但是我却没有难过的心情,也没有想疯狂洗澡的冲动,冲洗了一下,就出来喝蜜瓜苏打了。
但仔细想想,我好像确实没有资格以什么被害者自居。因为是我自己和对方一起走进旅馆的,是我自己意识到有风险还决定继续下去的,更何况,对方甚至最后很好心地放了我一马。虽然也可能是我之前假模假式的威胁起了点作用,但也有可能,是这就是求职的一环,单纯是我搞砸了罢了。
最重要的是,我是自己想当风俗女的。这种事的被害者里,可不会有谁是以风俗女为志愿的吧。如果这是和客人的交易,我肯定不会跑开,但是即便我这次并没有收取金钱,好像做的事情也没什么差别。
我这样想着,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常见的被害者心理。不过,我也并不想知道,为了保护这种无知,我干脆从此以后没有仔细看过这类被害后心理学有关的任何资料。
我吃完午饭后就回家了,重新洗了个澡。下午一点,拉上窗帘开始关灯睡觉。这一觉直接睡到了晚上,和网友们约好一起打游戏的时间。游戏很开心,我和大家有说有笑,暑假的日子和往常一样继续着。
游戏一直玩到了半夜,重新躺上床时,我好像已经把今天发生的事中不好的部分都忘掉了。为什么我能那么快就不难过了呢?我又问了一次自己。
在被睡意和疲惫渐渐模糊的意识里,我想起来,可能是因为这和我人生里遇到的第一起性侵害相比,实在没有那么可怕吧。相比之下,其他事好像都没有那么可怕了。这一次的甚至是可以停下来的,并且是素不相识的人。
我人生里遇到的第一次与性,与亲密关系有关的侵害,似乎来自于我的妈妈。
相比之下好像其他事都没有那么可怕了。

母亲并非不会强奸女儿,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内容已然记不得了,只是想到,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原来这件事在世界上的存在不是个例呀。
“面试” 回来后的那天晚上,我又做了噩梦,梦见了妈妈。我总是会做这个噩梦,哪怕我现在身在日本,一个人住在绝对安全的房间,每天早上将近睡醒前的时间,我都会在模糊的意识里幻听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 “咚咚” 声音,感觉 “她” 正站在我旁边。咚,咚,一如过往所有早晨一样死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咚,咚。然后我就会自噩梦中吓醒,确认现在自己的身边真的没有别人。
这样在噩梦中醒来的早晨持续了三四年,一天不落,日日如此。
在中学时,我的父母离婚,之后,妈妈的控制欲和怪异的性欲好像全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家里明明还有其他房间,但是我被要求必须每晚和她睡在一张床上。她会偷听我自慰,然后在早上我醒来之前掀开被子查看,并且以此来戏弄我。连初知世事的中学同学似乎也从我和我妈妈的关系上嗅到了奇怪的味道,有一个早熟的聪明女孩找过我,对我小声说,你妈妈是不是 “喜欢”(她说这个词时的表情带着早熟孩子特有的隐秘感)你啊。
那时的屈辱和恶心感,比以前孩子们在我身上做过的霸凌更糟糕。
后来读三岛由纪夫的小说,看到他说,谁能想到他的第一个情人竟是他幼年时因占有欲强行将他带在身边抚养的祖母,“谁能想到十三岁的我有一个六十岁的情人” 时,我感觉浑身冷的汗毛倒树了起来,又觉得绝望。
我们曾经大吵过一次,我对她说,你知不知道你对我有倒错的欲望,她愤怒起来,被我逼急了,然后又出奇地冷静,完全像是一个陌生人,对我说,“是,那你又能怎么办呢?”
是,那你又能怎么办。
在我还是孩子时,第一次对电影里的婚姻产生好奇,懵懂地说以后也想成为那个女主角。她愤怒起来,训斥了我两三个小时,告诉我:“你长成这样,以后是肯定不会有人要你的。你不可能结婚,不会有人和你结婚的。绝对不会有人爱你,除了我。”
这哪里是最后的稻草,这分明是最开始就压在我身上的山。我的血管里流动的东西,对我而言却最为恐怖。我看着墙壁,听到自己的血液在血管里流淌的声音,便感到诅咒拍打墙壁,自己或将要发疯的声音。其他的所有事才不过是稻草而已。我现在在安全的地方写着这些话,感觉没有办法呼吸,打字的手臂又冷又硬,我好像要把自己的血都写出来了。
我迫切想打破这个来自血亲的诅咒。我迫切想得到值得被别的人爱的证明,这样我或许以后就能选择自己所爱的人,被自己选择的人爱。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又在说什么了。我的人生一团混乱。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将面试那天发生的事简略记录在了自己的 sns 里,我把它当日记用。熟识的朋友看到后,来私聊我关心我的情况。我说没有关系,和妈妈对我做的事比起来算不上什么,我没有太受伤。
朋友对我说,可能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这太像是受害者安慰自己,让自己变得能忍受这些遭遇时所用的托辞了。我还是觉得你受到了伤害,我希望你好好的,别再做那么危险的事。
我停顿了一会儿,竟然不知道怎么回复,只好找了些话安慰朋友,让对方别太担心。我心里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就是不知为什么没法停下来。因为我的目的还没有达成。这真是个漫长的青春期。
再次打开 line 一看,果然阿吉从那天之后也没有再联络过我。
我放下手机,去洗澡,化妆,换上可爱的衣服,继续出门面试。
后来我短暂放弃了当风俗女的想法。不是因为别的,而是那之后,我又去参加了新宿一家 girl's bar 的面试,这一次我顺利通过。在那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正式成为了歌舞伎町的陪酒女。在一家以饮食店牌照擦边营业的酒吧里,穿着兔女郎制服,陪酒,和客人聊天,举着一小时 3000 日元的看板站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揽客。
暑假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