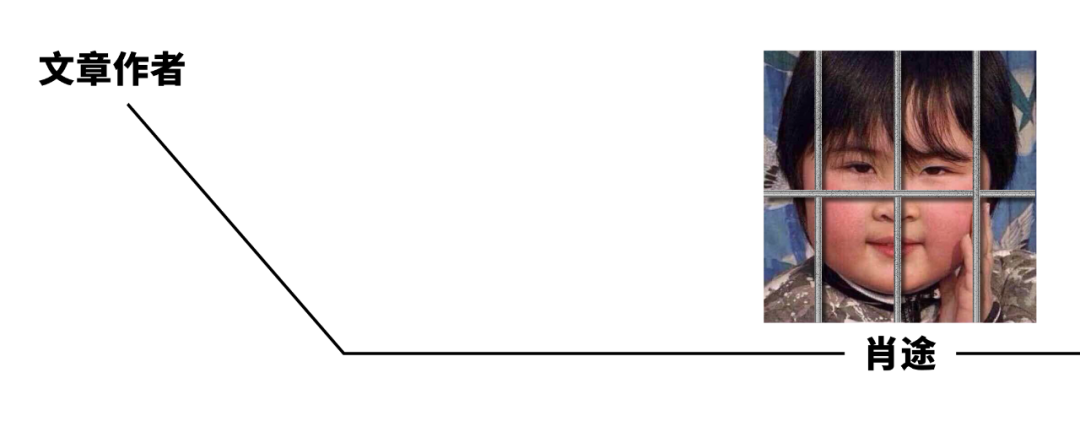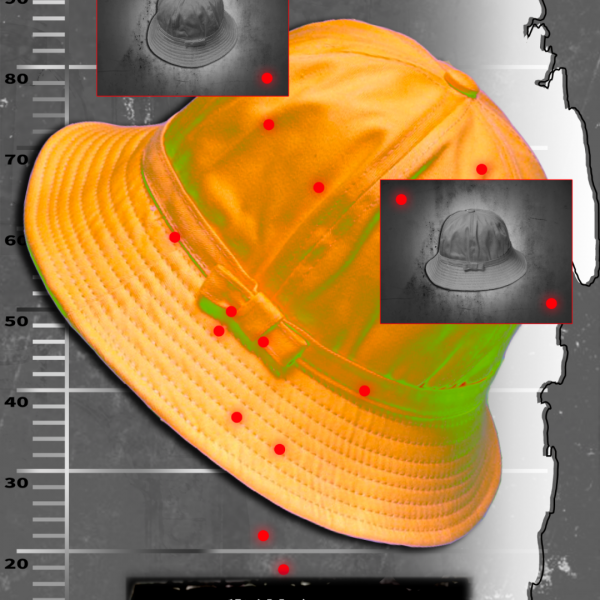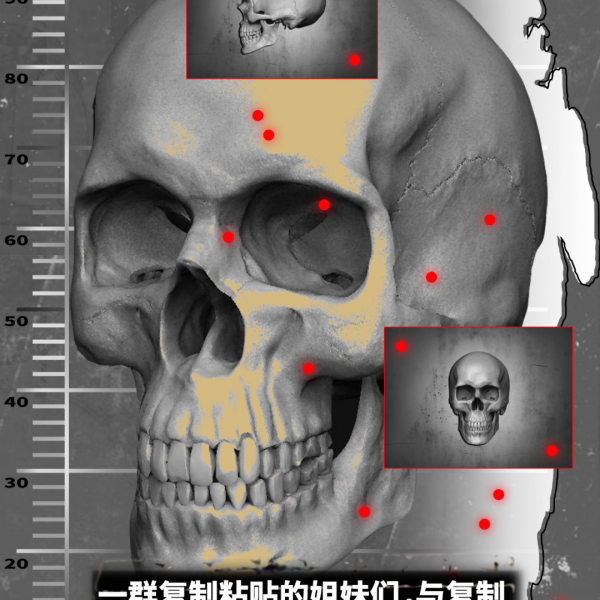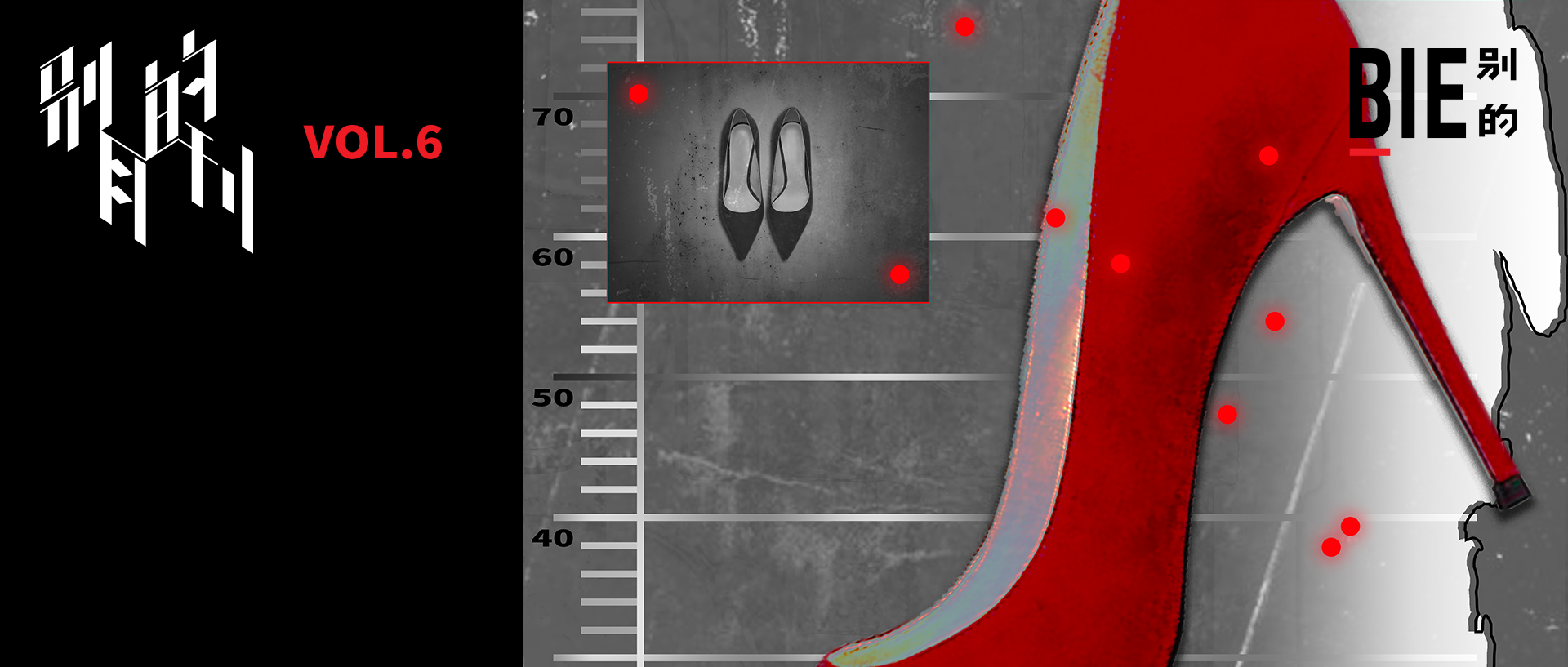
七夕夜,我走进了KTV小姐和掮客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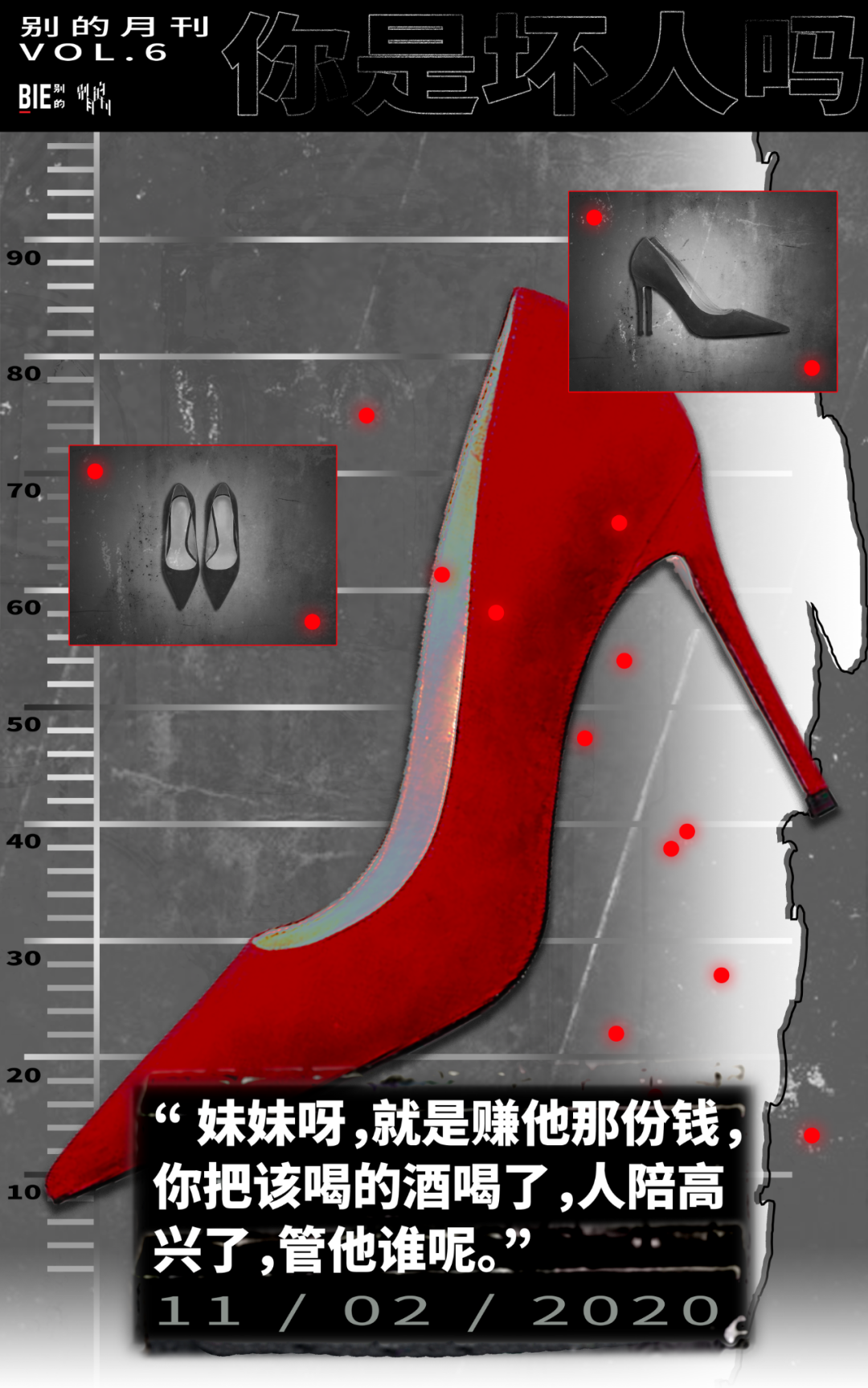
8 月的时候,我在岳阳呆了一周。白天我在太阳炙烤的街上游荡,或是在酒店里睡觉,晚上我在一家提供涩-情服务的 KTV 调研,陪坐台小姐们一起上班,也认识了一些嫖客和掮客。
1
我去 KTV 找小史的这天是七夕,和往常一样,他晚上 7 点半上班。我正在门口等着,一辆红色的老式摩托车停到我跟前,两个看上去 50 岁的男人摘掉头盔,问我:“这里是唱歌的地方吗?”
“是的,这上头写着。” 我指了指上方的闪烁着 “XX 国际 KTV” 字样的灯牌。
“你没来过吗?” 两人又问。
我开始怀疑他们真正想知道的其实是别的,比如 “这里有小姐吗?” 我只好说:“没有。” 两人仰着头打量了一番,抱着头盔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小史带我走过了两个男人刚看到的画面,门口漂亮的迎宾员朝着我们微笑,齐声 “欢迎光临”。小史告诉我,这些女人是 “公主”,在包厢里替人点歌,清理台面垃圾,但 “不陪人喝酒”,他补充道。喝酒是另一波女人的工作,也就是他负责的部分。小史是 KTV 的领班,工作包含但不限于替客人找到满意的女人喝酒,此刻他正带我穿过大堂,去小姐们的休息室。
“今天是七夕,还有客人会来吗?” 我问。
“有啊,单身的,年纪大的,等于来这找人过节了,其实节不节的也不妨碍。” 到了休息室,小史找了张沙发让我坐下就被招呼走了。
休息室其实是 KTV 左侧的一个清吧,因为疫情和正在进行的 “严查” 正好空了下来,成了小姐们集合和休息的地方。六七个卡座上都坐着人,吃饭的,化妆的,刷手机的,估摸有 50 人,但据说还是比往常少了五分之一。
一个白裙子的女人捧着个大盒子走进来,沙发上的女人迎上来笑盈盈地问:“男朋友送的?还是客人送的?” 接过盒子一翻,只有一束红色的玫瑰,她嫌弃地推到一边。“就一束花,连个口红都没有,你赶紧扔了去。” 白裙子女人靠着沙发,嘟囔了一声什么。
一个年纪稍长的女人说:“好歹还有花,今天的朋友圈晒得我气不过买了好几样东西。趁着今天人少,我得多上一个班。” 说完起身去门口排队试台。
空出来的位置很快被补上,一个身穿碎花裙的女人匆匆挂断电话趿着拖鞋在沙发上坐下,拿出一双高跟鞋换上。
“怎么来得这么迟?”
“去过节了呗。”
“刚才跟你老公打电话啊?笑眯眯的。”
听身边的女人替她问答了一轮,她才大笑说:“跟老公聊天哪能这么愉快。” 其他的女人也笑起来,跟换好鞋的女人一起朝门外走去。

小姐们的休息室
小史从包厢巡查回来,我把刚才的对话讲给他,他告诉我有些小姐会和客人成为情人,但不会跟老公离婚,就算离过婚,大多数最终还是会回到婚姻中。
“为什么不离?反正她们赚得也不少。” 我问。
“这工作又不能做一辈子。” 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而且这行的年龄天花板很低,30 岁留在 KTV 的女人已经做 “妈咪” 了。“更何况她们还有孩子。”
2
休息室门口,人们挤在一起,几个穿着制服的领班朝着屋子里喊:“还有谁没有去 209 的?都去试台。” 一个穿着制服年纪稍长的女人举着手机上的灯筒窜进沙发堆,弓着腰挨个脸瞧。她拉起一个女人:“209 试台,到门口排队去。” 女人回应:“去过了。” 这位 “妈咪” 拿起手机,端详了几秒,说:“人家要年纪小的,刚才是试台,现在要开始选了。” 接着就继续拉女人,对方大声说:“人家说我是混的,把我给退了!” 她抬了抬下巴,示意自己两侧锁骨上的纹身。
“就再去一次呗。” “妈咪” 嘴上说着,手上已经指着另外两个女人出去排队。
“这几个男孩子,就是情人节来找女朋友的。” 小史在一旁开着玩笑,但纹身女孩没有回应。
我后来找了个机会问她,为什么来这找女人的男人还会嫌弃纹身。
“有的客人觉得有纹身的女孩,经历比较多,不正经。” 她回答。小史补充道:“找年纪小的其实也是,妹子的阅历少,更纯。”
我试图去理解这个逻辑,男人在 KTV 找小姐,同时期待这个女人纯洁。纹身女人耸肩示意,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头上的时针指向八点,时候还早,小史正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于是他得空向我说起他的一段情感经历。小史曾与同在一间 KTV 的小姐恋爱,他巡房的时候总是顺带着看自己的女友,十个里有八个男人手脚都占着便宜。小史很生气,但他又觉得自己的脾气没道理,她只是做着她该做的工作。
有次他开玩笑跟女友说,要不干脆不干这个了,咱们一起做点小生意。女友也玩笑似地问他,你要养我吗?小史没敢说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不是就要和这个女人绑在一起。突然间他想到很多事,想到唯一疼爱他的奶奶,他想以后他得永远隐瞒女友的工作,他总觉得心里头堵着,这话头只好作罢。
后来,两人分手,小史的择偶标准做了调整:对方可以曾是坐台小姐,但是他们在一起之后,对方就别干了;或是他就干脆找普通女孩恋爱。
“毕竟找老婆和出来玩还是不一样的。” 他说。
我后来又向诗诗吐槽嫖客的虚伪,她回我:“妹妹呀,就是赚他那份钱,你把该喝的酒喝了,人陪高兴了,管他谁呢。”
也对,我觉得自己对于道德的严苛在夜场的语境中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在与我交谈的十几个陪酒小姐中,赚钱是无一例外的理由。
诗诗接着说,男人无论是老公还是嫖客都是一个 “德行”,而女人只有拥有钱才能摆脱这些失望。
诗诗 88 年出生,21 岁结婚,跟丈夫一家在广东生活,婚后不久有了一个儿子,平时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务。对她和婆婆的种种不合,她的老公只是在两人之间插科打诨,对于显眼的矛盾视而不见。
有天,诗诗同婆婆吵架,一气之下跑在河边坐了一下午。她说服自己撑下去,毕竟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等她回到家,丈夫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他们吃饭也不叫我,电话也不打,我跑出去,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没人找我。” 她说起的时候像是在说什么好笑的事。
一想到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几十年,她再也无法忍受,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三年前她离了婚,便从老家来到岳阳干上 KTV 陪酒小姐的工作,原因很简单,“能赚钱”。
小史回忆他刚见到诗诗,对方就是一副 “家庭妇女” 的模样,后来诗诗去整容,学化妆,收拾得漂漂亮亮,像是要重新活一回的架势。所以我看到诗诗的时候,她已然是 “头牌” 的作派。
诗诗所追求的女人独立资本,她已经攒到了一笔,但她不肯告诉我数字。她只说:“再干两年,反正做满 5 年就不干了。” 2022 年她 34 岁,她决定 35 岁就再婚,攒的钱都留给儿子。她说:“我没有时间陪着他,他从小没有一个好的家庭,但他物质上都得有。别人父母买房给儿子,我也能给他买。”
3
并非每个在 KTV 工作的小姐都能攒到钱。小史说,小姐们一个台的小费是 500-700 元不等,10% 的佣金给领班。运气好的时候,有人一晚上能转两个台。可轻易得到的钱也会被快速花掉:
有人置办昂贵的护肤品抵御熬夜造成的衰老,也有人把从男人那赚来的钱再花在自己的情人身上,不然就是撒在牌桌上。
小史还有别的法子替她们找钱,他放高利贷给她们,或给她们介绍出去过夜的客人。但是,赚钱 —— 赌博 —— 借高利贷 —— 跟客人出台,这种典型的戏剧桥段在夜场其实缺乏普遍性,赌博倾家荡产与女人们出卖身体的关联并不紧密。对于 KTV 的坐台小姐来说,出台,与客人上床,这需要斟酌的底线是因人而异的。小史说,很多女人不出台,她们日后仍需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可客人出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价格,她们还是会犹豫。“是个人都会想想吧!只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个价格有高有低。”

在一条曾经是红灯区的街上,按摩店正在转让
小史说起他带过的一个小姐,三十多岁的女人,东莞扫黄之后回来的,“真放得开,人家让她脱衣服她就脱”。通常,小姐们遇上客人这样的要求都会想着法子绕过去,大多数客人也不会真的指望花几百块钱就能让坐台小姐宽衣解带。
“她本来就是在东莞做按摩的,莞式服务,你知道吗?” 小史不好意思说,他只能对我解释,就是出台后干的事。
东莞女人作风豪放总有班上,但她还是要求小史给她介绍客人出台。其他人问东莞女人,赚了这么多钱都去哪潇洒了。东莞女人回答,她给丈夫父母拿去养孩子了。她老家的家人,包括 30 多岁的弟弟,都指望她在夜场赚的钱生活。
东莞女人没在岳阳呆多久就去了浙江,理由是那边坐台的价格高。
4
快到午夜了,几个女人坐在包厢里,她们还没有得到今晚的第一份工作,但知道自己多半等不到了。
在商务应酬的流程中,每个环节的安排都有其固定且 “合理” 的理由,也就是一套情绪的递进。6 点到 8 点,男人们会一起吃饭少量喝酒,8 点到 12 点,他们会来 KTV 叫上几个女人陪着喝酒,12 点以后,如果客户还有 “性致”,他们会安排按摩会所,或者直接去酒店开房。
“都这个点了,哪还有人来。” 婉婉又点上了一根烟,她打开手机上的外卖软件,没一会,她把手机递给身边的女人,“要不要吃点?” 女人接过手机很快又递了回去,“算了,我再等会,12 点还没人来,我再走。”
还有一个新来的年轻女孩,她刚换了身衣服,白色的露肩一字短裙显得身材很好。“你穿这个好上班。” 有人跟她说,她却自嘲:“我就准备在这干一周,结果第一天就没上着班。”
“你要去哪?” 婉婉说。
“跟我男朋友去广东。” 年轻女孩小声说。
“你男朋友?去广东能干什么?”
“我男朋友也是在 KTV 带妹子的,去广东赚得多。”
“你多大?”
“我 01 年的。”
没有人接话,婉婉继续点她的外卖,女人们在沉默中拿出自己的手机机械地滑动。一个看上去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走进包厢,重重地把自己扔到沙发上,生气地说:“哪有什么晚晚场的客人,人家早就都挑好了。”
这下谁也别等了。年长的女人叹了一口气,“本来我娃说今天来找我,我想着上班赚点钱就没让他来,结果班也没上着,孩子也没陪。”
又坐了一会,女人们出去透气,包厢里只剩我和婉婉还在等外卖。
“我说这女孩就是傻,去广东被卖了都不知道。” 婉婉嚼着槟榔,不屑地说。我不知该如何作答,叹了口气。

接近午夜的休息室,女人们大多去工作了
新来的年轻女孩回到包厢,婉婉冲着她大喊:“我听说跟你一起玩的都是些混黑社会的大哥大姐,你是不是也是混的姐姐!” 女孩面露难色,只是摆摆手。婉婉冲着我大笑,又重复了一遍:“诶我跟你说,这个新来的姐姐是混黑社会的。我好怕啊!” 当时我无法理解白婉婉言语中突如其来的恶意。
没人的时候婉婉跟我说,她也在广东呆过。她高中辍学,跑去浙江找妈妈学做美容,一天低着头坐十几个小时,累得脖子抬不起来,过年回老家时,一个同学叫她去广东打工,说那里工作机会多,工资也高。到了地方,是一间 KTV,同学递给她一套衣服,让她陪男人喝酒,婉婉说:“我不干这个,我不会喝。”
她还没成年,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她无处可逃,行李和证件都扣在 KTV 的老板手里。同学天天劝她:“咱们没读过多少书,能找到什么好工作,你陪人喝点酒就可以赚得比人家大学生多,你为什么不干。”
有天,她坐在包厢里,一个老男人拎着她领口的拉链径直往下扯,婉婉捂住衣服哭着冲出包厢。
她说:“那个新来的女人,她还笑得出来,她还挺期待的样子。”
我坐在婉婉的对面,默默地端详着她。头顶的灯球无声地旋转,光照着婉婉的脸,她其实也才 20 岁。
我意识到,婉婉对女孩没由来的怒气来自她们相似的命运,她想要骂醒对方,就像她期望当年有人阻拦了自己。
现实中,婉婉在黑心老板手下干了一年,只有春节的时候被放回家,但人走钱得留下,防止跑路。婉婉一咬牙,没回去。
“上大学好玩吗?” 婉婉问我。我回答,就是学习和参加社团,挺忙的。她听着觉得无聊,接着问:“那你挺爱学习的吧?” “还行,你不喜欢上学吗?” 婉婉笑了出声,说:“要是爱上学,我还出来干这个。”
她逃离了 KTV,最后还是回来了,她没有解释究竟是哪一个念头让她把屈辱感都忘掉,也许还是钱 —— 她大概是相信了那些话,“你又没读过什么书,离开了这里,上哪找好赚钱的事”。
婉婉告诉我,等她做到 25 岁钱攒够就不干了,“回去享我的福。” 这个年龄在婉婉看来,是该嫁人了,何况夜场的女人,二十大几就到头了。
5
快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和没班上的女人一起离开了 KTV,小史一个小时之前就邀上几个下班的小姐们去吃宵夜,他问我:“有收获吗?” 我也不清楚。小史开玩笑:“像你这样采访是不行的,你得跟着她们,站在那让人选,那才真实。”
其实我也试了,原因不仅是为了采访。
我时常处在缺钱的困顿中,每当我叫嚣着找人 “包养” 的时候,我都无比想试验自己的真心。在我看来,我只需要忍受男人有意无意地揩油,再多喝几杯酒,说几句甜言蜜语,我就可以拿到钱,这听起来并不难。于是,几小时前,小姐们换场到二楼包厢等晚场客人的时候,我跟着她们一起上楼。

KTV 的内饰
路过某间包厢时,一个男人出来打电话,他上下打量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块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肉,不消片刻,我那虚张声势的勇气就消失大半。
我逃回休息室,和剩下的小姐坐在沙发上,“妈咪” 进来叫人去试台,人都走光了,只剩我,她盯着我厉声说:“你怎么不去上班?” 我吓一跳,赶紧回答:“我不是来上班的。”
某种脆弱威胁着我稳固而相对体面的日常,我知道稍有不慎,我也会跌入一个由金钱编织的陷阱中,但此刻我明白我还属于有选择的那些人。
要是某天大难临头,我是不是也会和这些陷入困境的女人一样,做出相同的选择?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那天真的来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不止息地奋力逃离该死的命运。
(文中所用皆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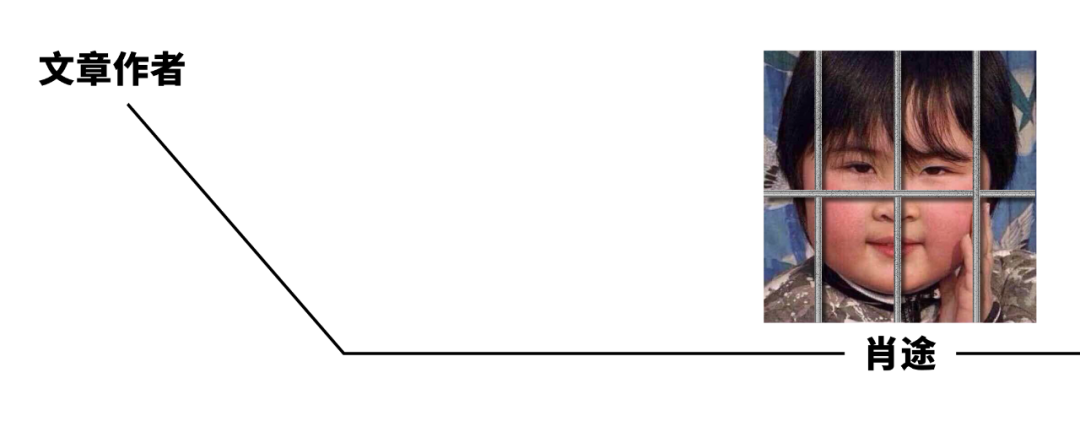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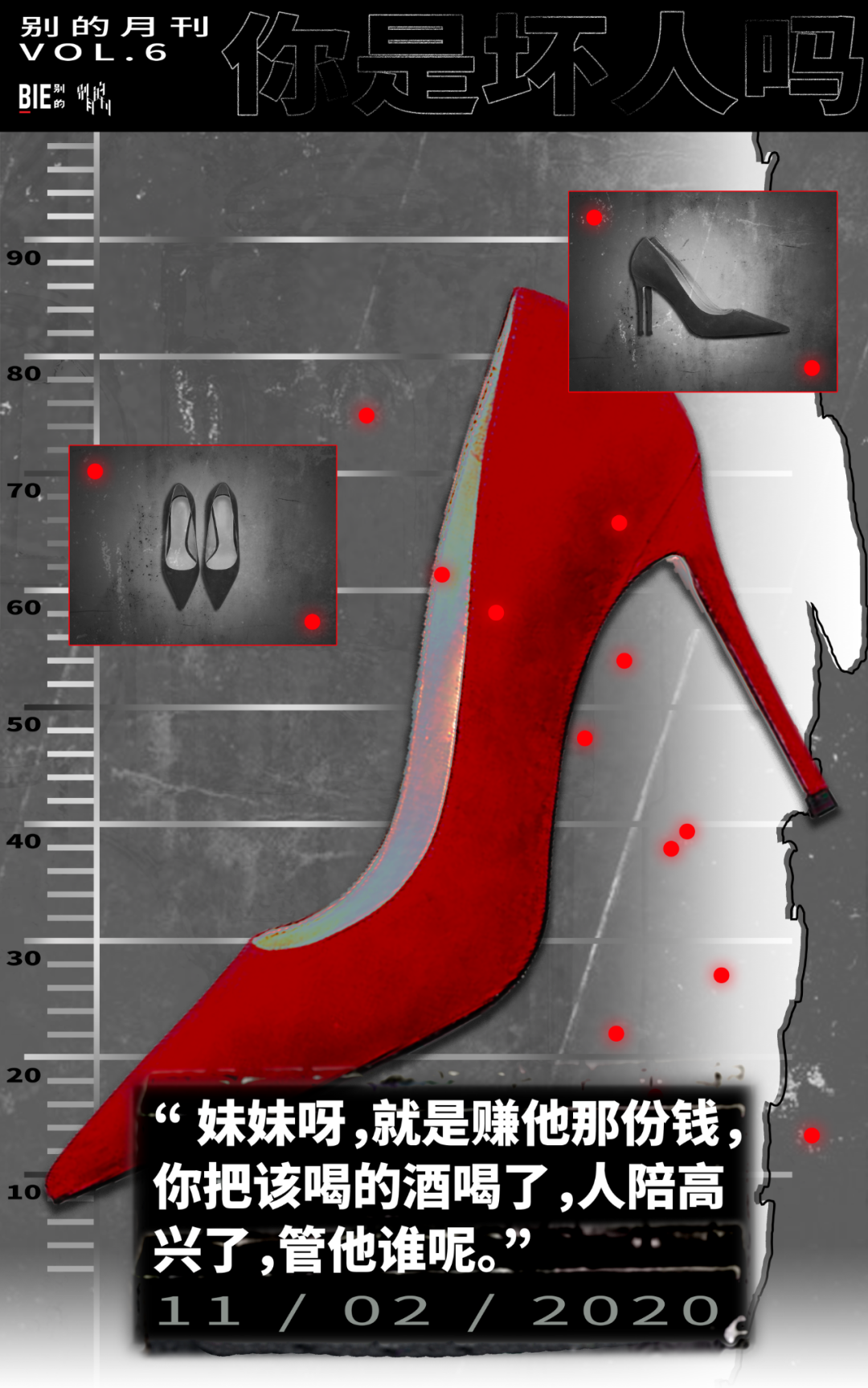
8 月的时候,我在岳阳呆了一周。白天我在太阳炙烤的街上游荡,或是在酒店里睡觉,晚上我在一家提供涩-情服务的 KTV 调研,陪坐台小姐们一起上班,也认识了一些嫖客和掮客。
1
我去 KTV 找小史的这天是七夕,和往常一样,他晚上 7 点半上班。我正在门口等着,一辆红色的老式摩托车停到我跟前,两个看上去 50 岁的男人摘掉头盔,问我:“这里是唱歌的地方吗?”
“是的,这上头写着。” 我指了指上方的闪烁着 “XX 国际 KTV” 字样的灯牌。
“你没来过吗?” 两人又问。
我开始怀疑他们真正想知道的其实是别的,比如 “这里有小姐吗?” 我只好说:“没有。” 两人仰着头打量了一番,抱着头盔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小史带我走过了两个男人刚看到的画面,门口漂亮的迎宾员朝着我们微笑,齐声 “欢迎光临”。小史告诉我,这些女人是 “公主”,在包厢里替人点歌,清理台面垃圾,但 “不陪人喝酒”,他补充道。喝酒是另一波女人的工作,也就是他负责的部分。小史是 KTV 的领班,工作包含但不限于替客人找到满意的女人喝酒,此刻他正带我穿过大堂,去小姐们的休息室。
“今天是七夕,还有客人会来吗?” 我问。
“有啊,单身的,年纪大的,等于来这找人过节了,其实节不节的也不妨碍。” 到了休息室,小史找了张沙发让我坐下就被招呼走了。
休息室其实是 KTV 左侧的一个清吧,因为疫情和正在进行的 “严查” 正好空了下来,成了小姐们集合和休息的地方。六七个卡座上都坐着人,吃饭的,化妆的,刷手机的,估摸有 50 人,但据说还是比往常少了五分之一。
一个白裙子的女人捧着个大盒子走进来,沙发上的女人迎上来笑盈盈地问:“男朋友送的?还是客人送的?” 接过盒子一翻,只有一束红色的玫瑰,她嫌弃地推到一边。“就一束花,连个口红都没有,你赶紧扔了去。” 白裙子女人靠着沙发,嘟囔了一声什么。
一个年纪稍长的女人说:“好歹还有花,今天的朋友圈晒得我气不过买了好几样东西。趁着今天人少,我得多上一个班。” 说完起身去门口排队试台。
空出来的位置很快被补上,一个身穿碎花裙的女人匆匆挂断电话趿着拖鞋在沙发上坐下,拿出一双高跟鞋换上。
“怎么来得这么迟?”
“去过节了呗。”
“刚才跟你老公打电话啊?笑眯眯的。”
听身边的女人替她问答了一轮,她才大笑说:“跟老公聊天哪能这么愉快。” 其他的女人也笑起来,跟换好鞋的女人一起朝门外走去。

小姐们的休息室
小史从包厢巡查回来,我把刚才的对话讲给他,他告诉我有些小姐会和客人成为情人,但不会跟老公离婚,就算离过婚,大多数最终还是会回到婚姻中。
“为什么不离?反正她们赚得也不少。” 我问。
“这工作又不能做一辈子。” 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而且这行的年龄天花板很低,30 岁留在 KTV 的女人已经做 “妈咪” 了。“更何况她们还有孩子。”
2
休息室门口,人们挤在一起,几个穿着制服的领班朝着屋子里喊:“还有谁没有去 209 的?都去试台。” 一个穿着制服年纪稍长的女人举着手机上的灯筒窜进沙发堆,弓着腰挨个脸瞧。她拉起一个女人:“209 试台,到门口排队去。” 女人回应:“去过了。” 这位 “妈咪” 拿起手机,端详了几秒,说:“人家要年纪小的,刚才是试台,现在要开始选了。” 接着就继续拉女人,对方大声说:“人家说我是混的,把我给退了!” 她抬了抬下巴,示意自己两侧锁骨上的纹身。
“就再去一次呗。” “妈咪” 嘴上说着,手上已经指着另外两个女人出去排队。
“这几个男孩子,就是情人节来找女朋友的。” 小史在一旁开着玩笑,但纹身女孩没有回应。
我后来找了个机会问她,为什么来这找女人的男人还会嫌弃纹身。
“有的客人觉得有纹身的女孩,经历比较多,不正经。” 她回答。小史补充道:“找年纪小的其实也是,妹子的阅历少,更纯。”
我试图去理解这个逻辑,男人在 KTV 找小姐,同时期待这个女人纯洁。纹身女人耸肩示意,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头上的时针指向八点,时候还早,小史正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于是他得空向我说起他的一段情感经历。小史曾与同在一间 KTV 的小姐恋爱,他巡房的时候总是顺带着看自己的女友,十个里有八个男人手脚都占着便宜。小史很生气,但他又觉得自己的脾气没道理,她只是做着她该做的工作。
有次他开玩笑跟女友说,要不干脆不干这个了,咱们一起做点小生意。女友也玩笑似地问他,你要养我吗?小史没敢说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不是就要和这个女人绑在一起。突然间他想到很多事,想到唯一疼爱他的奶奶,他想以后他得永远隐瞒女友的工作,他总觉得心里头堵着,这话头只好作罢。
后来,两人分手,小史的择偶标准做了调整:对方可以曾是坐台小姐,但是他们在一起之后,对方就别干了;或是他就干脆找普通女孩恋爱。
“毕竟找老婆和出来玩还是不一样的。” 他说。
我后来又向诗诗吐槽嫖客的虚伪,她回我:“妹妹呀,就是赚他那份钱,你把该喝的酒喝了,人陪高兴了,管他谁呢。”
也对,我觉得自己对于道德的严苛在夜场的语境中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在与我交谈的十几个陪酒小姐中,赚钱是无一例外的理由。
诗诗接着说,男人无论是老公还是嫖客都是一个 “德行”,而女人只有拥有钱才能摆脱这些失望。
诗诗 88 年出生,21 岁结婚,跟丈夫一家在广东生活,婚后不久有了一个儿子,平时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务。对她和婆婆的种种不合,她的老公只是在两人之间插科打诨,对于显眼的矛盾视而不见。
有天,诗诗同婆婆吵架,一气之下跑在河边坐了一下午。她说服自己撑下去,毕竟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等她回到家,丈夫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他们吃饭也不叫我,电话也不打,我跑出去,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没人找我。” 她说起的时候像是在说什么好笑的事。
一想到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几十年,她再也无法忍受,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三年前她离了婚,便从老家来到岳阳干上 KTV 陪酒小姐的工作,原因很简单,“能赚钱”。
小史回忆他刚见到诗诗,对方就是一副 “家庭妇女” 的模样,后来诗诗去整容,学化妆,收拾得漂漂亮亮,像是要重新活一回的架势。所以我看到诗诗的时候,她已然是 “头牌” 的作派。
诗诗所追求的女人独立资本,她已经攒到了一笔,但她不肯告诉我数字。她只说:“再干两年,反正做满 5 年就不干了。” 2022 年她 34 岁,她决定 35 岁就再婚,攒的钱都留给儿子。她说:“我没有时间陪着他,他从小没有一个好的家庭,但他物质上都得有。别人父母买房给儿子,我也能给他买。”
3
并非每个在 KTV 工作的小姐都能攒到钱。小史说,小姐们一个台的小费是 500-700 元不等,10% 的佣金给领班。运气好的时候,有人一晚上能转两个台。可轻易得到的钱也会被快速花掉:
有人置办昂贵的护肤品抵御熬夜造成的衰老,也有人把从男人那赚来的钱再花在自己的情人身上,不然就是撒在牌桌上。
小史还有别的法子替她们找钱,他放高利贷给她们,或给她们介绍出去过夜的客人。但是,赚钱 —— 赌博 —— 借高利贷 —— 跟客人出台,这种典型的戏剧桥段在夜场其实缺乏普遍性,赌博倾家荡产与女人们出卖身体的关联并不紧密。对于 KTV 的坐台小姐来说,出台,与客人上床,这需要斟酌的底线是因人而异的。小史说,很多女人不出台,她们日后仍需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可客人出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价格,她们还是会犹豫。“是个人都会想想吧!只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个价格有高有低。”

在一条曾经是红灯区的街上,按摩店正在转让
小史说起他带过的一个小姐,三十多岁的女人,东莞扫黄之后回来的,“真放得开,人家让她脱衣服她就脱”。通常,小姐们遇上客人这样的要求都会想着法子绕过去,大多数客人也不会真的指望花几百块钱就能让坐台小姐宽衣解带。
“她本来就是在东莞做按摩的,莞式服务,你知道吗?” 小史不好意思说,他只能对我解释,就是出台后干的事。
东莞女人作风豪放总有班上,但她还是要求小史给她介绍客人出台。其他人问东莞女人,赚了这么多钱都去哪潇洒了。东莞女人回答,她给丈夫父母拿去养孩子了。她老家的家人,包括 30 多岁的弟弟,都指望她在夜场赚的钱生活。
东莞女人没在岳阳呆多久就去了浙江,理由是那边坐台的价格高。
4
快到午夜了,几个女人坐在包厢里,她们还没有得到今晚的第一份工作,但知道自己多半等不到了。
在商务应酬的流程中,每个环节的安排都有其固定且 “合理” 的理由,也就是一套情绪的递进。6 点到 8 点,男人们会一起吃饭少量喝酒,8 点到 12 点,他们会来 KTV 叫上几个女人陪着喝酒,12 点以后,如果客户还有 “性致”,他们会安排按摩会所,或者直接去酒店开房。
“都这个点了,哪还有人来。” 婉婉又点上了一根烟,她打开手机上的外卖软件,没一会,她把手机递给身边的女人,“要不要吃点?” 女人接过手机很快又递了回去,“算了,我再等会,12 点还没人来,我再走。”
还有一个新来的年轻女孩,她刚换了身衣服,白色的露肩一字短裙显得身材很好。“你穿这个好上班。” 有人跟她说,她却自嘲:“我就准备在这干一周,结果第一天就没上着班。”
“你要去哪?” 婉婉说。
“跟我男朋友去广东。” 年轻女孩小声说。
“你男朋友?去广东能干什么?”
“我男朋友也是在 KTV 带妹子的,去广东赚得多。”
“你多大?”
“我 01 年的。”
没有人接话,婉婉继续点她的外卖,女人们在沉默中拿出自己的手机机械地滑动。一个看上去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走进包厢,重重地把自己扔到沙发上,生气地说:“哪有什么晚晚场的客人,人家早就都挑好了。”
这下谁也别等了。年长的女人叹了一口气,“本来我娃说今天来找我,我想着上班赚点钱就没让他来,结果班也没上着,孩子也没陪。”
又坐了一会,女人们出去透气,包厢里只剩我和婉婉还在等外卖。
“我说这女孩就是傻,去广东被卖了都不知道。” 婉婉嚼着槟榔,不屑地说。我不知该如何作答,叹了口气。

接近午夜的休息室,女人们大多去工作了
新来的年轻女孩回到包厢,婉婉冲着她大喊:“我听说跟你一起玩的都是些混黑社会的大哥大姐,你是不是也是混的姐姐!” 女孩面露难色,只是摆摆手。婉婉冲着我大笑,又重复了一遍:“诶我跟你说,这个新来的姐姐是混黑社会的。我好怕啊!” 当时我无法理解白婉婉言语中突如其来的恶意。
没人的时候婉婉跟我说,她也在广东呆过。她高中辍学,跑去浙江找妈妈学做美容,一天低着头坐十几个小时,累得脖子抬不起来,过年回老家时,一个同学叫她去广东打工,说那里工作机会多,工资也高。到了地方,是一间 KTV,同学递给她一套衣服,让她陪男人喝酒,婉婉说:“我不干这个,我不会喝。”
她还没成年,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她无处可逃,行李和证件都扣在 KTV 的老板手里。同学天天劝她:“咱们没读过多少书,能找到什么好工作,你陪人喝点酒就可以赚得比人家大学生多,你为什么不干。”
有天,她坐在包厢里,一个老男人拎着她领口的拉链径直往下扯,婉婉捂住衣服哭着冲出包厢。
她说:“那个新来的女人,她还笑得出来,她还挺期待的样子。”
我坐在婉婉的对面,默默地端详着她。头顶的灯球无声地旋转,光照着婉婉的脸,她其实也才 20 岁。
我意识到,婉婉对女孩没由来的怒气来自她们相似的命运,她想要骂醒对方,就像她期望当年有人阻拦了自己。
现实中,婉婉在黑心老板手下干了一年,只有春节的时候被放回家,但人走钱得留下,防止跑路。婉婉一咬牙,没回去。
“上大学好玩吗?” 婉婉问我。我回答,就是学习和参加社团,挺忙的。她听着觉得无聊,接着问:“那你挺爱学习的吧?” “还行,你不喜欢上学吗?” 婉婉笑了出声,说:“要是爱上学,我还出来干这个。”
她逃离了 KTV,最后还是回来了,她没有解释究竟是哪一个念头让她把屈辱感都忘掉,也许还是钱 —— 她大概是相信了那些话,“你又没读过什么书,离开了这里,上哪找好赚钱的事”。
婉婉告诉我,等她做到 25 岁钱攒够就不干了,“回去享我的福。” 这个年龄在婉婉看来,是该嫁人了,何况夜场的女人,二十大几就到头了。
5
快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和没班上的女人一起离开了 KTV,小史一个小时之前就邀上几个下班的小姐们去吃宵夜,他问我:“有收获吗?” 我也不清楚。小史开玩笑:“像你这样采访是不行的,你得跟着她们,站在那让人选,那才真实。”
其实我也试了,原因不仅是为了采访。
我时常处在缺钱的困顿中,每当我叫嚣着找人 “包养” 的时候,我都无比想试验自己的真心。在我看来,我只需要忍受男人有意无意地揩油,再多喝几杯酒,说几句甜言蜜语,我就可以拿到钱,这听起来并不难。于是,几小时前,小姐们换场到二楼包厢等晚场客人的时候,我跟着她们一起上楼。

KTV 的内饰
路过某间包厢时,一个男人出来打电话,他上下打量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块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肉,不消片刻,我那虚张声势的勇气就消失大半。
我逃回休息室,和剩下的小姐坐在沙发上,“妈咪” 进来叫人去试台,人都走光了,只剩我,她盯着我厉声说:“你怎么不去上班?” 我吓一跳,赶紧回答:“我不是来上班的。”
某种脆弱威胁着我稳固而相对体面的日常,我知道稍有不慎,我也会跌入一个由金钱编织的陷阱中,但此刻我明白我还属于有选择的那些人。
要是某天大难临头,我是不是也会和这些陷入困境的女人一样,做出相同的选择?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那天真的来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不止息地奋力逃离该死的命运。
(文中所用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