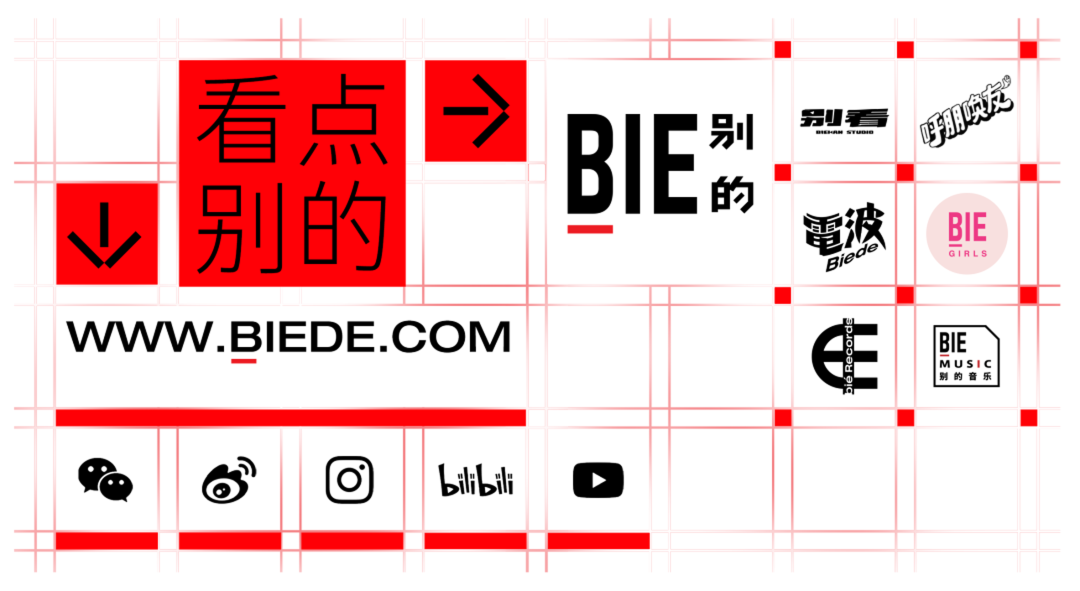当被教导“要听话”和“会来事儿”的女孩拿起笔


“水像一种爱”,这个句子叩访于一个瞬间。张天翼接住它,继续向下写,“那一刻的感觉真好,比猛灌一大口冰啤酒还好,比亲吻时舌头伸进一个可爱的嘴里还好。水给了浮力,也给了阻力——更像爱了。”
这是短篇小说《泳客》里的一段话,收录于青年作家张天翼的最新作品集《如雪如山》。雪,山,标题里又是两个比喻。张天翼爱用比喻,爱到一些读者连呼过量的地步。她介绍自己是“写小说的手艺人”,手艺人总要有点自己的小乐趣。比喻句就是给自己的小奖励,“每写出一个这样的句子来,就会带来一道非常确定的快乐。”
她还向我分享一段趣闻:“王尔德非常爱用具体宝石和花朵来作比,比如珊瑚、象牙、猫眼石、金子,还有紫罗兰,水仙,玫瑰......他的喻体加在一起,就像一个堆满了钻石孔雀毛这种美丽物品的屋子。这一部分和他的性格和审美有关,一部分也有当时英国皇家海军殖民全球,把大量奇珍异宝搜刮到本国,掀起贵族赏玩风潮的历史缘由。
“后来,毛姆在他的《作家笔记》里提起这一茬,说他读过王尔德的《莎乐美》之后,也想学会这种笔法。于是就去了大英博物馆,记下好多宝石的名字来做造句练习,有什么青金石、石榴石、珐琅、水苍玉……两个人可以说是隔空相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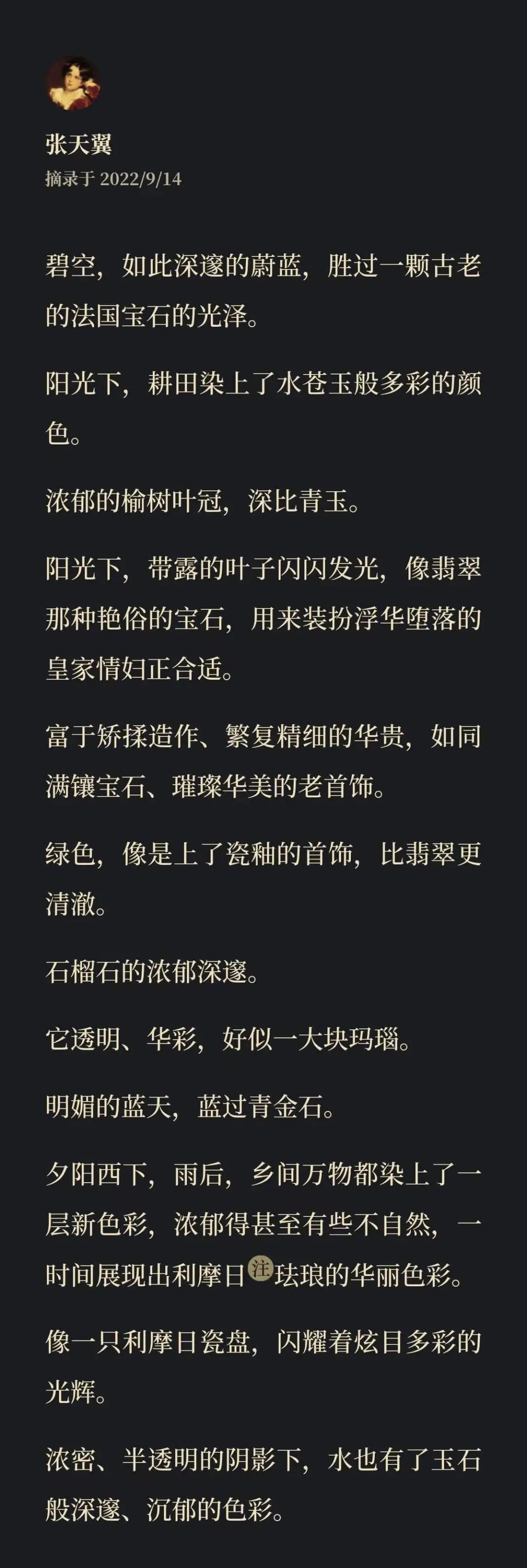
张天翼的读书笔记
她说:“看一个作者写比喻句所用的喻体,大致可知其审美趣味,阅读广度,童年经历甚至上限下限。把所有喻体集合起来,是一部微缩个人史的关键词。喻体暴露一切。”

“白瓷砖地上,洗手池和抽水马桶中间的阴影里,有个红点。是一滴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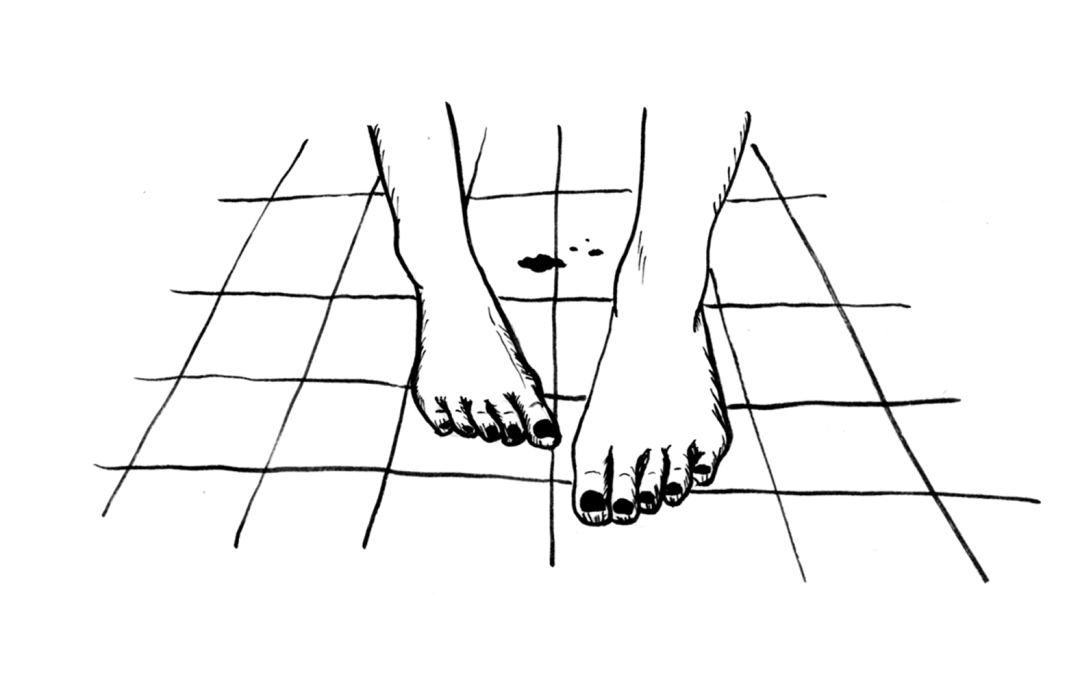
这滴生理期的血真实存在过,只不过距离现在好几个年头。经血原本应该在的地方是马桶里、卫生纸上、垃圾篓的卫生巾里。当它出现在白色瓷砖上时,你会觉得画面有一点刺眼。
那时张天翼还在念书,假期返校前,不慎在家里的地砖上留下一滴血。看到那滴血时,她脑子里出现一个怪念头,有些舍不得擦掉这个从自己身体里跑出来的东西。“老想着就算人走了,至少会有这么一点点的自己留在家里,和妈妈待在一起,那也是很好的。”
现实里的张天翼和母亲拥有过超出平常母女的亲密,故事里的主角粒粒和母亲也是。只不过,现实里她最终还是擦掉了血,而故事中的那一滴被留下来了,留在再婚后的母亲与继父的新家里。父亲在母女关系里总是名闯入者,和许多女儿一样,张天翼对自己的父亲并不满意,背地里偶尔跟母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离婚”。她是天津人,记忆里大家分外注重“在外不跌份儿”,夫妻离婚的少之又少。无论日常如何扭曲与倾轧,婚姻这床锦被一盖过,血腥味顿时就被锁在了家门里。
现实里未能如愿的事情,她搬到文字里,只不过也与圆满相去甚远。在短篇《地上的血》里,母亲王嫦娥在女儿粒粒上大学后离婚,经人介绍与一位中学老师再婚。故事是从粒粒放假回来,第一次踏入那个全然陌生的生活空间开始的。每个人在白天或多或少完成对“和美”的扮演,到了半夜,一切被粒粒突如其来的生理期打破平衡。面对染污的床单和不被预料的出血,在“一种阴沉的平静”里,王嫦娥说,自己半年前就停经了。
经期和经血,那本来是只属于母女两个人的秘密。一个三口之家里,背负劳累委屈的母亲通过这“红色印章”与女儿构建起排他的亲密,彼此拥有,不再孤立无援。然而一个重组家庭并不是如此。在女儿的注视下,中年女性被分裂成一个娴熟的“母亲”和一个生疏的“女人”, 女儿与爸爸抢妈妈,总是赢的毫无悬念;而女儿与妈妈本人抢“妈妈”时,走向却是两败俱伤。
母亲与女儿无法免于离散,就像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关系那样,这是张天翼隐隐想说的。这次与停经有关的冲击同样源自现实,某一次生理期,她像往常那样去家里老地方翻找母亲的卫生巾,“妈妈总会准备好一切,妈妈就是兜底”,这次却只翻出了最轻薄短小的护垫。面对她的询问,母亲回答说,自己已经快要绝经了,那点出血量用护垫已经绰绰有余。这对当时的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她好像看到两人曾经肌肤相贴的亲密正在随潮消退,而“她当初就乘着这样的红色潮水,从肉体的罅隙中滑进世界,从母亲的盼望中跨入现实。某种程度上,我们活在与亲爱的人共享的部分里”。在渐行渐远中被剥除的不只是关系,也是一部分的自己。而这个故事里,“如果说必须有反派,那也只能是时间了。”
几个月前,张天翼决定回一趟老家。她告诉妈妈自己订了后天周末的票。回家的前一天,妈妈一反常态,给她发来一张自拍,说,我想让你看看,我现在是长这样。母亲担心自己老得太多太快,离家太久的女儿回去乍一看到会接受不了。然而,“她的害怕令我害怕,她的担心让我更难受”,“人的泥潭通常就是自己”。两人之间套娃式的小心翼翼最后只能归于一句,“以前不是这样的”
《地上的血》写好后,她照着自己的脚,画了一幅简笔画做章节页小图。书印好后寄了一本给妈妈,隔天妈妈给她发来微信,“我还没看内容,翻了一翻,那插图上的脚是你的吧?有一根脚趾弯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如雪如山》共有七个故事,故事的主角都叫“lili”,有春运火车上的女学生詹立立,有怀抱婴儿、正为产后抑郁所苦的新手母亲俪俪,也有在一周年纪念日上与情人分手的已婚女插画师陶梨栗。据张天翼说,她们的名字是由英文名 Lily 而来,她喜欢词里爽脆的发音,词外百合花的涵义,不知不觉,一个荔荔变成了许多个 lili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边找到一个张丽或者王丽,每个人也或明或暗在这些 lili 身上瞥见自己,“所有女人身上都暗藏一块相同的拼图,她们的悲喜、隐秘的痛苦与爱憎,如此迥异,又彼此相通。”系在她们手腕间那些柔柔的结,有时是母亲与女儿,有时是女人与女孩,有时则是同窗、同事、萍水相逢的同路人……

lili 们也都是某一部分的张天翼,她们的共同特征是乖巧。“女孩子要有眼力见儿”,这是她从小被教导、逐渐深恶痛绝的一句话。在北方,这句话还有一个姊妹篇,叫做“女孩儿要会来事儿”。它们包含某些被整合到一起的规范,从家里的亲戚们口中,砸到每个小姑娘的头上。作为小孩,她花了许多工夫去揣摩,到底什么叫会来事儿,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会来事儿的人。善解人意的同时要学会察言观色,表露聪慧时一定要恰到好处。她的求生欲来自幼时阴晴不定的家庭气氛,“我爸爸脾气不太好,我在家里经常需要小心翼翼地去观察他的脸色,来决定今天是要喘气粗一点,还是不要那么粗;是在家里溜边走,还是走中间车道。”
在《我只想坐下》一篇中,火车上遭遇性骚扰的立立选择噤声,“他喜欢我所以才摸我”、“……换吧,值得”、“……就当免费按摩!要是什么都不想,还觉得有点舒服呢,说不定还能睡一会儿”,她跟自己这么说着。与此同时,那些横陈在车厢中散发臭气的人体、一人跨过千万里去开水房接回四五个人的热水、被不管不顾的中年男人抢走的座位,桩桩件件向她压来,“女孩子在乖巧懂事的造诣上无尽无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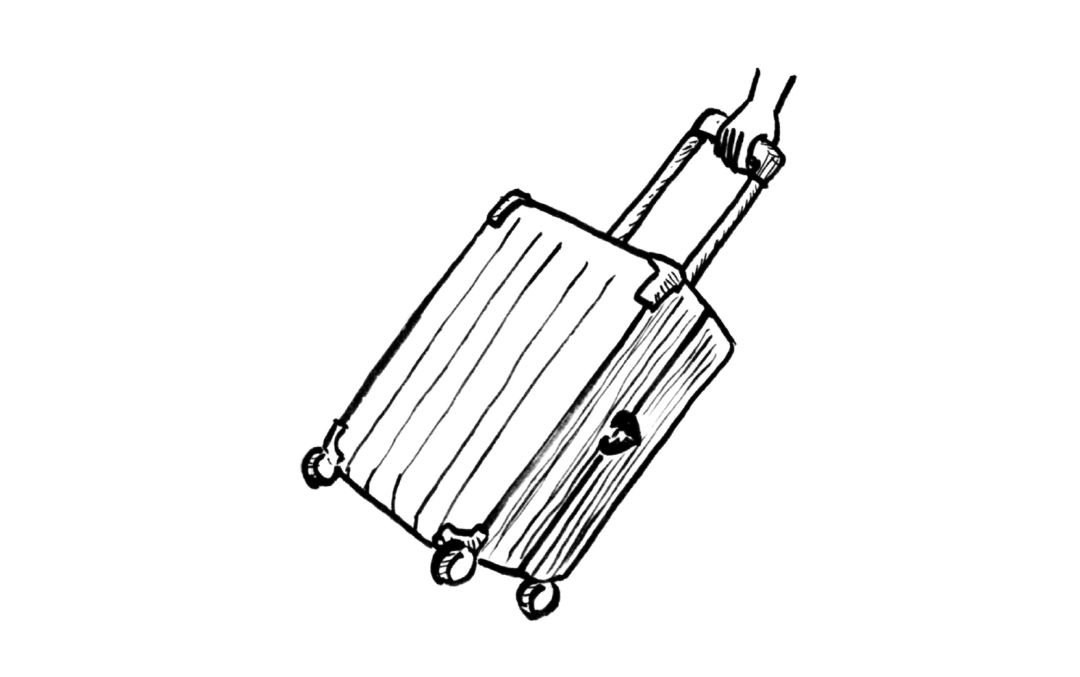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上,大家会用“讨好型人格”这个词汇。张天翼形容自己是一个“深度讨好型”,她记得自己也如故事中的立立那样,时常出现一种倾向,“想要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保持友善,甚至很努力地去结交与讨好对方,力图扭转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好像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一点。”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如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所说,“被要求蜷缩成特定的形状来讨人喜欢”的女性,也有太多如影片《罗马》女主角克里奥那样,永远乖顺地偏着头承受一切降临的女性。《如雪如山》中的主角总在境遇里隐忍,张天翼把这归结于自己“性格里缺乏勇气,比较懦弱,所以写下来的女性总不够勇敢”。但她也努力地在某些人物身上放置一些坦荡与行动力,让泳池里的白衣女子大声呵斥手脚不干净的泳客,让卖场里的柜员们结成相互帮衬、击退逾矩客人的小团体。“人可能都在不断找补”,当被问及她在找补些什么时,她说,“自由,和一张沙发”。
“我说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按照自己真正的心愿、真正的欲望去选择,而不是被迫选择。”
“我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心愿,想要一个单人沙发,它旁边会放一个落地灯,我可以坐在沙发里看书。其实我在淘宝上看了好多,会去想象我坐在它上面的样子。但也只能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去想象下一次满 300 减 30 的时候,能把它买下来。可是并没有发生。
“我跟我先生也商量很多遍了,但是之前住的是租的房子,现在的住处也不大,会冒出来很多顾虑。比如会被说,这沙发比较碍事儿;放家里不好看;格局被破坏了;单人沙发对颈椎不太好,其实并不那么适合久坐……总之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愿望,都这么难以达成。
“希望 5 年内我能有一个单人沙发,绿色的,绒面的那种。可能如果我确诊了癌症,一咬牙,说我这人都快没了,这个沙发必须给我安排,也许就达成了。之后再跟老公说,亲爱的,癌症是误诊,但是这沙发咱还是留着。于是沙发也有了,婚姻也保住了,大概只能是这样。
“现在就缺一个给我开这种单子的大夫,我得在 5 年内认识一个这种大夫,然后这沙发就有准儿了。”

在大概 10 年前的一期《人民文学》上,张天翼曾分享过自己的租客经历。她是“租二代”,小时候家境不算宽裕,跟随爸妈搬过七个住处,它们通常都是局促逼仄的,人与人的距离被迫变得紧密而没有转圜。叙述总与垃圾箱、公共厕所、无所适从的父母联系到一起。但母亲从没和脏乱和解,主动揽下公厕垃圾筐的清理,每天提着兑有消毒液的水桶冲洗厕所,早一遍,晚一遍,哪怕周围邻居毫不动容地每日持续糟蹋着刚刚洗净的地面,“拿李渔《无声戏》里的话说,老天原是要想法子磨灭好妇人。”后来她自己出来租房,母亲还会特定叮嘱,不要怕吃亏,出力长力,尽力多做公共卫生。
她们始终在向那个干净、整洁的应许之地主动靠近,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避无可避的窘迫被她看在眼里。浑浊而恶习堆积的大学宿舍,敝旧脏乱的群租公寓,不得不短暂“与肉体断绝关系”的春运车厢,没有刻意去记,但多年后抬笔一描,“他人即地狱”的窒息感依然很汹涌。不过那是于读者而言的,当事人已经翻篇了。每个人处理历史擦伤的方式不同,“回忆总是最好的除臭剂”,将一件事放置在记忆中时,它便已经不能构成肉体的痛苦与伤害,她甚至饶有兴味地拆解了一下,“等到动笔写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平静中夹杂着一丝愉悦,愉悦中又略有一点感慨,感慨中还带着一些怀念的感觉了。”
不过,发生过的总归是发生了,成长中经受的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可能说要成为真正的自己,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在之前的那么多年里,真正的我已经跟被要求成为的我混在一起,就好像你把桃树的枝嫁接到苹果树上,它们长在一起,然后结出一颗苹果桃。既挖不出苹果的部分,也挖不出桃的部分。”
于是,接下来的课题变成如何接受自己这颗苹果桃,怎么做一颗嫁接水果。苹果桃从小被父母要求做计划,计划需要精确到每个小时,到如今,她对每一天、任何事都需要事先有所计划,迎合的对象纠缠到一起,早就分不清那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选择从事自由职业,是因为它能允许人自由地去给自己做计划。
苹果桃喜欢写比喻句,喜欢在动笔前脑子里已经有画面感。生在曲艺之乡,她从小爱听说书人讲风在天上怎么刮,两个人的兵器闪着怎么样的光,他们在过招的时候,衣服是怎么样地飘动。她偏爱有点字词溢出的小说,不必要每段都准确朝着靶心射去,稍微有点迷迷糊糊的东西,也是迷人的。“《雅歌》里写道:‘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完全不合情理,但句子美就行了,谁顾得上情理?”
苹果桃接受了每个人都会看到一滴不一样的血。女儿眼中他是带来伤害的父亲,以至于需要在长大后写成的幻想小说里,一遍又一遍塑造温柔又宽容的完美父亲,让小说里的女儿浸泡在那样的爱里;邻居眼中他是不赌不嫖,只是偶尔打老婆的家庭支柱;同事眼中他是温吞耐心的老好人。他算得上一个好男人吗?怎么不算呢?
苹果桃小时候很爱欧·亨利,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有机锋,包袱都抖得响,转折带来一种不可替代的阅读快乐,而更要紧的是,看似荒诞无常的落版才是切了命运的题,她觉得一切像那首老歌唱的,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苹果桃初中时暗恋患有“抽动秽语症”(学名妥瑞症)的同桌,她在豆瓣日记里写,男孩会不时像触电一样哆嗦一下,口中念念有词,只不过他念叨的不是“秽语”,而是“我爱你”,有时抽得剧烈,则会连说“爱你爱你”。第一眼她就喜欢上他,每天近距离听着“我爱你”,觉得可爱死了,更加难以抵抗。
那个男孩拒绝她的喜欢时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些,我爱你,真的没兴趣,咱们做一对好同桌就行了吧。
后来一次美术课上她帮他画倒钩球,他道谢时说,对啦,就是这样!爱你爱你。哦,这个背后你给我画上 10 ,就是 10 号的意思。
到现在,每次看到球员倒钩射门,她都会想起他。“不知道他对哪个人说出了第一句真正的‘我爱你’?”
这多像个隐喻,又多像命运。像雪,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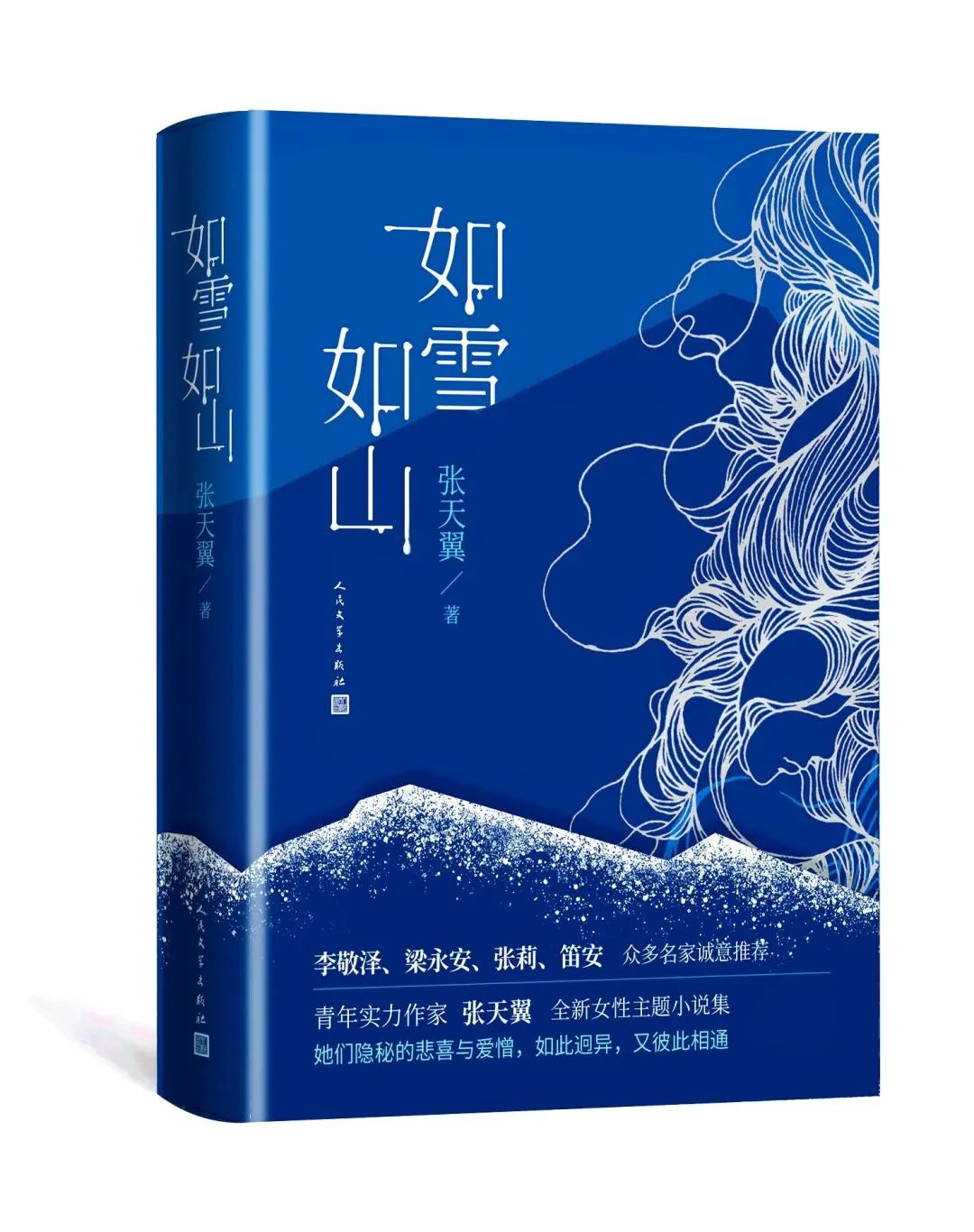
关于张天翼与她笔下的女性生命经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将在评论区抽选 2 位赠送《如雪如山》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