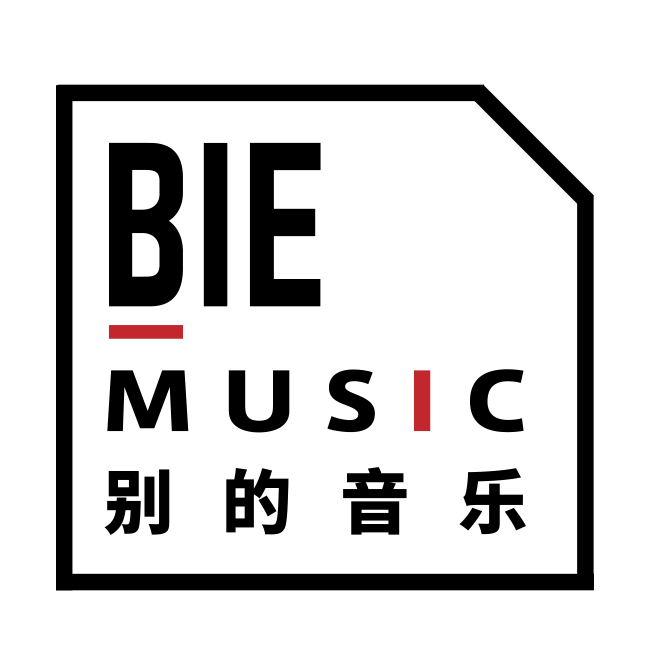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Chinese Musegirls” 是由 M-LAB 与 “BIE别的” 旗下的 BIE别的女孩 和 BIE别的音乐 共同呈现的关于女性音乐人的专题。这期文章介绍的是来自赤瞳音乐的 Sonicave。这里可以听到她们的作品。

有一晚跟Sonicave的女孩们在Nu Space聊到店打烊,那是十月初的成都。
盆地多雨,尤其到了深秋。奎星楼街是个成都的旅游地标,到处都是食肆和小吃摊,到了十点半,从街头到街尾都已经空荡荡。我们在黑了灯的Nu Space门口晃悠,抽了两根烟,祁麟突然说,“陪你走走这条街吧。”
她们刚发了第一张专辑《Rushing Hours》,即将迎来第一次小型巡演,走重庆、成都和昆明三城。但贝斯手狒狒家里突发变故,缺席了一段时间的排练。最近她们都把bassline做成采样,担心如果她来不了,还能有个应对方案。
“紧张,好慌啊。不知道狒狒来不来。” 吉他手Cherry的头发已经被毛毛雨濡湿了。祁麟说,“演出前再排练一次,到时候我再问问她。”
我们闲扯着走到街尾,包子(鼓手)被男友接走,Cherry也打车走了。我上了出租车,看到街对角的祁麟一直站着,好像在确认大家都坐上车了。窗户玻璃上盖了一层细雨,我挥了挥手,也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见。

修打口磁带的 “初四” 女孩
“那会儿我没啥朋友”,祁麟说,“有一个好朋友会弹吉他,我就又强拉了俩姑娘跟我组乐队。”
祁麟读初中那届是 “试验田”,唯一一届 “初四”,而她大概是这学校里唯一一个爱听 “挂在盒子上”、“L7”和 “冷血动物” 的姑娘。拉来三个好朋友,她的第一支乐队就这样组成了,四个女孩,她是鼓手。
其实她更擅长弹吉他,但实在找不到鼓手,就“赶鸭子上架”学起鼓来。她班上有一个男孩爱听摇滚乐,并有个比他大八岁的会打鼓的哥哥。这位哥哥本职是小学老师,还开了间打口磁带的店。祁麟就找他学打鼓,没事的时候去他的磁带店学着修磁带,给他搭把手。那是2002年的内蒙古包头。
那个年头的包头市难找 “排练房”。祁麟租了一间除了电什么也没有的房子给自己的乐队排练,房租一百块一个月。“那会是真的没考虑供暖的问题”,祁麟说,“结果我们四个冬天在那排练冻得瑟瑟发抖。” 祁麟讲到这段往事的时候,Cherry发了一大串 “哈哈哈”,评价了句,“太摇滚了。”
后来祁麟在学校的一次文艺汇演认识了隔壁班一个会打鼓的女孩,“那真是如获至宝,每天往人家家里跑”,最终成功把这位鼓手拉到自己的乐队。她拿回了擅长的吉他,作为主唱,就这样带着她的 “未成年摇滚乐队” 去酒吧演出了。
作为一支学生乐队,在校外的第一次演出评价如何?我问。
“就,不错啊,四个女孩。”
这个评价后来多次出现在祁麟的音乐生活中 —— 她至今的乐队里,乐手们往往都是女孩,而 “性别身份” 在她的生活和音乐里,是个无法忽视的标记。
“那时候组乐队的男生们会觉得我们不行,‘女孩嘛’,他们会这样评价,”祁麟回忆,“其实如果是善意或者描述性的 ‘全女子乐队’,我是无所谓的,但有人听到 ‘全女子’乐队就会说一句,‘哦,那挺不容易的’,我就觉得,哪不容易了?”
虽然可能是善意,但已然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
Sonicave的后朋式冷感和女孩间的细腻
祁麟大学毕业后从内蒙迁到成都定居。Sonicave组起来犹如网友见面:通过贴吧和豆瓣认识,四个人截然不同,好运的是,她们作为乐队成员出乎意料地合拍。
Cherry和狒狒性格内向,之前在同一支朋克乐队里,共同经历过几次完全 “嗨不起来” 的尴尬舞台,“朋克嘛,你好像得躁起来才行,可我们蹦不起来,台下的观众也一脸懵”。这事儿被Cherry一笑带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Sonicave很合适我们。” 冷冽、带着紧绷和躁郁气质的后朋克(post-punk),意外地让她们找到了舒服的表达方式。

图片均由 Sonicave 提供
起初是祁麟给乐队定下了基调。她偏爱后朋克和暗潮多年,对于 “Sonicave要什么样的声音” 想得很明白。四个女孩磨合起来非常快,不再需要强装姿态,在后朋克 “自闭” 又自省的基底中,她们找到更多的发挥和延展空间。尤其在发现了Savages——四个一袭黑衣的酷女孩——之后,她们找到与自己的共通之处。
她们再各自汲取养分(可以来听听这期 Podcast 中四个人分别做的歌曲推荐):从经典中的经典The Cure、Pink Floyd和Portishead 得到长久的灵感;从更加冷冽的The Soft Moon中获得些躁动的、工业的气息;再到Black Midi和 Modest Mouse的打破框架,如果能像他们一样娴熟地将喜欢的元素信手拈来是更好……在这之下,你听到的《Rushing Hours》或许不是一张 “前卫” 的专辑,但确实是一张暗含深意,成熟而且完整的作品。
第一首 “Happy Birthday Suit” 寓悲于喜,是颓丧又想把一切嚼碎的狠,踏着沉重的脚步向你缓缓走来:“来吧,学会自怨自艾,或者埋怨他人,你准备好了吗?” 中间的 “Rushing Hours” 瞬间提速,久久延迟的噪声中是祁麟的声音 “你大声叫喊,不甘为人妇”。而 “Dear Psycho” 作为终曲则是寓喜于悲,“亲爱的疯子,你还会被比作那永不能痊愈的溃疡吗?”满是同情又满是冷漠。

舞台上的Sonicave用厚重的眼线和一袭黑色将自己武装,显得冷淡、悲观、不易近人,但乐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关音乐,更是生活方式本身。在生活细节里的 Sonicave 其实充满温存。

她们的日常话题围绕着聊猫猫狗狗,分享好用的猫砂盆和优质猫粮,偶尔是Cherry分享美妆。巡演的日子里,四个人总聊到到凌晨四点才睡。
当被问到这个团都是女孩是不是巧合,Cherry说,“我还真的没法跟男生组乐队。除了我的男朋友,从小到大我的男性朋友都很少。”
“为什么?” 我很好奇。Cherry很漂亮,一头卷发过肩。排练房那天她穿了一身紫色的皮质大衣,腰线收紧,画了淡妆,红棕色的唇膏下嘴唇抿着。她踩了脚失真,太飒了。
“就是,没有共同话题,聊不起来。” Cherry显得很无奈。“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大家都很真诚,但就是……无法持续聊天,话不投机半句多。” 祁麟解释了下,“我觉得在一个乐队里,需要互相理解和信任,才能在音乐上更加顺畅地提出意见和沟通,所以聊得来很重要。”
包子则是第一次跟三个女孩一起玩乐队,起初还有些不习惯 —— 之前的两支乐队都跟男孩一起,乐队也是更内向的 Shoegaze(钉鞋)风格,“我有时候都忘了自己是个女生”。她一头短发,圆圆脸,抗拒化妆,演出就穿一件黑T恤。她享受 “规律”,每天五点准点起床健身;也享受 “打破规律” 的快感,在我们电话聊天的当下,她忽然说了一句,“我刚辞职了”,就在三十秒前。
但每当进入 “美妆话题” ,包子还是有点不知所措:“我感觉突然找回了我的女性身份,适应了好一段时间。”她仍然抗拒化妆,每回演出得祁麟按住她,让Cherry 给她涂上薄薄一层口红,算作 “完成任务”。
“我们并不是腻在一起的那种姐妹淘。” 四个人最长与最小相差十岁,个性也很不同,却有着简单直白,又细腻互通的理解和依靠。


十年后,我会不会变得不勇敢?
十多年过去了,祁麟和当初和她在内蒙玩乐队的姑娘们都步入而立,分道扬镳之感愈发明显起来。
“初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但现在已经聊不到一块去,她们变得更像我的父母辈了。“ 祁麟发觉,当家庭占据一个女人的全部注意力,她对一些细节和话题会不再保持敏感,或者说,无暇再顾及,这时候如果若没有警惕心,就很容易被迫坠入 “家庭主妇” 的漩涡里,不再拥有年轻的思考力。
当老友见面时尴尬的沉默时间越来越长,或者强行让不感兴趣的话题继续下去的时候,祁麟觉得遗憾而且难过。
这些选择都没有错,女人在 “三十岁” 这个节点需要面对的社会规则和强迫性选项太多,而祁麟跟好朋友们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在思考女性价值和面对这些矛盾与差异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种怀旧和温情:“我还是会珍惜她们,会保持联系,即使交谈只能止步于追忆过去,因为我无法再去交一个相识二十年的好朋友。”
这些作为女性的生存体验也透露在Sonicave的音乐里,“反反复复的迷茫,痛苦的清醒和怠惰的沉沦交织,简单纯真的东西转瞬即逝”。《Rushing Hours》里有一首歌叫《She Dreamt about a Witch Last Night》,传达出《使女的故事》一般的意象,她说虽然创作时没有参考,现在想起的确非常契合,那是从一个女人的视角里经历的爱情、重压、荒谬和人生变动。
祁麟没有选择婚姻和家庭生活,她留在成都,留在音乐里,但在采访的时候,她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我担心自己会越来越不够勇敢。”
二十出头的女孩们笑着说,“我应该不会有什么改变,吧?” 带着一点天真和不确定;而祁麟则笃定地补了一句,“我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十年后,我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