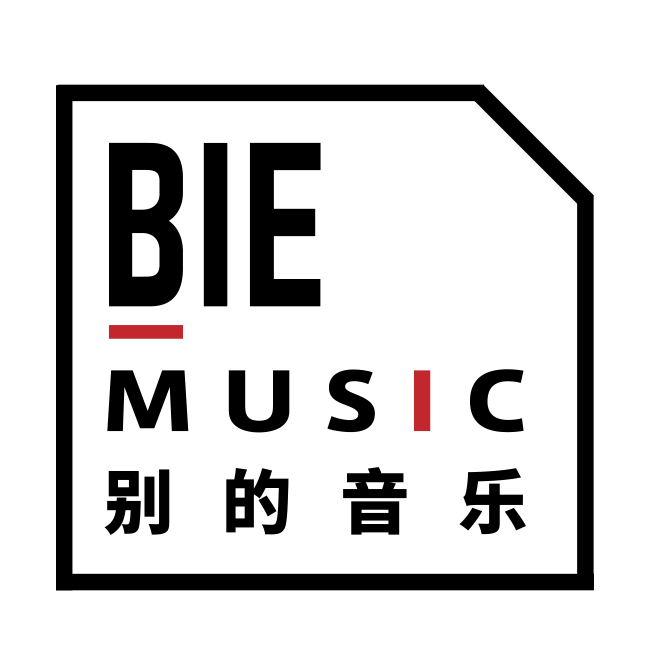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9 月 9 日)刚从朋友间传来的噩耗—— Silver Apples 的 Simeon Coxe III 辞世,享年 82 岁。
以下是 Simeon 和 Silver Apples 的一些背景故事:
在电子琴和合成器还没有面世的年代,Simeon 利用各种年代久远的震荡器,配合电报机和其他垃圾零件,制造出他的电子乐器 “The Simeon”,和鼓手 Danny Taylor 组成二人组 Silver Apples 银苹果在纽约首次制造电子音乐,推出了首张同名唱片。不幸的是他们于第二张唱片《Contact》内,因为两人坐在泛美航空客机的驾驶舱的封面,配上了两人坐在飞机失事现场的封底照,卷入了严重的法律纠纷:唱片被逼下架,唱片公司倒闭,两人也逃离纽约,乐队从此音讯全无……

一直来到九十年代,Simeon 在柏林某唱片店偶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才意识到原来 Silver Apples 的声音并没有随着乐队而消失,也因为航空公司倒闭,他才又以 Silver Apples 的名义继续创作和演出;没多久之后,在某次的深夜电台节目中,刚播放完 Silver Apples 歌曲的节目主持人收到鼓手 Danny 的电话查询,两人才又得以见面并重新继续这二人组,发行了 Danny 在家中保存多年的录音,他们的第三作《The Garden》和《Decatur》。

但好景不常,两人在 1998 年的巡演路上遇上事故,Simeon 受到重创而被逼停止所有演出和录音的计划。半边身体失去了触感的 Simeon 在康复期继续跟 Xian Hawkins 共同创作,而鼓手 Danny Taylor 则于 2005 年与世长辞。带着 Danny 练习时的鼓声采样,Simeon 于 2007 年再次复出,在世界各地继续 Silver Apples 的演出,也同时跟一起多年的女友 Lydia Winn LeVert 组成 Amphibian Lark 并且发行了两张专辑,而Simoen 最后的作品是为 2016 年 Silver Apples 的《Clinging To A Dream》专辑。
我对 Simeon 的回忆:
Simeon 是在 2011 年来到中国的,当时 “玫瑰楼模拟” (憬观:像同叠、Soviet Pop、金司机和 TR)在 Michael Pettis 先生的协助下举办了 Silver Apples 的三城巡演。已经忘了是高铁没通车还是要控制成本,我们安排了整个团队一起乘坐卧铺启程。但由于 Simeon 在第一程火车之后觉得睡卧铺没有隐私,所以临时安排了我来跟他改乘飞机,我也因此成为了他在中国的两个礼拜每天照顾他起居的助手。

机场送行
Simeon 十分平易近人,我还记得团队在第一次跟他晚饭见面后,大家都想:Simeon 的眼神锐利,更像是一个拥有 73 岁的身体里的年轻人,我还记得大家都暗地里说他年轻时肯定是个狠角色,实在非常庆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他认识。
下面就不分时序,边想边写出跟Simeon 的一些回忆,以此纪念这位真正伟大的人类:
- 应该是第一晚我和李文泰从愚公移山送 Simeon 回到三里屯的酒店,我问他对于自己当年创造了一个新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感觉,Simeon 眼睛似是看着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回想起来,然后说他看到台下的人都是目瞪口呆,根本给不出反应。后来多演了几次之后观众才开始对这最早期的电子音乐投入起来。李文泰接着问他是怎样操作自己 “The Simeon” 电子乐器。在前往三里屯的出租车后座内,坐在我们中间的 Simeon 开始用他还没完全康复过来的身体,一直示范怎样用左手按着电报器,右手摇着振动器,怎样勉强用手肘来按出其他音色,但同时间双脚还把低音的旋律踩出来,再同时唱歌。对看一眼之后我和李文泰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然后我们在三里屯酒吧街北口下车。
- 某一天我们在鼓楼的 Alba 天台吃饭(因为他吃腻了中国菜),他突然间问为什么北京是这么的一块大平地,后来才觉得他这个观察还真的挺不正常(又准确)的。

老莫餐厅
- 来到我们和 Soviet Pop 在六铺炕的排练房,他觉得我们都用年代老旧的器材有点不明所以,因为对他来讲他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科技革新和更方便使用对他来讲是好事,反而是我们后来的人才喜欢往回追求那个年代不方便使用的器材。离开的时候闻到地下车库的异味,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反而说:“这没什么,我去过英国那些小孩的排练室,环境也差不多。” 那些小孩包括 Blur 和 Portishead。
- 在北京场的调音时间,Simeon 坐在台前的楼梯上一直在细心聆听 Soviet Pop 的试音,那种依然在观摩其他乐队的好奇心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

憬观长城
- 在北京场的后台演出前,他跟我聊起来当年 Andy Warhol 尝试让他们组成 “Silver Apples & Ultra Violet” 跟地下丝绒一起成为他的乐队。Simeon 说起来还是十分激动,觉得自己绝对不可能跟那些“投机艺术家” 合作。我打圆场用脏话骂了 Andy Warhol 几句,Simeon 听到表示:“你可以这样说,但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 九十年代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有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用了 Silver Apples 的名义在纽约演出,也因为这样导致他被误以为是假的银苹果。后来我怎样查也查不到有关于这个事情的纪录,但我清楚记得当时 Simeon 那个愤怒到极点的表情。他气的并非有人冒充他,而在于 “为什么有人会空虚到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是自己?” 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人,替他焦急。
- 还有,他在酒店门收集了很多印上美女的卡片,Simeon 收集了起来全部送了给我……
更多零碎的记忆没有办法细说,但无论作为一个音乐人,或者是人类,Simeon 都是我最尊敬和仰慕的人,留下改变世界的音乐但同时过得淡薄。希望他能得到安息,也希望陪着他到最后的爱人 Lydia 可以释怀,节哀顺变。
谢谢 Simeon 送给我们的音乐。

愚公移山 by Reonda
作者//吴卓
(9 月 9 日)刚从朋友间传来的噩耗—— Silver Apples 的 Simeon Coxe III 辞世,享年 82 岁。
以下是 Simeon 和 Silver Apples 的一些背景故事:
在电子琴和合成器还没有面世的年代,Simeon 利用各种年代久远的震荡器,配合电报机和其他垃圾零件,制造出他的电子乐器 “The Simeon”,和鼓手 Danny Taylor 组成二人组 Silver Apples 银苹果在纽约首次制造电子音乐,推出了首张同名唱片。不幸的是他们于第二张唱片《Contact》内,因为两人坐在泛美航空客机的驾驶舱的封面,配上了两人坐在飞机失事现场的封底照,卷入了严重的法律纠纷:唱片被逼下架,唱片公司倒闭,两人也逃离纽约,乐队从此音讯全无……

一直来到九十年代,Simeon 在柏林某唱片店偶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才意识到原来 Silver Apples 的声音并没有随着乐队而消失,也因为航空公司倒闭,他才又以 Silver Apples 的名义继续创作和演出;没多久之后,在某次的深夜电台节目中,刚播放完 Silver Apples 歌曲的节目主持人收到鼓手 Danny 的电话查询,两人才又得以见面并重新继续这二人组,发行了 Danny 在家中保存多年的录音,他们的第三作《The Garden》和《Decatur》。

但好景不常,两人在 1998 年的巡演路上遇上事故,Simeon 受到重创而被逼停止所有演出和录音的计划。半边身体失去了触感的 Simeon 在康复期继续跟 Xian Hawkins 共同创作,而鼓手 Danny Taylor 则于 2005 年与世长辞。带着 Danny 练习时的鼓声采样,Simeon 于 2007 年再次复出,在世界各地继续 Silver Apples 的演出,也同时跟一起多年的女友 Lydia Winn LeVert 组成 Amphibian Lark 并且发行了两张专辑,而Simoen 最后的作品是为 2016 年 Silver Apples 的《Clinging To A Dream》专辑。
我对 Simeon 的回忆:
Simeon 是在 2011 年来到中国的,当时 “玫瑰楼模拟” (憬观:像同叠、Soviet Pop、金司机和 TR)在 Michael Pettis 先生的协助下举办了 Silver Apples 的三城巡演。已经忘了是高铁没通车还是要控制成本,我们安排了整个团队一起乘坐卧铺启程。但由于 Simeon 在第一程火车之后觉得睡卧铺没有隐私,所以临时安排了我来跟他改乘飞机,我也因此成为了他在中国的两个礼拜每天照顾他起居的助手。

机场送行
Simeon 十分平易近人,我还记得团队在第一次跟他晚饭见面后,大家都想:Simeon 的眼神锐利,更像是一个拥有 73 岁的身体里的年轻人,我还记得大家都暗地里说他年轻时肯定是个狠角色,实在非常庆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跟他认识。
下面就不分时序,边想边写出跟Simeon 的一些回忆,以此纪念这位真正伟大的人类:
- 应该是第一晚我和李文泰从愚公移山送 Simeon 回到三里屯的酒店,我问他对于自己当年创造了一个新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感觉,Simeon 眼睛似是看着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回想起来,然后说他看到台下的人都是目瞪口呆,根本给不出反应。后来多演了几次之后观众才开始对这最早期的电子音乐投入起来。李文泰接着问他是怎样操作自己 “The Simeon” 电子乐器。在前往三里屯的出租车后座内,坐在我们中间的 Simeon 开始用他还没完全康复过来的身体,一直示范怎样用左手按着电报器,右手摇着振动器,怎样勉强用手肘来按出其他音色,但同时间双脚还把低音的旋律踩出来,再同时唱歌。对看一眼之后我和李文泰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然后我们在三里屯酒吧街北口下车。
- 某一天我们在鼓楼的 Alba 天台吃饭(因为他吃腻了中国菜),他突然间问为什么北京是这么的一块大平地,后来才觉得他这个观察还真的挺不正常(又准确)的。

老莫餐厅
- 来到我们和 Soviet Pop 在六铺炕的排练房,他觉得我们都用年代老旧的器材有点不明所以,因为对他来讲他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科技革新和更方便使用对他来讲是好事,反而是我们后来的人才喜欢往回追求那个年代不方便使用的器材。离开的时候闻到地下车库的异味,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反而说:“这没什么,我去过英国那些小孩的排练室,环境也差不多。” 那些小孩包括 Blur 和 Portishead。
- 在北京场的调音时间,Simeon 坐在台前的楼梯上一直在细心聆听 Soviet Pop 的试音,那种依然在观摩其他乐队的好奇心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

憬观长城
- 在北京场的后台演出前,他跟我聊起来当年 Andy Warhol 尝试让他们组成 “Silver Apples & Ultra Violet” 跟地下丝绒一起成为他的乐队。Simeon 说起来还是十分激动,觉得自己绝对不可能跟那些“投机艺术家” 合作。我打圆场用脏话骂了 Andy Warhol 几句,Simeon 听到表示:“你可以这样说,但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 九十年代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有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用了 Silver Apples 的名义在纽约演出,也因为这样导致他被误以为是假的银苹果。后来我怎样查也查不到有关于这个事情的纪录,但我清楚记得当时 Simeon 那个愤怒到极点的表情。他气的并非有人冒充他,而在于 “为什么有人会空虚到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是自己?” 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人,替他焦急。
- 还有,他在酒店门收集了很多印上美女的卡片,Simeon 收集了起来全部送了给我……
更多零碎的记忆没有办法细说,但无论作为一个音乐人,或者是人类,Simeon 都是我最尊敬和仰慕的人,留下改变世界的音乐但同时过得淡薄。希望他能得到安息,也希望陪着他到最后的爱人 Lydia 可以释怀,节哀顺变。
谢谢 Simeon 送给我们的音乐。

愚公移山 by Reonda
作者//吴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