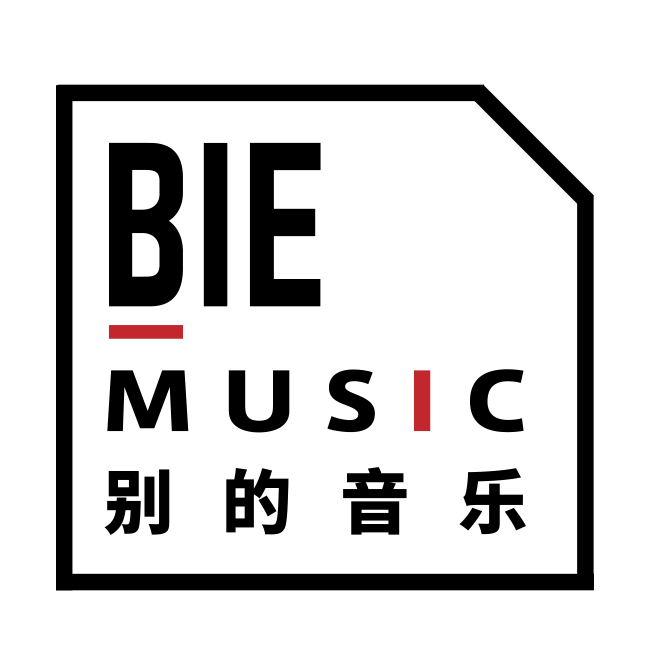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Chinese Musegirls” 是由 M-LAB 与 “BIE别的” 旗下的 BIE别的女孩 和 BIE别的音乐 共同呈现的关于女性音乐人的专题。这期文章介绍的是来自野生唱片的浪味仙贝灵魂人物 Zoo。这里可以听到他们的作品。
青春期:不再自信

有勇气在人前唱完歌的 Little Zoo
进入青春期之后这种充满勇气和自信的行为销声匿迹,因为她开始长大了 —— 这意味着,“性别” 身份开始愈发重要,“别人的意见和评价” 成为她评价自己的标准之一。Zoo的自信开始丧失,她的话越来越少,在班级里难得吭声。“我就属于那种,成绩普通,长相普通,运动也普通的女生”,她补充了一句,“偶尔心里有点叛逆。”
“叛逆在哪里?” 我问。
“听摇滚乐,觉得很多事情的存在都挺傻的,但我不会说,就心里觉得。”
在学业重压的高中和不谙世事的小学之间,初中生不够成熟的心智与加速发育的生理混合成少不经事的鲁莽。“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女同学一起放学回家,遇上她的小学同学,是个男生,他们一起走了一段”,Zoo在电话另一头回忆起十几年前,“那男生走了之后,我同学告诉我,’他刚跟我说你长得丑’。”
Zoo 停顿了一下,“那时候不懂事,但确实挺伤人的,我一直记得。” 不够苗条,不够漂亮,成绩不够拔尖,“自信” 莫名消退,让她在二三十个人的班级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感。她开始刻意尝试融入。
运动会是个好机会,班上运动神经发达,又长相姣好的男女生们总是不缺人缘。那一届运动会 Zoo咬了牙报了个800米跑。“我觉得这样就能跟他们搭上话,聊聊天然后融入他们”,但依旧事与愿违 —— ”没跑完,耐力不行,不擅长运动“。尝试了几次无果后,她倒放下了这段心事,因为时间替她解决了问题:高中后,学业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注意力。她依旧话少,一头短发,朋友不多;把空闲留给自己听歌,从涅槃(Nirvana)到彩虹(L'Arc en Ciel),她开始觉得既然能互相理解的人这么少,过度交往无益;但那份 “不自信” 却一直留了下来,时间没能改变它。

后青春期:女儿晚熟
摇滚乐一直伴随着她的青春期,也帮她解决了一系列人际关系上的难题:大多数人都聊不来,那就别做朋友了,毕竟人类的缺点太多了,无法互相容忍。“有时候也自己跟自己别扭”。
这种 “别扭” 与她对自己的高要求不无相关。这两年她爱听的东西一下子过渡到了fusion和 cool jazz,当流行与爵士的灵动随性相遇,又不拘于形式地与电器化相融合,从Paul Desmond《Music and Lights - Bossa Nova Only》,到砂原良德的《The Sound of 70's》,流行爵士和布鲁斯融合透着 “新” 的气息,而她对涩谷系乐队的疯狂迷恋也一下子拉高了她对自己做音乐的标准。“他们(涩谷系乐队)没有模版,每一支都不一样,充满独特,那就是我做音乐的理想化状态,但目前能力问题,做不到。”
“做不到”、“不够好”、“没进展”,诸如此类自省的词汇频频出现在我们最初的对话里,她的语气里带着认真,所以更显得严肃,时常让我语塞,不知道怎么接话——好久没遇到不带任何戏谑和自嘲,冷酷直面问题的聊天对象了。
她提到自己喜欢的Chara和椎名林檎,羡慕她们作为女人的自由和充分自信,“坦然接受自己的缺陷,不刻意去弥补“,这是她认为女性的美之所在,所以也常常对于城市内遍布的医美广告感到生气。”我觉得美或者不美,都要展现出来,我想要成为这样。”
但她又是个矛盾体,“较劲” 也在此处:她知道自己缺陷,却无法像希望的那样坦然面对,仍然被不自信束缚着;音乐上也是,有了想要达到的标杆,却触摸不到。
“浪味仙贝“ 这支乐队能玩起来是偶然,因祸得福于Zoo的一次骨折。
她研究生期间在武汉Vox打工,认识些玩滑板的同事。“我特爱跟他们玩,也不多话,你玩就很认真地教你,玩多了就互相熟悉了。” 有回玩板的时候不小心,她把双踝两侧的骨头给摔裂了。一场大手术后修养的几个月里,也不能玩板,她就呆在家里安心练琴,注意力终于都放在了乐队上。
这次意外摔伤居然也渐渐治好了Zoo的 “后青春期综合症”。“我住院那期间,同事们有事没事都来看我,觉得特别感动”,从周遭人中得到无限关怀的Zoo开始自愈,不论是受伤的双踝还是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我开始能更多看到人身上的优点,很多人虽然挺傻的,但还是有优点的,渐渐地觉得自己也不那么拧巴了。”
比如自己的 “美与不美”,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生活中的存在开始不那么刺眼了,她开始学会如何跟这些 “不完美” 相处。在这个过程中,“自信” 也慢慢找到回家的路。
“放弃自我” 中,求得自我
与覆盖了她整个青春期的少言和 ”不自信” 相反,作为浪味仙贝里唯一的女孩,Zoo一点也不少言和畏缩,”她有时候像个女领导”,贝斯手赵宸笑说。
“没想到吧,没想到吧!” 她终于松弛下来,开始戏谑自己性格中的反差。
“我开始排练的时候都不说话”,赵宸说,“被她带的我也开始会发表意见,觉得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她对自己的严苛转而投射在乐队上,“我在乐队里是挺强势的”,她说得干脆利索,“对自己在乎的事情我总是变得很严肃。”

浪味仙贝的4.0阵容
《东湖游泳》发行后,去年夏天Zoo面临毕业。在发行了一首单曲《爱的招待》之后,她决然选择给自己换一个环境,离开待了7年的武汉,去到杭州,“想要用新环境给自己的音乐来带些新东西”。乐队排练成了头个棘手难题,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有限,Zoo只能每月从杭州回去武汉一次,乐队的整体创作也陷入停滞。解决办法得找,他们也开始尝试 “互联网作业”,通过互传工程文件来继续共同创作,“但目前看来收效甚微”,Zoo笑笑说,这个难题还有待克服。
但在新的环境里,她开始逐渐找到自己的平衡。
“之前老想着 ‘自我’,从内而外都很别扭;但现在尝试坦然接受缺点,理想的状态是,自然开朗”,她说,“但目前我还达不到。”
女儿晚熟,大学四年都泡在图书馆和宿舍的一部部电影里,Zoo很少外出去玩,生活似乎与 “典型女大学生的日常” 相差甚远:恋爱、美妆、蹦迪、喝大酒,都没有。化妆被视为 “当代女性基本技能”,可直到研究生开始兼职的时候 Zoo才第一次拿起口红和眼影。
内在的叛逆只是她精神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的 Zoo崇尚自律,享受着规律生活带来的安全感。在这个安全感之内,她又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试探边界:毕业后离开已经熟悉的城市,却仍选择留在独立音乐厂牌工作;浪味仙贝经历了四次乐手更替,现任吉他手也将去日本留学,她再一次找到能共同前进的新朋友加入,踏平困难……她在安全区内小心翼翼地往外拓展,维持着躁动与自律的平衡。
这种因为对生活不够娴熟的 “试探” 让她会好奇衰老。“我有时候好奇那些比我大的、很勇敢自我的女音乐人,想生孩子就去生了,结婚离婚,在经历这些之外还能继续作出好音乐,自己的生活和音乐都兼顾着,就觉得真厉害,想知道在那个年纪的我是否也能这样……” 人生只有一次,却没机会彩排,捱过了试错的年轻,Zoo正在逐渐变得熟练,也开始与自己的一切存在共处。
她的后青春期,终于快要过去了。

中间的是 Zoo,以上所有图片均来源于浪味仙贝乐队
//设计:雪花
//编辑:Alexwood,赵四
//感谢:野生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