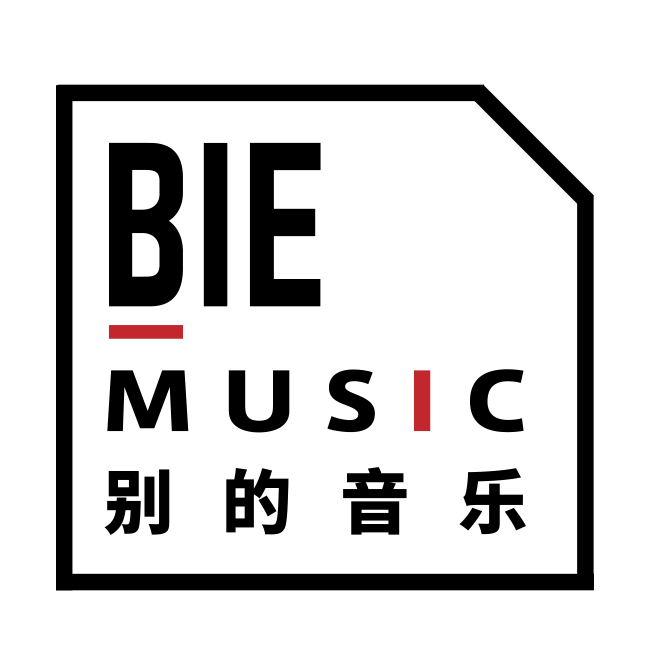这是日本独立乐队 DYGL(读作“dayglo”)第三次参加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的西南偏南音乐节(SXSW)了。
2013年成立于东京的 DYGL 由主唱兼吉他手秋山信树,吉他手下中洋介,贝斯手加地洋太郎和鼓手嘉本康平所组成,现旅居伦敦。除了吉他手下中以外,其他成员都曾在另一个也由秋山发起的乐队 Ykiki Beat 中担任角色,只不过获得了短暂的商业成功的 Ykiki Beat 还是在2016年宣布了活动休止。
与广泛运用合成器的 Ykiki Beat 不同,DYGL 玩的是相当扎实的吉他摇滚,带着股2000年初车库和后朋克复兴的狠劲儿。他们凭一己之力把复古浪潮推回时尚尖端,很快成为了独立音乐新世代中最具代表性的面孔之一。
海外生活
与他们前两年参加 SXSW 时相对清闲的日程不同,今年的 DYGL 被满满当当地订了八场演出。乐队成员跟我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像那么回事”的 SXSW,还坚持辩解说他们眼睛下的黑眼圈跟短时间内密集的演出没关系,只不过是因为宿醉而已。
对于市郊废弃仓库粘稠地板上的即兴演奏,或是 Red River 大街上纵情的酒精狂欢,DYGL 都早已轻车熟路了。这几个小伙子不管是跟 The Chills 这样的大牌乐队共演一场人头攒动的午夜派对,还是在只有几个熟人在舞池里晃悠的德州 BBQ 馆子的 happy hour 前来个暖场,他们都维持着松弛自在的状态。他们每场的演出曲目都会根据场合悉心调整,气氛也总是欢愉而热烈的。
不过,这看似无尽的嘉年华对乐队成员本身来说,也未必总意味着欢乐。那天,与 DYGL 很久没见过面的我在他们刚演出完的场地外碰到了吉他手下中。他当时手里攥着电话,一脸的烦躁。我试着打了个招呼,他先是一惊,却又严肃地“嘘——”了我一下,转身一头扎回他那看似紧绷的对话中去了。晚上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满怀歉意地跟我解释说他当时是在跟日本的女朋友讨论一些要紧事。当然,完全,可以,理解。

吉他手下中洋介
“长期保持这样的国外生活和巡演状态,你会有孤独感吗?”我问。我知道这个夏天就要发行新专辑的他们为了录音,住在伦敦东北部有好一阵子了。
下中马上摇头否定了,“我倒不怎么孤独,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我也并不想念日本,但确实很想念我在日本的亲友们。家人,女朋友和好友们都在千里之外,有时候是挺叫人难过的,不过只要想到这些都是为了音乐,那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我很好奇能否把呆在伦敦这件事看作他们现在做音乐的一个必要元素,毕竟 DYGL 的音乐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这片土壤孕育的。下中再次否认了我的猜测,不过也承认伦敦确实是录音的好地方。他还跟我说,新专辑完成之后,乐队可能会重新研讨要不要继续住在伦敦。现在没什么是板上钉钉的。
一些翻唱,和大都会棒球队
在 DYGL 那晚的演出前,我给乐队成员塞了几包“中南海”牌香烟。他们激动得不行。通常以中国政界高层的居住地为人所知,饱含政治隐喻意味的“中南海”,同时也是由中国地下音乐的标志性乐队 Carsick Cars 创作的一首名曲的名字。DYGL 在第一次来中国巡演时不但翻唱了这首歌,还顺便迷上了“中南海”牌香烟的滋味。
DYGL 很喜欢在海外巡演时翻唱本地出身乐队的经典作品。2015年他们在纽约最早的几场演出里,有一场在一个叫 “柏林”的本地小酒馆,一首 Ramones 的 “I Wanna Be Your Boyfriend”让他们很快与观众拉近了距离 。这次在 SXSW 也不例外。在烤肉馆子 Cooper's 阁楼上的一群烤牛腩爱好者面前,他们翻唱了 The Kinks 的 “So Tired of Waiting for You” ,也赢得了台下不少会心的眼神。
在 Cooper's 的演出结束后,我们去了旁边一家酒馆,打算喝上几杯奥斯汀最好的生啤。当被问到为什么这次翻唱 The Kinks,以及谁来决定翻唱曲目时,秋山说基本上是由大家一起决定的。

主唱、吉他手秋山信树
在 DYGL 开始新专辑的录音前,乐队曾经开了个会来讨论接下来做什么感觉的声音比较好。秋山觉得,他们的处女专《Say Goodbye to Memories Den》只能看作是一个歌曲合集,没什么整体性。但这一次,既然大家最近发掘了不少新的音乐流派,他认为在新专辑的制作风格上有必要让全体成员的意见保持一致。
几轮讨论下来,乐队倾向于了60年代以后,相对老派的车库风格 —— “说实话60年代本身就够信息量巨大了。”他们觉得 The Kinks 的音乐超酷的,巡演路上也老是拿来听。“现场演奏他们的歌挺能激发我们的灵感的。”
我说:“你们之前翻唱的那首 Buzzcocks 也挺不错的。”那首翻唱收录在一张由 Rhyming Slang 发行的欧美朋克名曲的翻唱合辑中。Rhyming Slang 是一家专注于独立音乐社群的活动组织。它的创始人铃木知美,是东京地下音乐圈中很有地位和影响的一位女士,据说很受本地青年乐队的尊敬。
DYGL 的成员们对于我竟然知道那张翻唱专辑的存在感到震惊。似乎当时的发行范围并不大,也没做什么宣传。

“不是有互联网吗!”我不禁笑了出来。
下中听了后做了个鬼脸,他一直都对当今的赛博生活和社交网络心存芥蒂。在我们去年的采访和聊天中,他都对这一点毫不掩饰。他觉得互联网把人类的隐私强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这件事很糟糕,毕竟又不是谁都喜欢天天直播自己的生活的。
“不过我也不是一点都不喜欢上网。我天天泡在 YouTube 上看视频。”
我问他一般都看什么样的视频,他先说不能告诉我,在我的坚持下,才勉强承认他看很多日本网红的搞笑视频,有时候也看一点音乐或者职业棒球相关的东西。他说他支持纽约大都会队(the New York Mets),还说,“洋基队(注:the New York Yankees,大都会队的死对头)倒也不是不行,就是有那么点……”
我举起一只手叫他别接着说了,因为我是洋基队的粉丝。
做音乐,也交一些新朋友
乐队的早期,还是在叫 DYGL 这个名字以前的时候,秋山,下中和嘉本组过一个叫 De Nada 的“副本乐队”。在这个乐队里,成员经常交换着乐器来创作,大部分时间都是秋山打鼓,嘉本弹吉他。这段时光里,一首美丽而柔和,又注入了乡愁感的曲子“Nashville” 诞生了。从那以后差不多过了七年,DYGL 再次把这首歌搬到了 SXSW 的舞台上,却是以当前乐队的分工来演奏的。
我对秋山表示了想在 SXSW 看到他打鼓的愿望。他说他也想,但是器材设备都有限制,而且对这首歌,目前乐队还停留在探索编曲的阶段,研究着怎么改才能让这首歌在新专辑里合群,这次也是想从现场中得到一些启迪。
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乐队试着跟当时的两位制作人,也就是 The Strokes 的吉他手 Albert Hammond Jr. 和制作了 The Strokes 后两张专辑的 Gus Oberg 说过,能不能把这首歌加进去,但后来发现确实不是很合适。这回又发新专辑,秋山想再试一试。
贴心的加地告诉我其实他们做了另外一首曲子,里面是秋山打鼓,嘉本弹贝斯。但是他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首歌会不会在新专辑的最终阵容里。

贝斯手加地洋太郎
上个月,DYGL 发行了睽违已久的新单曲“A Paper Dream”。这张单曲距离上一张“Bad Kicks”的发行已有一年了。两张单曲都也是正在制作他们新专辑的制作人 Rory Attwell 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A Paper Dream”的录音是在 Stereolab 的鼓手 Andrew Ramsay 开的录音室 Press Play Studio 完成的。加地对于这个录音室里的设备和器材津津乐道,“他们那儿的鼓,哇,都是最顶级的。”
在新单曲的MV里,加地弹奏着一把古典低音提琴,很符合他的气质。可当我向他提起来这码事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下中突然爆笑起来。加地看起来更害羞了,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就是在那假装弹呢。那把琴就放在那,大家都觉得拿来拍摄应该效果挺好的。那是我第一次碰这种乐器,根本不知道怎么弹。”大家没看出来,说明装得还挺像样的。

贝斯手加地洋太郎
曾来过中国巡演,现在活动已休止的乐队 Splashh 的吉他手 Toto Vivian 执导了这首歌的MV。从以前就很欣赏 Splashh 的秋山在看了由 Vivian 亲自执镜的 Splashh 美国巡演的纪录片之后,对片子的拍摄手法着了迷,“光怪陆离,扣人心弦,带着种酷酷的波普感。重要的是又很切题。”他当即联系了 Vivian。
Vivian 先是帮 DYGL 拍摄了“Bad Kicks”的影片,这回又包揽了“A Paper Dream”。这一次的拍摄,原本最受乐队成员欢迎的提案是做成一个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来配合怀旧气息满溢,带有歌谣感的旋律,可是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而从头改造一个新场地所需的费用又超过了他们的预算,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期间,得知 DYGL 在找人设计单曲封面后的 Vivian 还把身为视觉艺术家的孪生兄弟 Cosmo Macdonald(Vivian 的全名是 Taddeo “Toto” Vivian Macdonald)介绍给了他们。在当地的小酒馆见面后,大家一拍即合。在音乐录影带里没能实现的有五十年代电视节目气氛的复古元素,转而由唱片封面传达了出来。
“我们想要象征性强,色彩艳丽的那种花哨氛围,最好再带点哀愁感。这张唱片封面该有的都有了。”秋山说, 不管是乐队周边还是唱片封面,他们都很看重作品的平面设计。“这代表我们的形象,是我们 DNA 的一部分。”
有吉他,贝斯和鼓,谁在乎什么永生?
浪漫和青春是 DYGL 的歌词里常提及的两大主题。我让秋山给我描绘一下他心中理想的浪漫场景,他却给了我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对我来说,浪漫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他总偏爱经典和不朽的事物。这也是乐队为什么不太愿意使用合成器这样的现代科技。“就最简单的吉他,贝斯和鼓。这大概就是我的浪漫。”
他接着说,“我们内心也知道最后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相信这世界上有不朽的东西存在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只要人类文化还有一天在,音乐就会长存。”
除了音乐以外,秋山还创作诗歌。与他的歌词不同,他写的诗更为具象化,也大多来自于他更为私人的体验。“诗歌需要坚实一些,因为他们只是言语。但做音乐这件事上,曲子对我来说比歌词要优先考虑。我平时听音乐时,脑海中会形成一些意象,而这些意象经常是抽象的。这促使我寻求一个平衡 —— 既能传达我的心路历程,又给听众的幻想留有通路的平衡。”无论是音乐还是诗歌,即使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写作而成的,都是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的艺术品。是它们向秋山揭示了浪漫的终极奥义。
至于青春,秋山说不管我们年龄多大,都该保有像一个孩子般感知世界的能力。对他来说,青春意味着纯粹和不忘初心。
但大家对人都会变老的现实作何感想呢?我知道我时常为终有一天脖颈上会长满皱纹这个事实而恐慌,而每次把酒混着喝时,身体的耐受力也明显不如以前强。“你害怕变老吗?”我问他们,“如果永生这种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你想要吗?”
结果我发现我错误地把问题建立在了假定乐队里的人都是无神论者的基础上。“害怕变老这件事再寻常不过了。有点麻烦的是,即使我现在信仰还没那么明确,对于永生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还是跟大部分不相信有神的人不太一样。就算我现在的生活方式跟传统基督徒有所区别,毕竟我还是从小生长在基督教背景下的,所以不好说。”秋山解释说。
DYGL 的其他成员对于永生这件事也有着大相径庭的见解。下中最开始觉得这主意挺不错的,但紧接着就迷失在了他自己跳跃的思维回路里面, “听起来真心好,也不用工作赚钱了,也不用为生计苦恼了,但是生活的整个意义就变了,不是吗?我跟你说,关于这种事我一般不去想这么多。”
另一边的嘉本则维持了他的虚无主义精神,“目前的我不是很在乎“生命”这种东西,大概三十年后也不会在乎自己还会活多久。反正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吧。”

鼓手嘉本康平
这个时候,Beach Fossils的 “This Year” 在酒吧里响了起来。我跟秋山关于这首歌是专辑“Somersault”里的第一首还是第二首还争论了一会。但说真的,这几位去年可是刚在 Beach Fossils 的日本巡演上跟人家联合出演,所以我还争个什么劲儿呢?
我们都是 “卡在中间的人”
DYGL 成员的生活看起来仿佛没什么太大瑕疵。他们住在孕育了他们灵感的理想城市中,把自己的音乐交给少时的吉他偶像来制作,又能与这个时代最有名望的几支独立乐队同台演奏……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多贴近他们的 “paper dream” 呢?这些年轻人还有哪些挣扎,下一步的目标又会是什么呢?
下中是这样说的,“我现在二十七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搞音乐的人多多少少都在想着退团,因为普遍都是二十岁出头开始搞乐队的大家现在都觉得是到了该回归‘普通人’生活的节点上。我们有我们的挣扎,但是我从未想过要放弃音乐,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谈目标的话,最终还是希望能有一天对自己的音乐产生满足感吧。虽然说老实话,我大概到死都不会满足的。在死之前,我会一直前进。”

鼓手嘉本康平
秋山的目标则是让所有人都对他的音乐产生连带感。把自己定义为“有点怪的一个人”的他仍不愿往自己身上贴标签,不管是“indie”啊,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并不是啊。”他觉得他始终是处于一种中间过渡的位置,就像他在基督教徒间长大,却搞起了摇滚乐,又抑或是他出身于日本南缘的小岛,却因缘巧合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几座城市间往返生活着。
他把这个话题进一步扩展到了与队友间的共鸣,“世俗眼光里,我们都不是男子汉气概那么强的人,但也不是走阴性路线的类型。我们对于艺术和时尚的触感可以说有女性化的成分在,但并不是过度阴柔的。事情的关键是,我不想把任何这些东西降格成陈词滥调,尤其是放到这支乐队身上。我希望DYGL的音乐可以是所有人都能尽情欢享的,you know what I mean?”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 DYGL 的音乐,可以用这片 playlist 进入他们的车库:
这是日本独立乐队 DYGL(读作“dayglo”)第三次参加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的西南偏南音乐节(SXSW)了。
2013年成立于东京的 DYGL 由主唱兼吉他手秋山信树,吉他手下中洋介,贝斯手加地洋太郎和鼓手嘉本康平所组成,现旅居伦敦。除了吉他手下中以外,其他成员都曾在另一个也由秋山发起的乐队 Ykiki Beat 中担任角色,只不过获得了短暂的商业成功的 Ykiki Beat 还是在2016年宣布了活动休止。
与广泛运用合成器的 Ykiki Beat 不同,DYGL 玩的是相当扎实的吉他摇滚,带着股2000年初车库和后朋克复兴的狠劲儿。他们凭一己之力把复古浪潮推回时尚尖端,很快成为了独立音乐新世代中最具代表性的面孔之一。
海外生活
与他们前两年参加 SXSW 时相对清闲的日程不同,今年的 DYGL 被满满当当地订了八场演出。乐队成员跟我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像那么回事”的 SXSW,还坚持辩解说他们眼睛下的黑眼圈跟短时间内密集的演出没关系,只不过是因为宿醉而已。
对于市郊废弃仓库粘稠地板上的即兴演奏,或是 Red River 大街上纵情的酒精狂欢,DYGL 都早已轻车熟路了。这几个小伙子不管是跟 The Chills 这样的大牌乐队共演一场人头攒动的午夜派对,还是在只有几个熟人在舞池里晃悠的德州 BBQ 馆子的 happy hour 前来个暖场,他们都维持着松弛自在的状态。他们每场的演出曲目都会根据场合悉心调整,气氛也总是欢愉而热烈的。
不过,这看似无尽的嘉年华对乐队成员本身来说,也未必总意味着欢乐。那天,与 DYGL 很久没见过面的我在他们刚演出完的场地外碰到了吉他手下中。他当时手里攥着电话,一脸的烦躁。我试着打了个招呼,他先是一惊,却又严肃地“嘘——”了我一下,转身一头扎回他那看似紧绷的对话中去了。晚上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满怀歉意地跟我解释说他当时是在跟日本的女朋友讨论一些要紧事。当然,完全,可以,理解。

吉他手下中洋介
“长期保持这样的国外生活和巡演状态,你会有孤独感吗?”我问。我知道这个夏天就要发行新专辑的他们为了录音,住在伦敦东北部有好一阵子了。
下中马上摇头否定了,“我倒不怎么孤独,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我也并不想念日本,但确实很想念我在日本的亲友们。家人,女朋友和好友们都在千里之外,有时候是挺叫人难过的,不过只要想到这些都是为了音乐,那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我很好奇能否把呆在伦敦这件事看作他们现在做音乐的一个必要元素,毕竟 DYGL 的音乐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这片土壤孕育的。下中再次否认了我的猜测,不过也承认伦敦确实是录音的好地方。他还跟我说,新专辑完成之后,乐队可能会重新研讨要不要继续住在伦敦。现在没什么是板上钉钉的。
一些翻唱,和大都会棒球队
在 DYGL 那晚的演出前,我给乐队成员塞了几包“中南海”牌香烟。他们激动得不行。通常以中国政界高层的居住地为人所知,饱含政治隐喻意味的“中南海”,同时也是由中国地下音乐的标志性乐队 Carsick Cars 创作的一首名曲的名字。DYGL 在第一次来中国巡演时不但翻唱了这首歌,还顺便迷上了“中南海”牌香烟的滋味。
DYGL 很喜欢在海外巡演时翻唱本地出身乐队的经典作品。2015年他们在纽约最早的几场演出里,有一场在一个叫 “柏林”的本地小酒馆,一首 Ramones 的 “I Wanna Be Your Boyfriend”让他们很快与观众拉近了距离 。这次在 SXSW 也不例外。在烤肉馆子 Cooper's 阁楼上的一群烤牛腩爱好者面前,他们翻唱了 The Kinks 的 “So Tired of Waiting for You” ,也赢得了台下不少会心的眼神。
在 Cooper's 的演出结束后,我们去了旁边一家酒馆,打算喝上几杯奥斯汀最好的生啤。当被问到为什么这次翻唱 The Kinks,以及谁来决定翻唱曲目时,秋山说基本上是由大家一起决定的。

主唱、吉他手秋山信树
在 DYGL 开始新专辑的录音前,乐队曾经开了个会来讨论接下来做什么感觉的声音比较好。秋山觉得,他们的处女专《Say Goodbye to Memories Den》只能看作是一个歌曲合集,没什么整体性。但这一次,既然大家最近发掘了不少新的音乐流派,他认为在新专辑的制作风格上有必要让全体成员的意见保持一致。
几轮讨论下来,乐队倾向于了60年代以后,相对老派的车库风格 —— “说实话60年代本身就够信息量巨大了。”他们觉得 The Kinks 的音乐超酷的,巡演路上也老是拿来听。“现场演奏他们的歌挺能激发我们的灵感的。”
我说:“你们之前翻唱的那首 Buzzcocks 也挺不错的。”那首翻唱收录在一张由 Rhyming Slang 发行的欧美朋克名曲的翻唱合辑中。Rhyming Slang 是一家专注于独立音乐社群的活动组织。它的创始人铃木知美,是东京地下音乐圈中很有地位和影响的一位女士,据说很受本地青年乐队的尊敬。
DYGL 的成员们对于我竟然知道那张翻唱专辑的存在感到震惊。似乎当时的发行范围并不大,也没做什么宣传。

“不是有互联网吗!”我不禁笑了出来。
下中听了后做了个鬼脸,他一直都对当今的赛博生活和社交网络心存芥蒂。在我们去年的采访和聊天中,他都对这一点毫不掩饰。他觉得互联网把人类的隐私强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这件事很糟糕,毕竟又不是谁都喜欢天天直播自己的生活的。
“不过我也不是一点都不喜欢上网。我天天泡在 YouTube 上看视频。”
我问他一般都看什么样的视频,他先说不能告诉我,在我的坚持下,才勉强承认他看很多日本网红的搞笑视频,有时候也看一点音乐或者职业棒球相关的东西。他说他支持纽约大都会队(the New York Mets),还说,“洋基队(注:the New York Yankees,大都会队的死对头)倒也不是不行,就是有那么点……”
我举起一只手叫他别接着说了,因为我是洋基队的粉丝。
做音乐,也交一些新朋友
乐队的早期,还是在叫 DYGL 这个名字以前的时候,秋山,下中和嘉本组过一个叫 De Nada 的“副本乐队”。在这个乐队里,成员经常交换着乐器来创作,大部分时间都是秋山打鼓,嘉本弹吉他。这段时光里,一首美丽而柔和,又注入了乡愁感的曲子“Nashville” 诞生了。从那以后差不多过了七年,DYGL 再次把这首歌搬到了 SXSW 的舞台上,却是以当前乐队的分工来演奏的。
我对秋山表示了想在 SXSW 看到他打鼓的愿望。他说他也想,但是器材设备都有限制,而且对这首歌,目前乐队还停留在探索编曲的阶段,研究着怎么改才能让这首歌在新专辑里合群,这次也是想从现场中得到一些启迪。
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乐队试着跟当时的两位制作人,也就是 The Strokes 的吉他手 Albert Hammond Jr. 和制作了 The Strokes 后两张专辑的 Gus Oberg 说过,能不能把这首歌加进去,但后来发现确实不是很合适。这回又发新专辑,秋山想再试一试。
贴心的加地告诉我其实他们做了另外一首曲子,里面是秋山打鼓,嘉本弹贝斯。但是他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首歌会不会在新专辑的最终阵容里。

贝斯手加地洋太郎
上个月,DYGL 发行了睽违已久的新单曲“A Paper Dream”。这张单曲距离上一张“Bad Kicks”的发行已有一年了。两张单曲都也是正在制作他们新专辑的制作人 Rory Attwell 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A Paper Dream”的录音是在 Stereolab 的鼓手 Andrew Ramsay 开的录音室 Press Play Studio 完成的。加地对于这个录音室里的设备和器材津津乐道,“他们那儿的鼓,哇,都是最顶级的。”
在新单曲的MV里,加地弹奏着一把古典低音提琴,很符合他的气质。可当我向他提起来这码事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下中突然爆笑起来。加地看起来更害羞了,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就是在那假装弹呢。那把琴就放在那,大家都觉得拿来拍摄应该效果挺好的。那是我第一次碰这种乐器,根本不知道怎么弹。”大家没看出来,说明装得还挺像样的。

贝斯手加地洋太郎
曾来过中国巡演,现在活动已休止的乐队 Splashh 的吉他手 Toto Vivian 执导了这首歌的MV。从以前就很欣赏 Splashh 的秋山在看了由 Vivian 亲自执镜的 Splashh 美国巡演的纪录片之后,对片子的拍摄手法着了迷,“光怪陆离,扣人心弦,带着种酷酷的波普感。重要的是又很切题。”他当即联系了 Vivian。
Vivian 先是帮 DYGL 拍摄了“Bad Kicks”的影片,这回又包揽了“A Paper Dream”。这一次的拍摄,原本最受乐队成员欢迎的提案是做成一个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来配合怀旧气息满溢,带有歌谣感的旋律,可是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而从头改造一个新场地所需的费用又超过了他们的预算,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期间,得知 DYGL 在找人设计单曲封面后的 Vivian 还把身为视觉艺术家的孪生兄弟 Cosmo Macdonald(Vivian 的全名是 Taddeo “Toto” Vivian Macdonald)介绍给了他们。在当地的小酒馆见面后,大家一拍即合。在音乐录影带里没能实现的有五十年代电视节目气氛的复古元素,转而由唱片封面传达了出来。
“我们想要象征性强,色彩艳丽的那种花哨氛围,最好再带点哀愁感。这张唱片封面该有的都有了。”秋山说, 不管是乐队周边还是唱片封面,他们都很看重作品的平面设计。“这代表我们的形象,是我们 DNA 的一部分。”
有吉他,贝斯和鼓,谁在乎什么永生?
浪漫和青春是 DYGL 的歌词里常提及的两大主题。我让秋山给我描绘一下他心中理想的浪漫场景,他却给了我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对我来说,浪漫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他总偏爱经典和不朽的事物。这也是乐队为什么不太愿意使用合成器这样的现代科技。“就最简单的吉他,贝斯和鼓。这大概就是我的浪漫。”
他接着说,“我们内心也知道最后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相信这世界上有不朽的东西存在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只要人类文化还有一天在,音乐就会长存。”
除了音乐以外,秋山还创作诗歌。与他的歌词不同,他写的诗更为具象化,也大多来自于他更为私人的体验。“诗歌需要坚实一些,因为他们只是言语。但做音乐这件事上,曲子对我来说比歌词要优先考虑。我平时听音乐时,脑海中会形成一些意象,而这些意象经常是抽象的。这促使我寻求一个平衡 —— 既能传达我的心路历程,又给听众的幻想留有通路的平衡。”无论是音乐还是诗歌,即使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写作而成的,都是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的艺术品。是它们向秋山揭示了浪漫的终极奥义。
至于青春,秋山说不管我们年龄多大,都该保有像一个孩子般感知世界的能力。对他来说,青春意味着纯粹和不忘初心。
但大家对人都会变老的现实作何感想呢?我知道我时常为终有一天脖颈上会长满皱纹这个事实而恐慌,而每次把酒混着喝时,身体的耐受力也明显不如以前强。“你害怕变老吗?”我问他们,“如果永生这种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你想要吗?”
结果我发现我错误地把问题建立在了假定乐队里的人都是无神论者的基础上。“害怕变老这件事再寻常不过了。有点麻烦的是,即使我现在信仰还没那么明确,对于永生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还是跟大部分不相信有神的人不太一样。就算我现在的生活方式跟传统基督徒有所区别,毕竟我还是从小生长在基督教背景下的,所以不好说。”秋山解释说。
DYGL 的其他成员对于永生这件事也有着大相径庭的见解。下中最开始觉得这主意挺不错的,但紧接着就迷失在了他自己跳跃的思维回路里面, “听起来真心好,也不用工作赚钱了,也不用为生计苦恼了,但是生活的整个意义就变了,不是吗?我跟你说,关于这种事我一般不去想这么多。”
另一边的嘉本则维持了他的虚无主义精神,“目前的我不是很在乎“生命”这种东西,大概三十年后也不会在乎自己还会活多久。反正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吧。”

鼓手嘉本康平
这个时候,Beach Fossils的 “This Year” 在酒吧里响了起来。我跟秋山关于这首歌是专辑“Somersault”里的第一首还是第二首还争论了一会。但说真的,这几位去年可是刚在 Beach Fossils 的日本巡演上跟人家联合出演,所以我还争个什么劲儿呢?
我们都是 “卡在中间的人”
DYGL 成员的生活看起来仿佛没什么太大瑕疵。他们住在孕育了他们灵感的理想城市中,把自己的音乐交给少时的吉他偶像来制作,又能与这个时代最有名望的几支独立乐队同台演奏……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多贴近他们的 “paper dream” 呢?这些年轻人还有哪些挣扎,下一步的目标又会是什么呢?
下中是这样说的,“我现在二十七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搞音乐的人多多少少都在想着退团,因为普遍都是二十岁出头开始搞乐队的大家现在都觉得是到了该回归‘普通人’生活的节点上。我们有我们的挣扎,但是我从未想过要放弃音乐,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谈目标的话,最终还是希望能有一天对自己的音乐产生满足感吧。虽然说老实话,我大概到死都不会满足的。在死之前,我会一直前进。”

鼓手嘉本康平
秋山的目标则是让所有人都对他的音乐产生连带感。把自己定义为“有点怪的一个人”的他仍不愿往自己身上贴标签,不管是“indie”啊,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并不是啊。”他觉得他始终是处于一种中间过渡的位置,就像他在基督教徒间长大,却搞起了摇滚乐,又抑或是他出身于日本南缘的小岛,却因缘巧合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几座城市间往返生活着。
他把这个话题进一步扩展到了与队友间的共鸣,“世俗眼光里,我们都不是男子汉气概那么强的人,但也不是走阴性路线的类型。我们对于艺术和时尚的触感可以说有女性化的成分在,但并不是过度阴柔的。事情的关键是,我不想把任何这些东西降格成陈词滥调,尤其是放到这支乐队身上。我希望DYGL的音乐可以是所有人都能尽情欢享的,you know what I mean?”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 DYGL 的音乐,可以用这片 playlist 进入他们的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