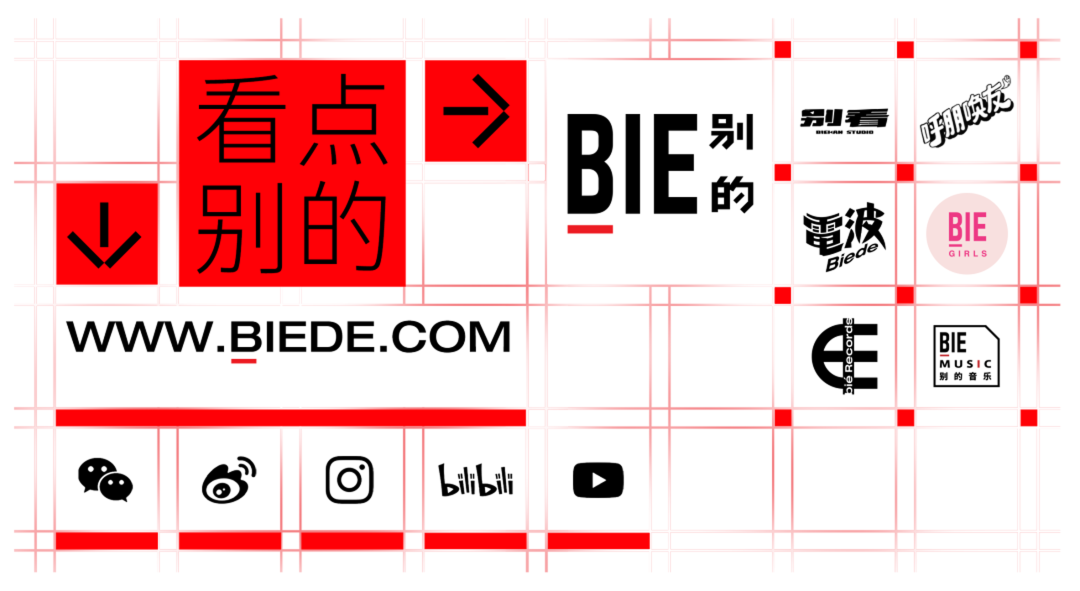我在上海封控管理时遇到邻居家暴
别的女孩: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个正在进行的赛博事实 —— 观点正在被大量稀释,最稀缺的是你的冒险。忘掉那些二手的阐释,直接用你的眼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青年人,动起来,走进这个社会。
这里是专栏#当时我在#, 邀请你围观女孩们的亲历、观察与冒险。如果这击中了你的分享欲,欢迎投稿至 biedegirls@yishiyise.com。可以独特,可以幽默,必须真实,最好还有点危险。

提 图
▼
在上海封城的第十天左右,我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忽然,天花板传来一声巨响。
我打开窗户,探出头去,想听得更仔细些。楼上传来了男人的辱骂声,打耳光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哭声。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 这显然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我倒吸一口凉气:即使在非疫情期间,受害者得到帮助已经很难了,而在封城的时候遭遇到,可以说是一场噩梦。
帮助家暴受害者,首要任务就是将她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却因为封城下 “足不出户” 的政策而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受害者不得不和施暴者困在同一屋檐下。
我还是得做点什么。我打了 110 报警,告诉接线员我听到楼上邻居在家暴,想让他们派人来处理。
“你想让我们怎么处理?” 接线员警察回答。“因为疫情管理,我们进不来你的小区。”
“那怎么办?” 我问。他说他会给我的居委会打电话,请他们去看一下情况,然后挂了电话。
我不放心,也给我认识的一位居委发了微信,请她去看看楼上的邻居,但在当晚没收到回复。“警察这是逃避责任”,第二天她回复我。“警察要进去有啥进不去的。” 最后,无论是警察和居委都没有上门查看。
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说,“哦,那应该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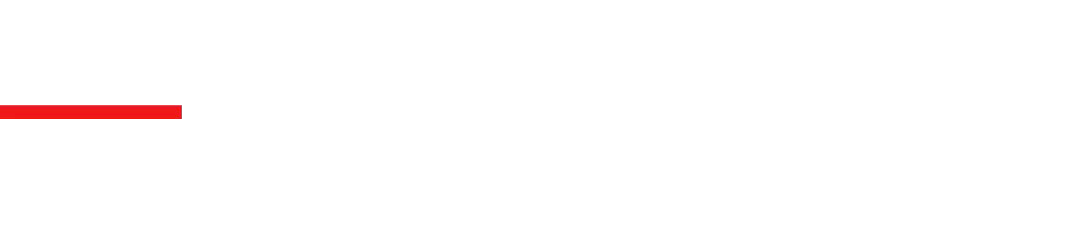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虽然失望,但其实也不惊讶。求助警察和居委失败后,我决定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她。但这做起来远比想象中难。几个月前我才刚搬进这栋楼。像大多数上海居民在封控前一样,我几乎不认识我的邻居。这件事情发生后,那几天我每天去做核酸或领物资的时候都四处张望,在 “中年女性”,“和我住同一栋楼” 等几个关键词中寻觅邻居。
直到有一天,我在领完物资回家的路上,锁定了和我走入同一栋楼的一位女性。
她看起来 30 多岁,消瘦,长发。我先是试探着问她最近是否听到一些 “打人的声音”。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在我表达对这位女性的担心之后,她迟疑了一下,似乎很惊讶, “哦,那应该是我”。
她用一种很轻松的语气和我说,没事的,不要担心,这只是 “夫妻吵架”。我向她指了我的房间,如果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她可以到我的房间里来。
这是我在上海做反家暴志愿者的第三年。与家暴受害者建立连结,是我们作为志愿者很重要的工作。遭受暴力的女性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而以一种关心、敢于干预的态度和她们连结,相当于告诉她们,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拘留?”她没想到,受害者也会被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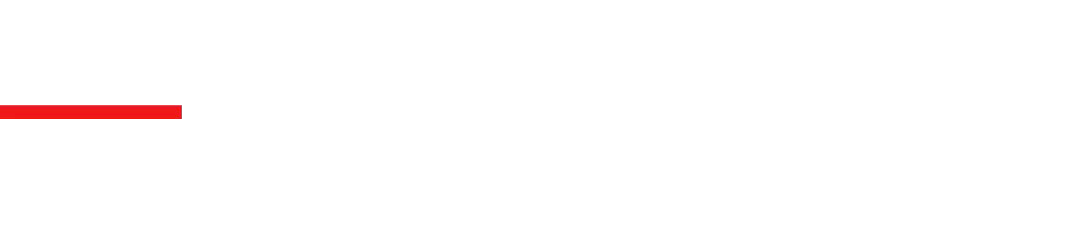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5 月 19 日晚,在距离第一次家暴的五周后,我又听到了天花板传来熟悉的巨大声响。先是家具被砸在地板上,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救命!救命啊! 渣男在打人!” 我冲上楼去,发现那个消瘦的她坐在地板上,无法站立。
我回到自己的楼层,再次报了警。这一次我和警察强调说,事情很严重,那位女邻居看起来受了严重的伤,需要治疗。并且强调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家暴了。这是反家暴志愿者的另一个策略。通过强调情况的严重性,更容易说服警察,使他们相信这个案件不仅仅是 “夫妻吵架”。
在反复确认我们楼里没有阳性病例后,大约 15 分钟,两名从头到脚都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出现在我邻居家门口,我在楼下竖着耳朵听。
“发生什么事了”,一名警官问。
女人说她被打了;男人则反驳说她也抓伤了他。警官问女人,是否需要他们来 “解决 ”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女人问。
“哦,你们互殴,解决的话就是把你们两个都拘留。” 警察轻描淡写地说。
拘留,这两个字显然让我的女邻居感到害怕。她大概没有想到,作为受害者也会受到惩罚。
“那不用处理了。” 她悻悻地说。随后小心翼翼地问警察,能不能把她带出去住,或者协助她买一个新手机 —— 她的手机在被丈夫家暴的时候被摔烂了。而在封城期间,买一个新手机特别困难。
当然,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
之后,他们检查了这对夫妻的身份证和健康码,就走了,全程花了不到10分钟。
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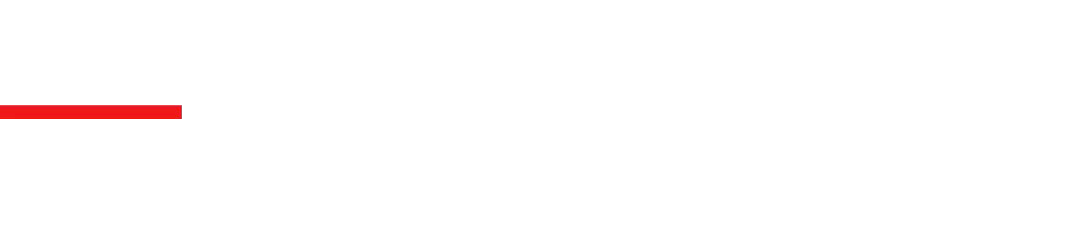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发生在我邻居身上的事远不是孤立的案例。
联合国妇女署将疫情间的家暴称为 “在暗处的流行病”(The Shadow Pandemic)。在新冠爆发的这几年,全球许多地方政府都报告了家暴案例激增。我国的《反家暴法》自2016年起生效,但在疫情爆发的这几年,严格的隔离、封锁防疫政策使得家暴受害者的求助难上加难。

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将预防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纳入其防疫计划中,同时,有150个国家已经出台了加强对疫情期间的家暴受害者的服务。数据来自https://www.unwomen.org/en/what-we-do/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facts-and-figures。图源:unwomen.org
在上海封城的两个月里,我和其他几位上海的反家暴志愿者收到了超过10个来自家暴受害者的求助 —— 这个数字,大约是我们平时工作量的三倍。
其中一位求助者是一位 50 多岁的阿姨。她被前夫殴打,玻璃杯摔过来,手指不停流血。在封城之前,她和她的女儿本已准备搬走。但突如其来的封城让家暴不断升级。
她向警察求助,但警察的说法和当时我替邻居报警一样,也说因为防疫政策无法进入小区。她向居委会求助,希望居委能给她开出入证,让她搬到她在上海的姐姐或妈妈那里去住,但也被拒绝了。最后,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那几天上海天气很冷,还下着雨,她和女儿就这样在外面躲了几个小时,直到居委会答应她们可以在物业办公室里暂住一晚。
“她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被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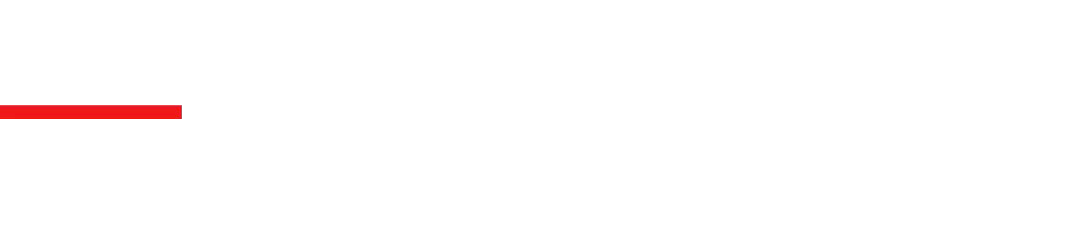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接到阿姨的求助后,我多次拨打了阿姨住所的区妇联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后来我才听说,封城期间,许多妇联工作人员都被隔离在家中。
接着,我试着拨打了 12338 全国妇女维权热线,接线员(她称自己是志愿者,“我们也不是妇联的,我们只是接电话”)听到阿姨的遭遇感到很惊讶,“怎么这么多女的被家暴了?” 说这已经是她今天下午接听的第四个家暴求助的电话。
“被家暴也不能让你出小区”,她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的要去惹男人,都知道封城期间……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为什么会挨打?”
类似的话,这位接线员还说了很多:
......
我也联系了家暴庇护所。是的,这也是《反家暴法》提到的政策之一,这些庇护所一般和救助站建立在一起,为受暴者提供一个暂时的安全容身之所。
但结局同样令人失望:我被告知,封城期间家暴庇护所已被用作救助站,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外地滞留人口。
帮助受害者维权的那几天,被困在家中的我不断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我仿佛被困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每次尝试着找出口,却不断撞向一堵又一堵墙。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志愿者伙伴用私人关系联系到了上海妇联的一位老师。几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在她们的介入下,警察同意将阿姨和她的女儿带到附近一家酒店居住。
第二天,我们收到了阿姨的微信:“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
“她们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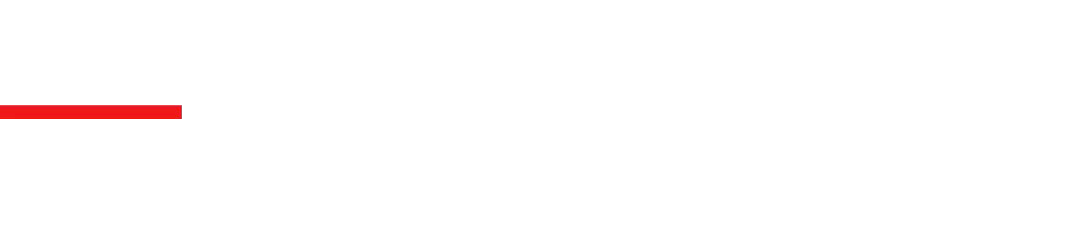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受害者不报警?她们为什么不逃跑?
维权,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往往是痛苦的过程。它大多数时候意味着,向一个把家暴当作 “家务事” 的系统寻求保护和正义。如果说这封城的两个月的反家暴志愿者工作有什么感想,那就是:维权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时候比忍受暴力的成本更高。
在封锁期间,我们也接到一些 “没有下文” 的求助,受害者一开始也积极维权,和我们讲述自己被暴力的遭遇,但在一次次求助失败后,和我们表示 “算了”,就像那位妇联接线员说的,忍气吞声,不去惹恼对方。
久而久之,我们逐渐观察到一种怪象:对于疫情期间的受暴妇女来说,维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与施暴者呆在一起似乎是更 “合理”的选择。
那位 50 多岁的阿姨是幸运的,她最终和女儿安全地住在酒店直到解封。而我楼上的邻居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两个月来,我能做的只是不断督促相关部门的工作,并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我的天花板不会再发出声音。

2020 年 4 月 16 日,黎巴嫩全国疫情封锁期间,一名妇女在阳台上悬挂横幅,写有 “停止家暴妇女” 并附上援助热线。// 摄影:Bilal Huss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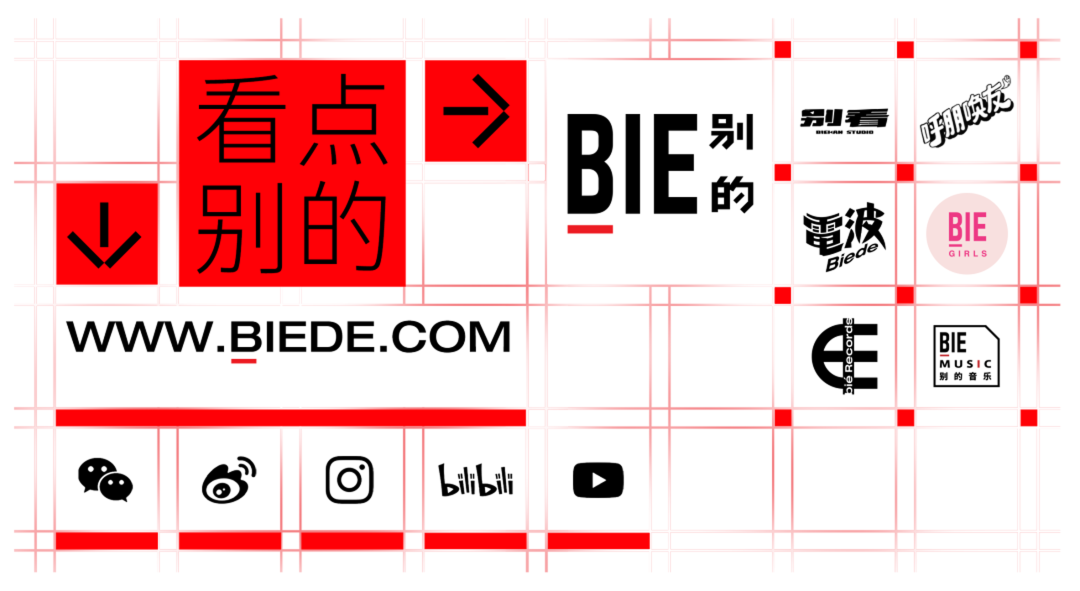
别的女孩: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个正在进行的赛博事实 —— 观点正在被大量稀释,最稀缺的是你的冒险。忘掉那些二手的阐释,直接用你的眼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青年人,动起来,走进这个社会。
这里是专栏#当时我在#, 邀请你围观女孩们的亲历、观察与冒险。如果这击中了你的分享欲,欢迎投稿至 biedegirls@yishiyise.com。可以独特,可以幽默,必须真实,最好还有点危险。

提 图
▼
在上海封城的第十天左右,我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忽然,天花板传来一声巨响。
我打开窗户,探出头去,想听得更仔细些。楼上传来了男人的辱骂声,打耳光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哭声。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 这显然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我倒吸一口凉气:即使在非疫情期间,受害者得到帮助已经很难了,而在封城的时候遭遇到,可以说是一场噩梦。
帮助家暴受害者,首要任务就是将她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却因为封城下 “足不出户” 的政策而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受害者不得不和施暴者困在同一屋檐下。
我还是得做点什么。我打了 110 报警,告诉接线员我听到楼上邻居在家暴,想让他们派人来处理。
“你想让我们怎么处理?” 接线员警察回答。“因为疫情管理,我们进不来你的小区。”
“那怎么办?” 我问。他说他会给我的居委会打电话,请他们去看一下情况,然后挂了电话。
我不放心,也给我认识的一位居委发了微信,请她去看看楼上的邻居,但在当晚没收到回复。“警察这是逃避责任”,第二天她回复我。“警察要进去有啥进不去的。” 最后,无论是警察和居委都没有上门查看。
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说,“哦,那应该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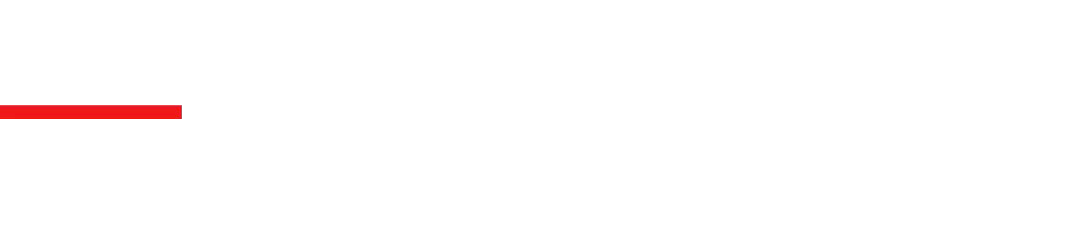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虽然失望,但其实也不惊讶。求助警察和居委失败后,我决定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她。但这做起来远比想象中难。几个月前我才刚搬进这栋楼。像大多数上海居民在封控前一样,我几乎不认识我的邻居。这件事情发生后,那几天我每天去做核酸或领物资的时候都四处张望,在 “中年女性”,“和我住同一栋楼” 等几个关键词中寻觅邻居。
直到有一天,我在领完物资回家的路上,锁定了和我走入同一栋楼的一位女性。
她看起来 30 多岁,消瘦,长发。我先是试探着问她最近是否听到一些 “打人的声音”。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在我表达对这位女性的担心之后,她迟疑了一下,似乎很惊讶, “哦,那应该是我”。
她用一种很轻松的语气和我说,没事的,不要担心,这只是 “夫妻吵架”。我向她指了我的房间,如果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她可以到我的房间里来。
这是我在上海做反家暴志愿者的第三年。与家暴受害者建立连结,是我们作为志愿者很重要的工作。遭受暴力的女性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而以一种关心、敢于干预的态度和她们连结,相当于告诉她们,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拘留?”她没想到,受害者也会被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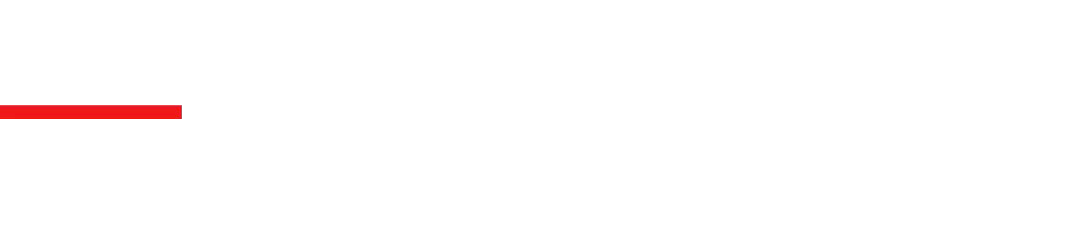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5 月 19 日晚,在距离第一次家暴的五周后,我又听到了天花板传来熟悉的巨大声响。先是家具被砸在地板上,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救命!救命啊! 渣男在打人!” 我冲上楼去,发现那个消瘦的她坐在地板上,无法站立。
我回到自己的楼层,再次报了警。这一次我和警察强调说,事情很严重,那位女邻居看起来受了严重的伤,需要治疗。并且强调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家暴了。这是反家暴志愿者的另一个策略。通过强调情况的严重性,更容易说服警察,使他们相信这个案件不仅仅是 “夫妻吵架”。
在反复确认我们楼里没有阳性病例后,大约 15 分钟,两名从头到脚都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出现在我邻居家门口,我在楼下竖着耳朵听。
“发生什么事了”,一名警官问。
女人说她被打了;男人则反驳说她也抓伤了他。警官问女人,是否需要他们来 “解决 ”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女人问。
“哦,你们互殴,解决的话就是把你们两个都拘留。” 警察轻描淡写地说。
拘留,这两个字显然让我的女邻居感到害怕。她大概没有想到,作为受害者也会受到惩罚。
“那不用处理了。” 她悻悻地说。随后小心翼翼地问警察,能不能把她带出去住,或者协助她买一个新手机 —— 她的手机在被丈夫家暴的时候被摔烂了。而在封城期间,买一个新手机特别困难。
当然,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
之后,他们检查了这对夫妻的身份证和健康码,就走了,全程花了不到10分钟。
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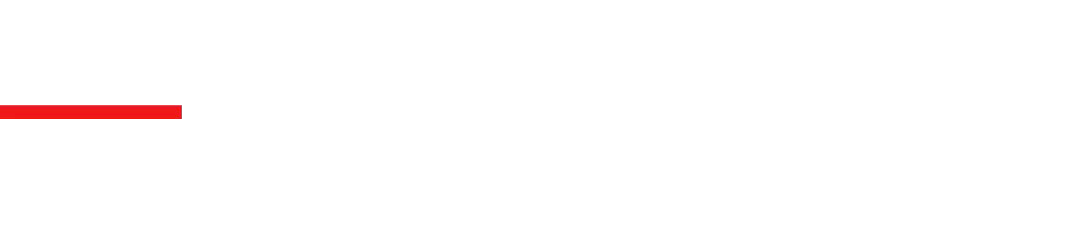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发生在我邻居身上的事远不是孤立的案例。
联合国妇女署将疫情间的家暴称为 “在暗处的流行病”(The Shadow Pandemic)。在新冠爆发的这几年,全球许多地方政府都报告了家暴案例激增。我国的《反家暴法》自2016年起生效,但在疫情爆发的这几年,严格的隔离、封锁防疫政策使得家暴受害者的求助难上加难。

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将预防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纳入其防疫计划中,同时,有150个国家已经出台了加强对疫情期间的家暴受害者的服务。数据来自https://www.unwomen.org/en/what-we-do/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facts-and-figures。图源:unwomen.org
在上海封城的两个月里,我和其他几位上海的反家暴志愿者收到了超过10个来自家暴受害者的求助 —— 这个数字,大约是我们平时工作量的三倍。
其中一位求助者是一位 50 多岁的阿姨。她被前夫殴打,玻璃杯摔过来,手指不停流血。在封城之前,她和她的女儿本已准备搬走。但突如其来的封城让家暴不断升级。
她向警察求助,但警察的说法和当时我替邻居报警一样,也说因为防疫政策无法进入小区。她向居委会求助,希望居委能给她开出入证,让她搬到她在上海的姐姐或妈妈那里去住,但也被拒绝了。最后,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那几天上海天气很冷,还下着雨,她和女儿就这样在外面躲了几个小时,直到居委会答应她们可以在物业办公室里暂住一晚。
“她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被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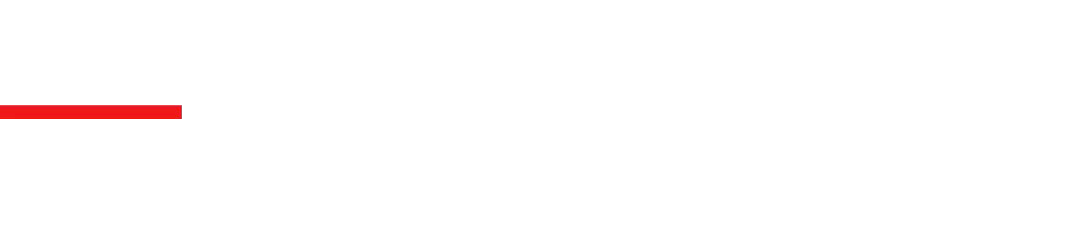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接到阿姨的求助后,我多次拨打了阿姨住所的区妇联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后来我才听说,封城期间,许多妇联工作人员都被隔离在家中。
接着,我试着拨打了 12338 全国妇女维权热线,接线员(她称自己是志愿者,“我们也不是妇联的,我们只是接电话”)听到阿姨的遭遇感到很惊讶,“怎么这么多女的被家暴了?” 说这已经是她今天下午接听的第四个家暴求助的电话。
“被家暴也不能让你出小区”,她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的要去惹男人,都知道封城期间……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为什么会挨打?”
类似的话,这位接线员还说了很多:
......
我也联系了家暴庇护所。是的,这也是《反家暴法》提到的政策之一,这些庇护所一般和救助站建立在一起,为受暴者提供一个暂时的安全容身之所。
但结局同样令人失望:我被告知,封城期间家暴庇护所已被用作救助站,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外地滞留人口。
帮助受害者维权的那几天,被困在家中的我不断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我仿佛被困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每次尝试着找出口,却不断撞向一堵又一堵墙。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志愿者伙伴用私人关系联系到了上海妇联的一位老师。几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在她们的介入下,警察同意将阿姨和她的女儿带到附近一家酒店居住。
第二天,我们收到了阿姨的微信:“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
“她们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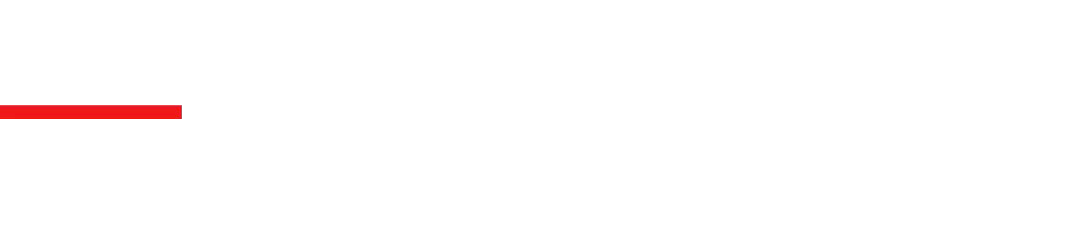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受害者不报警?她们为什么不逃跑?
维权,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往往是痛苦的过程。它大多数时候意味着,向一个把家暴当作 “家务事” 的系统寻求保护和正义。如果说这封城的两个月的反家暴志愿者工作有什么感想,那就是:维权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时候比忍受暴力的成本更高。
在封锁期间,我们也接到一些 “没有下文” 的求助,受害者一开始也积极维权,和我们讲述自己被暴力的遭遇,但在一次次求助失败后,和我们表示 “算了”,就像那位妇联接线员说的,忍气吞声,不去惹恼对方。
久而久之,我们逐渐观察到一种怪象:对于疫情期间的受暴妇女来说,维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与施暴者呆在一起似乎是更 “合理”的选择。
那位 50 多岁的阿姨是幸运的,她最终和女儿安全地住在酒店直到解封。而我楼上的邻居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两个月来,我能做的只是不断督促相关部门的工作,并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我的天花板不会再发出声音。

2020 年 4 月 16 日,黎巴嫩全国疫情封锁期间,一名妇女在阳台上悬挂横幅,写有 “停止家暴妇女” 并附上援助热线。// 摄影:Bilal Huss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