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后打零工的我,是“名校废柴”吗?
我打零工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三年前。
本科毕业以后,失去学生身份庇佑的我,终于没法心安理得地继续过着无所事事、毋需自食其力的日子。为了生存,我决定出去打工搞钱。这期间,我做过许多 “hit-and-run” 式的零工,包括但不仅限于画室模特,精神病房的临时会议协调员,群演,充场人员,超市促销,发模,演讲稿代写,小学生托管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在形形色色的打零工经验里,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无论何种性质的工作,总免不了因为性别的原因出现区别对待。除了某些岗位偏爱或直接限定男生,体力劳动男女差价工资,女性附加外貌形象条件等等之外,还有一些是性别刻板印象造成的隐性差别。
比如我在一家教育机构当中学助教,负责人会跟我说:“明天答疑的是高中理科,你们女生应该都不如男生擅长,所以明天安排了两个男大学生。” 而到了核对数据的时候,听到的则是:“这种不能出错的步骤就交给小姑娘完成吧,毕竟心细”。
这些话相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我还碰到过另一些 “老生常谈” —— 一次是和我妈提起去画室做了模特,她紧张兮兮地问:“没做裸模吧?女孩子坚决不能做”;还有一次是打算去应聘深夜的兼职便利店员,被提醒说深夜时间段遇到店内安全问题 “可能一个女生无法妥善处置”,遂作罢。
找零工的女性里,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并不多。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和四十往上的中年女性往往是主力军。其中一个原因是,除去某些以女性特征为筹码的工作(例如礼仪,模特等),许多临时兼职以体力负担为主,对女性而言并不轻松,而且此类工作多半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年轻女性多会担忧安全保障和权益维护的问题。
除了性别,打零工还令我思考起学历和教育这件事。名校文凭几乎是每个中国小孩梦寐以求并为之努力的,但在零工世界里,它毫无用处 —— 或者说,它的作用就是避开这些工作的 “垫脚石”。当被偶尔问起在哪所学校读书时,我不得不编造蹩脚的谎言 —— 我的大学虽然称不上殿堂级高校,但它的知名度也足以令我躲在背后小小虚荣一番;也正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提及自己的出身,“名校废柴” 的尴尬感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世人观念里,体力劳动与精神生活有云泥之别。但在我打零工的日子里,我意识到,象牙塔里获取的知识除了赋予某种非常虚幻的、形而上的支撑感之外,它能提供的作用实际是微不足道的。接触这些简单机械劳累的劳动之前,我一直执拗地认定,自己是脱离庸俗世界的 “精神性” 的人,因此只能投身于精神世界的生产活动:一切与美和艺术相关联的、凝结了人类情感共鸣的表达都令我着迷。我应该去做人类灵魂后花园的建筑者,或是艺术界的抽象思辨领袖!
在表达欲的冲动下,我去到一家零食公司做新媒体文案策划,最后只坚持了一个月。放弃的缘由,跟大多数以笔谋生的文学青年没什么区别:既对商业性迎合观众的表达深恶痛绝,又想自己的表达被大众认可,最后因质疑绝大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而止步不前。匆匆办完离职,我的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就结束了。
在这之前,我还接连搞砸过 “高薪优待” 的培训机构教师与专业对口的证券公司客户经理两个工作,离校后无处可去只得逃回家赋闲。在家里那段日子里,虽然有生存的焦虑,但更令我无法想象、极为恐慌的是:我究竟该如何投身成为社会链条上运转的一分子?一切招聘、面试、体制考试相关的消息,都令我头痛欲裂。我像一只搁浅在海滩上的软体动物,只要缩进暗无天日的硬壳然后往沙子深处一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失去与整个世界的关联。
现在想来,我逃避的是什么呢?大概是所谓的 “主流生活” —— 毕业、工作、组建家庭,环环相扣,从我们成年之后就被套上命运的枷锁,被牵引着度过一生。未来的轨迹早已被周遭的人推着设定完毕,要做的无非是在这条道上走一遍。每个被推进去的年轻人其实都心知肚明,社会共识加于我们身上的许多框架,需要我们削减个性以适应,并为了普世意义上的成功而承担许多不快乐的代价。
对于我周遭圈子的 “主流” 来说,放弃找正式工作,转而去做零工女孩,显然是离经叛道、不可理解之举。这意味着我并没有被某一社会身份收容,虽然同样付出的是劳动。跟旧识的人提及现状时,我不得不承受一些误解与不恰当的评价;当朋友善意地劝我回归 “正轨” 时,我也只能是报以感谢。即使自食其力努力打工显得狼狈不堪,但我恰恰在此间找到了与自己本性相符的姿态。
我设想过,如果是曾经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也会心存不解与质疑。唯有亲身经历过零工生活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动荡,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些因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而自愿放弃 “正常人” 的轨迹,在大众认可的生存方式之外游荡的人,是一种更多元的生命形态。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零工的世界里是宽容的。恰恰相反,在这里你能体会到多种多样的社会规训和歧视。例如穿了 JK 水手服去参加充场活动,听到来自活动主办方窃窃私语的议论;为了做发模(为新手美发师练手的角色)染了一头宝石蓝,结果因为发色 “不够正统”,被教育机构以 “影响不佳” 为由拒之门外。还有一次是负责精神障碍会议协调的短期工作,第一次和与我对接的负责人姐姐进入精神病院的病房,出来时她在背后悄悄问我:“你怎么这么淡定啊,我都紧张得不得了。”
那一瞬间我的心情其实相当复杂,不晓得怎么用简短的语言解释大众对精神病的刻板化、污名化,也不想大方承认我亦定期拜访这家医院的门诊部,期间早已观察过形形色色的病患群体。我便无意识冒出一句 “我不怕,又不是没见过”,反应过来后立刻接上一句 “以前陪别人探望过。”
打零工的日子里,我周旋在曾经试图躲避的外部世界,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格格不入。但有一次经历,令我这个从精神到身体的 “边缘人”,竟然意外获得与周围陌生人的联结感。当时我去剧组当群众演员,经过一番被审视和挑选,我入选了,成为十几名 “年轻、微胖、女孩” 中的一员。到达场地之前,剧组还特意叮嘱我们化好妆,衣服要 “穿得漂亮一点,最好有女孩子的感觉”。
那是为数不多的、能见到那么多与我同龄女孩的机会,而且她们还与我分享相似的身体外形!(出于剧情需要,招募条件是 “体型偏胖的女生优先”)。辗转三辆公交车赶到拍摄现场以后,我们这十几个群演女孩坐在帐篷旁天南地北地闲聊,聊身材超重的顾虑,妆容与衣服的搭配,正在经历的生活,还有虚无缥缈的未来。因为逃避社交的缘故,我快已经与同龄女生脱节了,甚至连 “是一个女孩” 这层意识都快模糊了。但是在那次的场景里,我感受到了水滴落入汪洋的归属感。
在等待剧组布景、安排戏份的空当,我蹲在沙滩上大口吞咽着工作盒饭,望着远处天色渐暗的海平线发呆。看到旁边的女孩子点了根烟,我把脑袋凑过去:“可以给我一根吗,谢谢。”

那天的沙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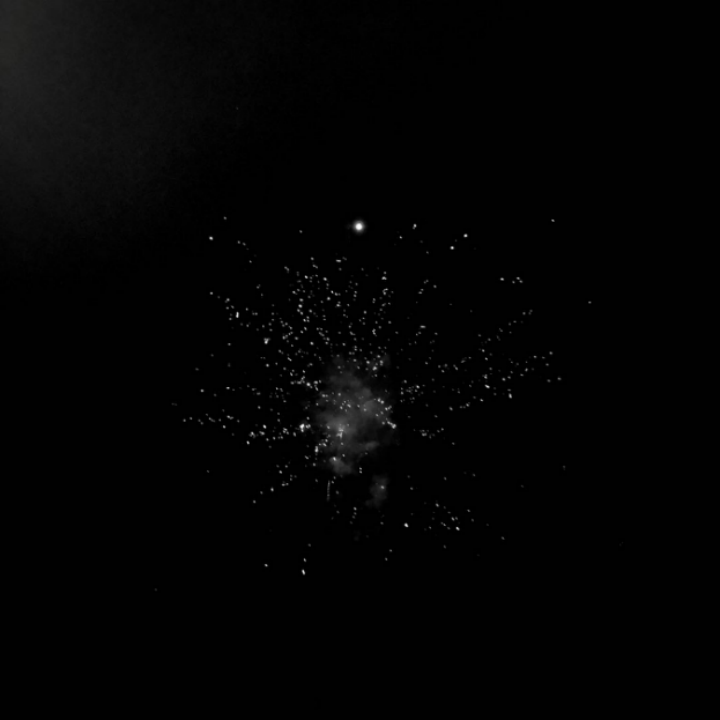
那天的烟火

那些与我短暂相处的女孩们
两年多的零工生活结束了,我回到学校继续念书,结束了那段充满随性的 “混乱” 经历。即使到现在,我也还会时不时陷入 “这次毕业后能否融入工作环境” 的自我怀疑中,我清楚地知道,学生身份只是延缓我与世界磨合进程的一道缓冲带,而不是我能躲避一生的安全区。加上疫情的冲击,更让我感受到零工维生状态的脆弱:它只是勉强维持住了我的生活,却无法抵御任何突发事件。
但无论如何,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用尚有活力的生命从主流里逃逸了一回,总归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