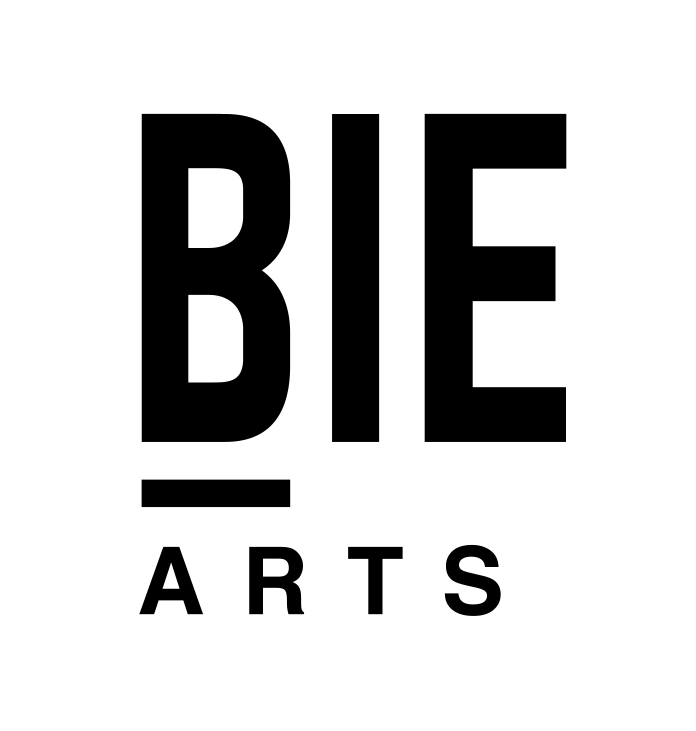帕特里夏的钩织人偶在你毫不设防的时候突然出击
艺术家帕特里夏·沃勒(Patricia Waller)所做的的羊毛钩织玩偶觉不是祖母哄你睡觉时拿出来的小娃娃。这些玩偶一眼看上去天真无邪,色彩生动,再看一眼,你就想“哇”地一声哭出来。这位出生在智利、生活在德国的艺术家,自从 90 年代开始在创作中引入羊毛和钩织技法之后,就不断用针线描绘着血淋淋的灾难场面,无论多么惹人喜爱的人物都免不了最悲惨的结局。她似乎在有意利用织物所传递的温暖和安全感,先卸下你的防备,再向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出击。

Patricia Waller, Who killed bambi?: Yarn, fabric, cotton wool,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32 x 24 x 18 in.; 2008
从觉得可爱到感到好笑,再到内心涌起酸楚……这就是帕特里夏的玩偶给观众带来的情绪波浪线。在帕特里夏的个人网站上,各系列玩偶作品按照年代排列。跟随时间的发展,她的作品主题也在不断推进。较早期的作品更像是对被生活击打得狼狈不堪的现代人的做出的无情讽刺,如果你的内心强大,还是可以对着这些你我共享的生活惨剧放声大笑,甚至还会觉得它带走了你的负面情绪,安抚了你受伤的心灵。而在近几年的新作中,帕特里夏的“幽默”愈发黑暗,可爱的形象和它们所欲探讨的沉重主题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苦涩的回味另人不安。
帕特里夏·沃勒的作品将于 9 月 20 日- 22 日,以影像的形式跟随 BROWNIE Project 参加 2019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Shanghai)。通过邮件,帕特里夏跟我们聊了聊她的作品是如何处理暴力、死亡,身份、娱乐这些议题的,也聊了聊批量生产时代手工劳动的价值,以及她如何利用“针线活”这种被认为具有“女性属性”的技法来表现严肃主题。

Patricia Waller, Cinderella: yarn,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height 34 in.; 2016

Patricia Waller, Winnie Pooh: Yarn, cotton wool, fabrics; crochet; hight bear 32 in.; 2012
创想计划: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最初是如何接触到“钩织”这种技法,并决定用它做艺术的?
帕特里夏·沃勒: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先强调一下,我的所有观点和论据都是从西方视角出发的。
90 年代,我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学院学习雕塑,在学校的最后一段时期里我开始考虑用织物做作品。我当时想找一种还没有在艺术领域内被广泛应用的材料,比如说,木头、石膏或者金属等等之外的材料。另外,我也不想依赖于机器和电子设备。
我人生中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块在学校课堂做的烤箱隔热布,我当时 9 岁。我做的那块布十分糟糕,被我妈扔进了垃圾桶里。所以,我其实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发现,我其实可以在作品里用钩织技术。我觉得大家能看出来,我的技术进步了!

Patricia Waller, Tweety: Yarn, polystyrene, wood,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28 x 28 x 33 in.; 2008
你怎么描述羊毛、织物等等给你的感觉?
羊毛这种材料,不管是钩织的还是编织的,都是一种亲昵、实用的产品,可以给予人类庇护和温暖,是一种无害的、舒适柔软的材料。
在艺术世界里,几乎没有哪种材料比羊毛更不受重视了。手工钩织这种方法,不仅对艺术发起进攻,也是如今这种批量生产时代的一种几乎是悖论式的尝试。在今天看来,纺织材料作品更像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怀旧物品。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手工做的,花上几个月才能做完一件。在批量生产时代,用手来制作手工艺品,看起来几乎是一个矛盾。通过这个过程,我对手工劳动的价值提出了疑问。
这种“家庭主妇艺术”的形象正是我要利用的。所以,第一眼看上去,我的作品天真无邪,但仔细看看,人们就会看到里面有一种邪恶的讽刺。如果观众看到我的作品以后开始微笑或者大笑,我就知道,我尝试接近他们的第一步获得了成功。

Patricia Waller, Accident 5: Cat: Yarn, cotton wool, length 20 in., 2004
你较早的作品经常描绘一些血淋淋的事故场景,主角都是可爱的小动物,透着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你当初做这些的意图是什么?
我的幽默当然是相当黑暗的,死亡、恐怖或者苦涩的主题都用钩织的方法表现出来。
残酷的伤残和肆无忌惮的屠杀,是好莱坞或者游戏工业内视觉中的一个标准主题。这些改变并塑造了我们对于现实中的暴力和死亡的视角。人们屈服于媒介中表现出的这种暴力审美的魔力。
生命权和保持身体完整的权利都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我们仍然每天都会遭遇暴力。暴力是一种基本体验,我们早在幼儿园玩沙子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同龄的小孩会拿塑料铲子打我们的头,把沙子扔到我们的眼睛里。也没有谁的童年是完美的,谁不曾因为一时气愤就扯掉玩具娃娃的手臂,或者抠掉他的眼睛呢?我提出的问题,关于我们的社会如何处理不同形式的暴力,并不断抬高的对于残忍的接受度。
在我的作品中,血是随处可见的。在这种奇特又夸张的行为中,血与材料发生了对立。对我来说,我的作品中的血也象征着我们的弱小,我们在命运面前的脆弱和无力。

Patricia Waller, Ernie: Yarn, cotton wool, fabrics, glass; crochet; 40 x 40 x 32 in.; 2011
之后你就做了“Broken Heroes”(破碎英雄)这个系列,主角变成了更明确的英雄人物。你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用这系列作品对我们社会中的明星崇拜表达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我们当今社会中的明星、名人、偶像是那些传统英雄的当代替代品。他们是模范也是希望的化身,反映了我们对于“天选之人”的渴望。英雄不会自己出现,他们是被制造出来的。他们总得保持光鲜亮丽;必须时刻处于积极状态,丝毫不可松懈;并且他们知道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别人的目光之中,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身份错乱。
“Broken Heroes”系列中的人物,都是流行文化中的著名偶像。第一眼看上去,这些作品很逗很好笑,因为他们展现了“英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芝麻街》当中无忧无虑的 Ernie 带着他的橡皮鸭醉倒在路边;蜘蛛侠绝望地缠在自己的网里;海绵宝宝成了自杀式炸弹,周身绑着能炸平一个街区的火药……
最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单一维度的屏幕上认识这些“英雄”的,把某些积极的性格特点投射上去,“失败的可能性”就不是他们的人设的一部分。

Patricia Waller, SpongeBob: Yarn, styrofoam, wood,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52 x 40 x 25 in.; 2011

Patricia Waller, Sword swallower: Yarn, styrofoam, synthetic material, wood; crochet; 20 x 11 x 43 in.; 2014
“Menschen, Tiere, Sensationen series”(人,动物,感受) 这个系列就更让人伤心了。
所有的钩织人物都必须以最惨烈的方式失败,栽倒在自己赖以生存的技巧和表演当中——否则就不是我的作品了。大变活人中的女模特被切成两半,吞剑人的剑刺穿了他自己的喉咙,平衡表演造成灾难……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血和恐怖镜头是否只是另一个为猎奇的观众们所精心准备的一股穿透脊椎的凉意,不管是不是这样吧,解读总归是开放的。
马戏团总是视觉领域里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毕加索、夏加尔、亨利·图卢兹·洛特雷克、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奥古斯特·麦克(August Macke), 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埃里希·黑克尔(Erich Heckel),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涉猎过这个主题的艺术家太多了。为什么视觉艺术家喜欢马戏团?可能是这种儿童剧般的充满启发性的世界,为我们描绘了自由和冒险前景,充满魔力和神秘。
小丑是一个普遍形象。他通过假扮“笨拙”来逗乐,展现出我们是如何荒唐地在悲喜交加的日常战斗中努力求生的。由于他的失败而引发的幸灾乐祸的笑声,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虚荣心。但于此同时,小丑也是反抗“想象力匮乏”的英雄。
即便在过去几十年间,环绕着马戏团的神话逐渐消解了,大众媒体却很快滴接手了这个角色:今天的真人秀节目跟过去的畸形秀一样,充斥着不相上下的庸俗的娱乐和丑陋的哗众取宠。

Patricia Waller, Clown: yarn, cotton wool, fabric, styrofoam,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55 x 36 c 36 in.; 2013
“Innocent”(无辜)这个系列是你最近两年完成的,这些作品让我们无法再笑出声。能说说你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吗?
“无辜”这个系列讲述的是对我们这个社会中最柔软的部分所施加的暴力——针对儿童的暴力。
在世界上某些危机四伏的地区,这种画面已经变得不能再熟悉了。饥饿、创伤、流离失所、童兵、强奸事件、性奴、身体残疾和死亡,覆盖着多种多样其他形式的精神和身体暴力,后者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也屡见不鲜。
我从媒体报道和援助申请案例中选用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能够抓住眼球的模式化的形象。我用一种通俗刻板的方式来运用这些悲惨的图像,而这些人物的外形正如那些着重强调“可爱”特征的娃娃一样,那么效果就被加强了。
在当今世界数不清的战争当中,儿童通常都是第一批受害者,成为冲突的每一方都默认接受的一种附带性伤害。他们所遭受的悲伤情绪及身体伤残将影响他们的一生。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儿童的关爱之心,让这些受苦的画面无法忍受。它迫使我们去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

Patricia Waller, Innocent II: yarn, cotton wool, styrofoam, wire,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length 40 in.; 2017

Patricia Waller, George: yarn, cotton wool, styrofoam, wire; Crochet; height 22in.; 2016
在创作时,你会有意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吗?
我在 90 年代开始在作品中使用羊毛,并且开始钩织。当时,我的同事都嘲笑我用这么老土的材料。在德国,我曾经是一个先锋,因为大多数人都拒绝认真对待这种方法。
羊毛和纱线不是主要艺术作品所应用的材料,而且人们认为它天然带有女性属性。因此如果女艺术家主动用它来创作,就能够达到反思我们在艺术、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效果。我的作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手工作品”(craftwork,例如陶艺、玻璃吹制等)就比“针线活”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更重要。但是最后,只有结果算数;相比起艺术家的性别、种族和血统,艺术本身更重要。
钩织很好的一点在于,我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干活”,不管是在工作室,还是在公园、火车或者飞机上。在火车或者飞机上钩织很有意思,人们总会问我在弄什么。我不想说“我在钩一条假腿”,所以我就说我在做连身裤,虽然我做的这玩意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什么裤子。

Patricia Waller, Pinocchio: Yarn, synthetic material, wire; chrochet; 51 x 20 x 36 in.; 2011
能否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小孩?
6岁以前,我是在南美洲的智利长大的。我没有太多那时候的记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娃娃,她的背后一个大洞,因为那个能让她叫“妈妈”的装置掉了出来。可能就是这点给我造成了创伤,而我现在还在用我的作品克服这种创伤……(我们觉得艺术家可能正在开玩笑——编辑注。)
搬到德国以后,我妈妈在幼儿园工作。每天晚上她都会用纸、纱线、布料等材料准备一些东西,和孩子们一起做些东西。所以手工,或者用手做东西,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2016 年你来中国做驻地项目。当时的体验如何?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是 2003 年。我当时参加了在北京的一次展览。那一次,我既困惑,又着迷。
几年前,应画廊主和藏家林明珠(Pearl Lam)的邀请,我第一次去了上海,立刻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但必须承认,当时因为害怕走丢,我只在公寓附近溜达过几条街。所以我很高兴 16 年“Shirley’s Temple-Art 的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让我有机会在上海呆上一个月!创始人Shirley 和她的团队非常积极地跟我一起工作,并做了许多超出工作范围外的事情。在当时的展览,“狂暴的钩针”之外,我也做了一次暖心的儿童慈善工作坊,帮助中国的白血病儿童父母。我非常激动。感谢STE和 Shirley,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在柏林又见过了很多次。
现在我很高兴跟 BROWNIE Project 一起参加这一届 PHOTOFAIRS Shanghai。
哦对了,上次我也学会用地铁了,我走完了整个城市!
谢谢你,帕特里夏!

Patricia Waller 《狂暴的钩针》展览现场,上海,2016,图片来自网络
艺术家帕特里夏·沃勒(Patricia Waller)所做的的羊毛钩织玩偶觉不是祖母哄你睡觉时拿出来的小娃娃。这些玩偶一眼看上去天真无邪,色彩生动,再看一眼,你就想“哇”地一声哭出来。这位出生在智利、生活在德国的艺术家,自从 90 年代开始在创作中引入羊毛和钩织技法之后,就不断用针线描绘着血淋淋的灾难场面,无论多么惹人喜爱的人物都免不了最悲惨的结局。她似乎在有意利用织物所传递的温暖和安全感,先卸下你的防备,再向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出击。

Patricia Waller, Who killed bambi?: Yarn, fabric, cotton wool,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32 x 24 x 18 in.; 2008
从觉得可爱到感到好笑,再到内心涌起酸楚……这就是帕特里夏的玩偶给观众带来的情绪波浪线。在帕特里夏的个人网站上,各系列玩偶作品按照年代排列。跟随时间的发展,她的作品主题也在不断推进。较早期的作品更像是对被生活击打得狼狈不堪的现代人的做出的无情讽刺,如果你的内心强大,还是可以对着这些你我共享的生活惨剧放声大笑,甚至还会觉得它带走了你的负面情绪,安抚了你受伤的心灵。而在近几年的新作中,帕特里夏的“幽默”愈发黑暗,可爱的形象和它们所欲探讨的沉重主题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苦涩的回味另人不安。
帕特里夏·沃勒的作品将于 9 月 20 日- 22 日,以影像的形式跟随 BROWNIE Project 参加 2019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Shanghai)。通过邮件,帕特里夏跟我们聊了聊她的作品是如何处理暴力、死亡,身份、娱乐这些议题的,也聊了聊批量生产时代手工劳动的价值,以及她如何利用“针线活”这种被认为具有“女性属性”的技法来表现严肃主题。

Patricia Waller, Cinderella: yarn,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height 34 in.; 2016

Patricia Waller, Winnie Pooh: Yarn, cotton wool, fabrics; crochet; hight bear 32 in.; 2012
创想计划: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最初是如何接触到“钩织”这种技法,并决定用它做艺术的?
帕特里夏·沃勒: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先强调一下,我的所有观点和论据都是从西方视角出发的。
90 年代,我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学院学习雕塑,在学校的最后一段时期里我开始考虑用织物做作品。我当时想找一种还没有在艺术领域内被广泛应用的材料,比如说,木头、石膏或者金属等等之外的材料。另外,我也不想依赖于机器和电子设备。
我人生中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块在学校课堂做的烤箱隔热布,我当时 9 岁。我做的那块布十分糟糕,被我妈扔进了垃圾桶里。所以,我其实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发现,我其实可以在作品里用钩织技术。我觉得大家能看出来,我的技术进步了!

Patricia Waller, Tweety: Yarn, polystyrene, wood,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28 x 28 x 33 in.; 2008
你怎么描述羊毛、织物等等给你的感觉?
羊毛这种材料,不管是钩织的还是编织的,都是一种亲昵、实用的产品,可以给予人类庇护和温暖,是一种无害的、舒适柔软的材料。
在艺术世界里,几乎没有哪种材料比羊毛更不受重视了。手工钩织这种方法,不仅对艺术发起进攻,也是如今这种批量生产时代的一种几乎是悖论式的尝试。在今天看来,纺织材料作品更像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怀旧物品。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手工做的,花上几个月才能做完一件。在批量生产时代,用手来制作手工艺品,看起来几乎是一个矛盾。通过这个过程,我对手工劳动的价值提出了疑问。
这种“家庭主妇艺术”的形象正是我要利用的。所以,第一眼看上去,我的作品天真无邪,但仔细看看,人们就会看到里面有一种邪恶的讽刺。如果观众看到我的作品以后开始微笑或者大笑,我就知道,我尝试接近他们的第一步获得了成功。

Patricia Waller, Accident 5: Cat: Yarn, cotton wool, length 20 in., 2004
你较早的作品经常描绘一些血淋淋的事故场景,主角都是可爱的小动物,透着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你当初做这些的意图是什么?
我的幽默当然是相当黑暗的,死亡、恐怖或者苦涩的主题都用钩织的方法表现出来。
残酷的伤残和肆无忌惮的屠杀,是好莱坞或者游戏工业内视觉中的一个标准主题。这些改变并塑造了我们对于现实中的暴力和死亡的视角。人们屈服于媒介中表现出的这种暴力审美的魔力。
生命权和保持身体完整的权利都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我们仍然每天都会遭遇暴力。暴力是一种基本体验,我们早在幼儿园玩沙子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同龄的小孩会拿塑料铲子打我们的头,把沙子扔到我们的眼睛里。也没有谁的童年是完美的,谁不曾因为一时气愤就扯掉玩具娃娃的手臂,或者抠掉他的眼睛呢?我提出的问题,关于我们的社会如何处理不同形式的暴力,并不断抬高的对于残忍的接受度。
在我的作品中,血是随处可见的。在这种奇特又夸张的行为中,血与材料发生了对立。对我来说,我的作品中的血也象征着我们的弱小,我们在命运面前的脆弱和无力。

Patricia Waller, Ernie: Yarn, cotton wool, fabrics, glass; crochet; 40 x 40 x 32 in.; 2011
之后你就做了“Broken Heroes”(破碎英雄)这个系列,主角变成了更明确的英雄人物。你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用这系列作品对我们社会中的明星崇拜表达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我们当今社会中的明星、名人、偶像是那些传统英雄的当代替代品。他们是模范也是希望的化身,反映了我们对于“天选之人”的渴望。英雄不会自己出现,他们是被制造出来的。他们总得保持光鲜亮丽;必须时刻处于积极状态,丝毫不可松懈;并且他们知道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别人的目光之中,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身份错乱。
“Broken Heroes”系列中的人物,都是流行文化中的著名偶像。第一眼看上去,这些作品很逗很好笑,因为他们展现了“英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芝麻街》当中无忧无虑的 Ernie 带着他的橡皮鸭醉倒在路边;蜘蛛侠绝望地缠在自己的网里;海绵宝宝成了自杀式炸弹,周身绑着能炸平一个街区的火药……
最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单一维度的屏幕上认识这些“英雄”的,把某些积极的性格特点投射上去,“失败的可能性”就不是他们的人设的一部分。

Patricia Waller, SpongeBob: Yarn, styrofoam, wood,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52 x 40 x 25 in.; 2011

Patricia Waller, Sword swallower: Yarn, styrofoam, synthetic material, wood; crochet; 20 x 11 x 43 in.; 2014
“Menschen, Tiere, Sensationen series”(人,动物,感受) 这个系列就更让人伤心了。
所有的钩织人物都必须以最惨烈的方式失败,栽倒在自己赖以生存的技巧和表演当中——否则就不是我的作品了。大变活人中的女模特被切成两半,吞剑人的剑刺穿了他自己的喉咙,平衡表演造成灾难……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血和恐怖镜头是否只是另一个为猎奇的观众们所精心准备的一股穿透脊椎的凉意,不管是不是这样吧,解读总归是开放的。
马戏团总是视觉领域里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毕加索、夏加尔、亨利·图卢兹·洛特雷克、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奥古斯特·麦克(August Macke), 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埃里希·黑克尔(Erich Heckel),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涉猎过这个主题的艺术家太多了。为什么视觉艺术家喜欢马戏团?可能是这种儿童剧般的充满启发性的世界,为我们描绘了自由和冒险前景,充满魔力和神秘。
小丑是一个普遍形象。他通过假扮“笨拙”来逗乐,展现出我们是如何荒唐地在悲喜交加的日常战斗中努力求生的。由于他的失败而引发的幸灾乐祸的笑声,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虚荣心。但于此同时,小丑也是反抗“想象力匮乏”的英雄。
即便在过去几十年间,环绕着马戏团的神话逐渐消解了,大众媒体却很快滴接手了这个角色:今天的真人秀节目跟过去的畸形秀一样,充斥着不相上下的庸俗的娱乐和丑陋的哗众取宠。

Patricia Waller, Clown: yarn, cotton wool, fabric, styrofoam,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55 x 36 c 36 in.; 2013
“Innocent”(无辜)这个系列是你最近两年完成的,这些作品让我们无法再笑出声。能说说你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吗?
“无辜”这个系列讲述的是对我们这个社会中最柔软的部分所施加的暴力——针对儿童的暴力。
在世界上某些危机四伏的地区,这种画面已经变得不能再熟悉了。饥饿、创伤、流离失所、童兵、强奸事件、性奴、身体残疾和死亡,覆盖着多种多样其他形式的精神和身体暴力,后者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也屡见不鲜。
我从媒体报道和援助申请案例中选用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能够抓住眼球的模式化的形象。我用一种通俗刻板的方式来运用这些悲惨的图像,而这些人物的外形正如那些着重强调“可爱”特征的娃娃一样,那么效果就被加强了。
在当今世界数不清的战争当中,儿童通常都是第一批受害者,成为冲突的每一方都默认接受的一种附带性伤害。他们所遭受的悲伤情绪及身体伤残将影响他们的一生。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儿童的关爱之心,让这些受苦的画面无法忍受。它迫使我们去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

Patricia Waller, Innocent II: yarn, cotton wool, styrofoam, wire, synthetic material; crochet; length 40 in.; 2017

Patricia Waller, George: yarn, cotton wool, styrofoam, wire; Crochet; height 22in.; 2016
在创作时,你会有意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吗?
我在 90 年代开始在作品中使用羊毛,并且开始钩织。当时,我的同事都嘲笑我用这么老土的材料。在德国,我曾经是一个先锋,因为大多数人都拒绝认真对待这种方法。
羊毛和纱线不是主要艺术作品所应用的材料,而且人们认为它天然带有女性属性。因此如果女艺术家主动用它来创作,就能够达到反思我们在艺术、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效果。我的作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手工作品”(craftwork,例如陶艺、玻璃吹制等)就比“针线活”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更重要。但是最后,只有结果算数;相比起艺术家的性别、种族和血统,艺术本身更重要。
钩织很好的一点在于,我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干活”,不管是在工作室,还是在公园、火车或者飞机上。在火车或者飞机上钩织很有意思,人们总会问我在弄什么。我不想说“我在钩一条假腿”,所以我就说我在做连身裤,虽然我做的这玩意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什么裤子。

Patricia Waller, Pinocchio: Yarn, synthetic material, wire; chrochet; 51 x 20 x 36 in.; 2011
能否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小孩?
6岁以前,我是在南美洲的智利长大的。我没有太多那时候的记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娃娃,她的背后一个大洞,因为那个能让她叫“妈妈”的装置掉了出来。可能就是这点给我造成了创伤,而我现在还在用我的作品克服这种创伤……(我们觉得艺术家可能正在开玩笑——编辑注。)
搬到德国以后,我妈妈在幼儿园工作。每天晚上她都会用纸、纱线、布料等材料准备一些东西,和孩子们一起做些东西。所以手工,或者用手做东西,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2016 年你来中国做驻地项目。当时的体验如何?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是 2003 年。我当时参加了在北京的一次展览。那一次,我既困惑,又着迷。
几年前,应画廊主和藏家林明珠(Pearl Lam)的邀请,我第一次去了上海,立刻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但必须承认,当时因为害怕走丢,我只在公寓附近溜达过几条街。所以我很高兴 16 年“Shirley’s Temple-Art 的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让我有机会在上海呆上一个月!创始人Shirley 和她的团队非常积极地跟我一起工作,并做了许多超出工作范围外的事情。在当时的展览,“狂暴的钩针”之外,我也做了一次暖心的儿童慈善工作坊,帮助中国的白血病儿童父母。我非常激动。感谢STE和 Shirley,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在柏林又见过了很多次。
现在我很高兴跟 BROWNIE Project 一起参加这一届 PHOTOFAIRS Shanghai。
哦对了,上次我也学会用地铁了,我走完了整个城市!
谢谢你,帕特里夏!

Patricia Waller 《狂暴的钩针》展览现场,上海,2016,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