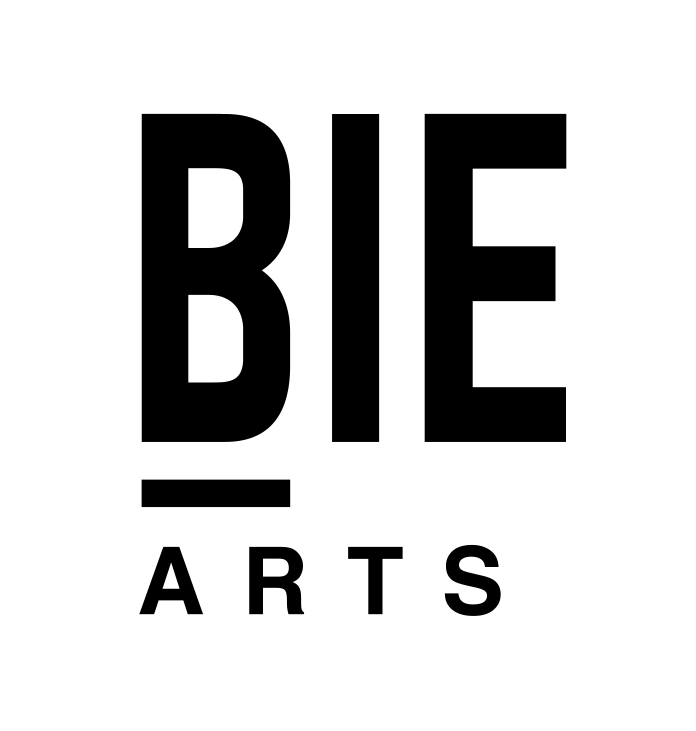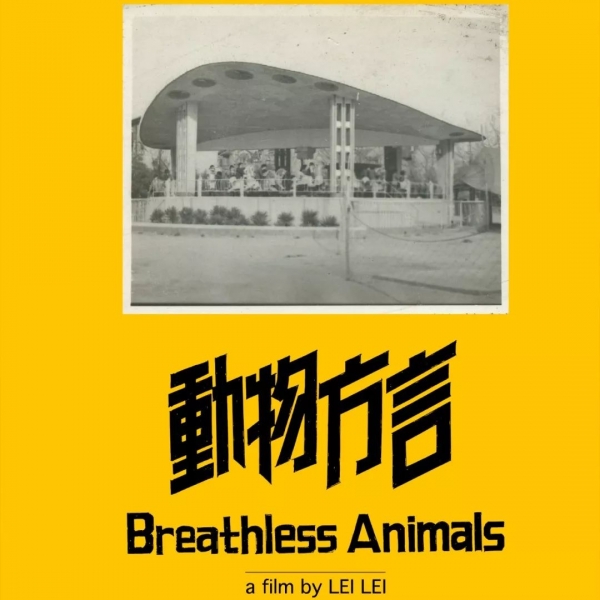黄汉明的脸像噩梦一样反复出现在经典电影场景中

中国科幻戏曲的舞台布景设计,2015,黄汉明
三年多以前,新加坡华裔艺术家黄汉明(Ming Wong)在个展《黄汉明:明年》中,把彼时的北京UCCA甬道变成了一个混合了西方科幻电影和中国传统戏剧舞台的奇异空间。当时,他已经开始着手在“科幻”和“粤剧”这两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概念当中建立联系。而走过那一条横穿文化与时空的通道之后,观众们见到了他更有代表性的创作方式:一个人扮演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角色,“翻拍”经典电影。在展览《黄汉明:明年》中,他重新演绎了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这之前,他还用相似的手法演绎过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灵魂》、波兰斯基的《唐人街》等多部电影——黄汉明的脸像噩梦一样反复出现在我们熟悉的场景中。

我中我,2013,黄汉明,图片来自网络
在“翻拍”电影的作品中,黄汉明把自己当作媒介,串接起多种不同层次的身份。一个有着典型东方面孔的男人,在镜头前一板一眼地扮演着西方贵妇、白人美少年、传统日本女性、女同性恋者、摩洛哥移民等与自己相去甚远的角色,吃力又拙劣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神情、语言和情绪。某种喜剧效果呼之欲出,与之相伴而生的,是被放大和凸显的身份错位感。
黄汉明2007年的作品《跟柏蒂娜学德语》在他的创作中有某种点题式的作用。这件作品在他搬去柏林居住的前夕完成,作品中,他扮演成法斯宾德电影《柏蒂娜的苦与泪》当中一位女性角色,表演了她情绪崩坏的一场戏,借此预演“自己作为一个超过35岁的单身、同性恋、少数族裔、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艺术家,在搬到柏林以后所可能遇到的情况中,会经历的动作、情感以及要表达的言辞——例如感到痛苦、绝望,或者溃不成军。”黄汉明总是通过这种错位的表演,把自己(或者别的演员)置于一个十分容易受伤的脆弱境地,如同一个突兀地出现在陌生文化中的他乡客,在周围和格格不入的自我之间艰难地寻找相连的纽带。这个异乡人的举动很容易引人发笑,但随后让人觉得更加荒唐的,则是人与人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和隔阂。

跟柏蒂娜学德语,2007,黄汉明

世界上的窗户(第 1 部分),2014,黄汉明
黄汉明“重演”的电影作品虽然并不都在一个时代,但他在其中对身份和文化的探索主要还是横向的。近几年,他开始把探索的方向向过去与未来展开。作为广东人的后裔,黄汉明同粤语文化有很深的联系。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粤剧这种传统戏曲形式其实具有很高的开放度,不仅可以进行电影化,也可以“在唱词中结合俚语和英语”,表达与社会时事和潮流相关的主题。正如他影像作品中不可思议的身份碰撞一样,他开始把古老的“粤剧”跟“科幻”拼接在一起。2014年,黄汉明在作品《世界上的窗户》(第 2 部分)当中聚焦“亚洲女性太空探索者”这个形象,其中就包括了含有粤剧元素的香港电影《嫦娥奔月》(1960)的片段。黄汉明的文化穿梭之旅中于是又加入了科学与神话、未来与宗教的维度。
在“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上,黄汉明延续他对中国传统戏曲和科幻的探索,创作了一部结合川剧与科幻的影像装置“竹制飞船”(Bamboo Spaceship)。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黄汉明。

明年,2016,黄汉明
创想计划:你在作品中经常扮演成不同的角色。你曾经提过,第一次表演时,你感到非常不自在,随着表演的经历增加,你有变得更熟练吗?这对创作是否有影响?“表演”这个行为在你的作品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黄汉明:在镜头前表演,是可以通过练习而变得越来越简单的。但同时我也做现场表演,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十分极端的挑战。表演我不熟悉的人物构成了我的一部分艺术实践,例如,说一种外语,唱另一种文化的传统歌曲,或者作为一个没接受过舞蹈训练的人表演一段舞蹈。我试图在表演中插入一道鸿沟,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这样可以放大自我意识,打断“表演”的幻觉。
展现不完美、展现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不稳定性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从中正好能表现出“变化”所拥有的潜力,“成为”(becoming)所拥有的潜力。 表演一个你不熟悉的东西,将暴露人作为人的脆弱。想要“成为”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而不断尝试就是人生意义所在。

生死威尼斯,2010,黄汉明
在你出生、长大、搬家的过程中,你曾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吗?
我在新加坡出生长大,那是一个现代国家,连接着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文化。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缺陷,因为我似乎没办法归属到某种悠久的历史或者文化当中去。我是华裔,但又不是大陆人;我是广东人,但我的英语和普通话又比粤语好;我在英国的学校系统中接受教育,但我又不是英国人;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个酷儿艺术家,等等。
但最后,我逐渐学会把自己的境遇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让我能够在不同的编码之间转换,让我有“不同的外衣”可以披,这样,我就拥有了刺进不同的文化语境的自信和灵活度。这一点对我的艺术实践有深刻的影响:我可以拉开一段距离,去检视世界不同地方的文化身份。

再造唐人街,2012,黄汉明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电影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成长过程中,我最早的灵感就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和流行文化:港剧、BBC 广播、美式情景喜剧、宝莱坞音乐剧、新加坡出产的马来电影等等。
新加坡还在挣扎着寻找自己在世界艺术史当中的位置。我的创作跟视觉艺术其实没有太多联系,我感兴趣的是宝莱坞、香港老电影中的通俗煽情剧情,以及英国戏剧和流行文化中的“变装”(Drag)的力量。
长大一些以后,我便开始投入到新加坡戏剧行业中,因为新加坡最早的作品就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最初那一代导演和剧作家真是相当有才华。那个时候,新加坡的剧场是了不起的地方,它挑战、刺激并捕捉着当地观众的情感与想象。
我最后终于在新加坡做戏剧编剧的工作。用不同的语言写作的经历和戏剧舞台布景的体验,让我见识到了后台的世界:排练、幕后制作,演员在角色内外转换,我也理解了我的演员同事们在事业中面对角色定式、文化刻板印象时的挣扎。 而我想要创造相当谁就当谁的可能性,能够表演任何我想表演的角色。这影响了我之后的艺术实践。

Biji Diva! 现场表演照片
你最近的作品更多的是现场表演,接下来的计划是怎样的呢?
20多年以后,我又被剧场重新吸引了,回到了现场表演,回到了剧本写作。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因为我们正处在过度依赖小屏幕乃至上瘾的时代。在共享的社会空间里观看一场演出,在现场剧场的背景下社交,又开始变得重要了,它可以打断当代媒介的隔离。在现场看剧,能带来一种活着的感觉、让人感到我们与人在一起、是某个共同体当中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很实在,是生活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
我很期待能再次回到剧场做现场表演。

中国科幻戏曲的舞台布景设计,2015,黄汉明
你的粤剧科幻作品项目进展如何?
我正在准备这部剧的叙事部分,之后将会从中发展出一部科幻粤剧电影的剧本和台词。其中包含在时间、空间和性别之间穿梭的元素,以及从过去到未来广东文化身份的变化。
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展出的作品“竹制飞船”吧,这件作品是如何延续了你对汉语科幻和地方戏剧的计划的?
我当时很有兴趣到中国西部去做一做调研。中国西南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都在经历十分快速的发展,它们对我来说如同是科幻城市,当地的建筑及其周围的环境都包含着丰富的时间层次。实际上,成都也正是中国的科幻之乡。
我也对川剧变脸很感兴趣,它似乎是中国诸多变化的一种符号化的体现。与此同时,成都还是流行音乐行业的心脏,其中也包括中国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Rap。实际上,我觉得 Rap 是一种当代“说唱”(边说边唱),而中国戏曲则是一种传统的“说唱”。所以在成都的新项目中,我写了一个科幻故事,把两代说唱——Rap 和川剧——连接在一起。我们最后做了一个 MV,在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竹子太空舱里进行展示。

竹制飞船,2018,黄汉明,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展览现场
这个竹子建筑结构是我和四川当地的竹子工艺大师一起做的。它是一个弯曲的时间隧道,观众可以走进来看视频。“竹制飞船”的灵感来自香港粤剧竹棚和成都传统茶馆,所以整个作品的概念跟“时空旅行”有关,在代际之间、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之间、在不同地理地点种种多种社会空间之间、在现代性和神秘事物之间、在传统和技术之间穿梭旅行。
这是你第一次到成都吗?能谈谈你对成都的印象吗?
2018 年初我第一次到成都,总共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发现还有好多东西没看。成都年轻人身上的能量和他们开放、好奇的态度,都预示着这将会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城市。这里的“蜀文化”和早期文明也很有意思,它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可能性。我认为,当地人之所以能够对“多元”和“差异”保持开放态度,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对历史和自觉和骄傲,以及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熟悉。这也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的好兆头。我相信这种开放也能够延伸到当地对科幻的态度上,连接到对另一个可能世界的想象当中。
谢谢你,黄汉明!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展览现场,黄汉明在作品前

艺术家黄汉明(左)和说唱歌手三锤(右),摄影:桌子,图片提供:“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执行组

中国科幻戏曲的舞台布景设计,2015,黄汉明
三年多以前,新加坡华裔艺术家黄汉明(Ming Wong)在个展《黄汉明:明年》中,把彼时的北京UCCA甬道变成了一个混合了西方科幻电影和中国传统戏剧舞台的奇异空间。当时,他已经开始着手在“科幻”和“粤剧”这两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概念当中建立联系。而走过那一条横穿文化与时空的通道之后,观众们见到了他更有代表性的创作方式:一个人扮演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角色,“翻拍”经典电影。在展览《黄汉明:明年》中,他重新演绎了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这之前,他还用相似的手法演绎过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灵魂》、波兰斯基的《唐人街》等多部电影——黄汉明的脸像噩梦一样反复出现在我们熟悉的场景中。

我中我,2013,黄汉明,图片来自网络
在“翻拍”电影的作品中,黄汉明把自己当作媒介,串接起多种不同层次的身份。一个有着典型东方面孔的男人,在镜头前一板一眼地扮演着西方贵妇、白人美少年、传统日本女性、女同性恋者、摩洛哥移民等与自己相去甚远的角色,吃力又拙劣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神情、语言和情绪。某种喜剧效果呼之欲出,与之相伴而生的,是被放大和凸显的身份错位感。

跟柏蒂娜学德语,2007,黄汉明
黄汉明2007年的作品《跟柏蒂娜学德语》在他的创作中有某种点题式的作用。这件作品在他搬去柏林居住的前夕完成,作品中,他扮演成法斯宾德电影《柏蒂娜的苦与泪》当中一位女性角色,表演了她情绪崩坏的一场戏,借此预演“自己作为一个超过35岁的单身、同性恋、少数族裔、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艺术家,在搬到柏林以后所可能遇到的情况中,会经历的动作、情感以及要表达的言辞——例如感到痛苦、绝望,或者溃不成军。”黄汉明总是通过这种错位的表演,把自己(或者别的演员)置于一个十分容易受伤的脆弱境地,如同一个突兀地出现在陌生文化中的他乡客,在周围和格格不入的自我之间艰难地寻找相连的纽带。这个异乡人的举动很容易引人发笑,但随后让人觉得更加荒唐的,则是人与人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和隔阂。

世界上的窗户(第 1 部分),2014,黄汉明
黄汉明“重演”的电影作品虽然并不都在一个时代,但他在其中对身份和文化的探索主要还是横向的。近几年,他开始把探索的方向向过去与未来展开。作为广东人的后裔,黄汉明同粤语文化有很深的联系。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粤剧这种传统戏曲形式其实具有很高的开放度,不仅可以进行电影化,也可以“在唱词中结合俚语和英语”,表达与社会时事和潮流相关的主题。正如他影像作品中不可思议的身份碰撞一样,他开始把古老的“粤剧”跟“科幻”拼接在一起。2014年,黄汉明在作品《世界上的窗户》(第 2 部分)当中聚焦“亚洲女性太空探索者”这个形象,其中就包括了含有粤剧元素的香港电影《嫦娥奔月》(1960)的片段。黄汉明的文化穿梭之旅中于是又加入了科学与神话、未来与宗教的维度。
在“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上,黄汉明延续他对中国传统戏曲和科幻的探索,创作了一部结合川剧与科幻的影像装置“竹制飞船”(Bamboo Spaceship)。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黄汉明。

明年,2016,黄汉明
创想计划:你在作品中经常扮演成不同的角色。你曾经提过,第一次表演时,你感到非常不自在,随着表演的经历增加,你有变得更熟练吗?这对创作是否有影响?“表演”这个行为在你的作品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黄汉明:在镜头前表演,是可以通过练习而变得越来越简单的。但同时我也做现场表演,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十分极端的挑战。表演我不熟悉的人物构成了我的一部分艺术实践,例如,说一种外语,唱另一种文化的传统歌曲,或者作为一个没接受过舞蹈训练的人表演一段舞蹈。我试图在表演中插入一道鸿沟,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这样可以放大自我意识,打断“表演”的幻觉。
展现不完美、展现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不稳定性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从中正好能表现出“变化”所拥有的潜力,“成为”(becoming)所拥有的潜力。 表演一个你不熟悉的东西,将暴露人作为人的脆弱。想要“成为”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而不断尝试就是人生意义所在。

生死威尼斯,2010,黄汉明
在你出生、长大、搬家的过程中,你曾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吗?
我在新加坡出生长大,那是一个现代国家,连接着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文化。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缺陷,因为我似乎没办法归属到某种悠久的历史或者文化当中去。我是华裔,但又不是大陆人;我是广东人,但我的英语和普通话又比粤语好;我在英国的学校系统中接受教育,但我又不是英国人;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个酷儿艺术家,等等。
但最后,我逐渐学会把自己的境遇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让我能够在不同的编码之间转换,让我有“不同的外衣”可以披,这样,我就拥有了刺进不同的文化语境的自信和灵活度。这一点对我的艺术实践有深刻的影响:我可以拉开一段距离,去检视世界不同地方的文化身份。

再造唐人街,2012,黄汉明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电影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成长过程中,我最早的灵感就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和流行文化:港剧、BBC 广播、美式情景喜剧、宝莱坞音乐剧、新加坡出产的马来电影等等。
新加坡还在挣扎着寻找自己在世界艺术史当中的位置。我的创作跟视觉艺术其实没有太多联系,我感兴趣的是宝莱坞、香港老电影中的通俗煽情剧情,以及英国戏剧和流行文化中的“变装”(Drag)的力量。
长大一些以后,我便开始投入到新加坡戏剧行业中,因为新加坡最早的作品就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最初那一代导演和剧作家真是相当有才华。那个时候,新加坡的剧场是了不起的地方,它挑战、刺激并捕捉着当地观众的情感与想象。
我最后终于在新加坡做戏剧编剧的工作。用不同的语言写作的经历和戏剧舞台布景的体验,让我见识到了后台的世界:排练、幕后制作,演员在角色内外转换,我也理解了我的演员同事们在事业中面对角色定式、文化刻板印象时的挣扎。 而我想要创造相当谁就当谁的可能性,能够表演任何我想表演的角色。这影响了我之后的艺术实践。

Biji Diva! 现场表演照片
你最近的作品更多的是现场表演,接下来的计划是怎样的呢?
20多年以后,我又被剧场重新吸引了,回到了现场表演,回到了剧本写作。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因为我们正处在过度依赖小屏幕乃至上瘾的时代。在共享的社会空间里观看一场演出,在现场剧场的背景下社交,又开始变得重要了,它可以打断当代媒介的隔离。在现场看剧,能带来一种活着的感觉、让人感到我们与人在一起、是某个共同体当中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很实在,是生活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
我很期待能再次回到剧场做现场表演。

中国科幻戏曲的舞台布景设计,2015,黄汉明
你的粤剧科幻作品项目进展如何?
我正在准备这部剧的叙事部分,之后将会从中发展出一部科幻粤剧电影的剧本和台词。其中包含在时间、空间和性别之间穿梭的元素,以及从过去到未来广东文化身份的变化。
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展出的作品“竹制飞船”吧,这件作品是如何延续了你对汉语科幻和地方戏剧的计划的?
我当时很有兴趣到中国西部去做一做调研。中国西南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都在经历十分快速的发展,它们对我来说如同是科幻城市,当地的建筑及其周围的环境都包含着丰富的时间层次。实际上,成都也正是中国的科幻之乡。
我也对川剧变脸很感兴趣,它似乎是中国诸多变化的一种符号化的体现。与此同时,成都还是流行音乐行业的心脏,其中也包括中国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Rap。实际上,我觉得 Rap 是一种当代“说唱”(边说边唱),而中国戏曲则是一种传统的“说唱”。所以在成都的新项目中,我写了一个科幻故事,把两代说唱——Rap 和川剧——连接在一起。我们最后做了一个 MV,在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竹子太空舱里进行展示。

竹制飞船,2018,黄汉明,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展览现场
这个竹子建筑结构是我和四川当地的竹子工艺大师一起做的。它是一个弯曲的时间隧道,观众可以走进来看视频。“竹制飞船”的灵感来自香港粤剧竹棚和成都传统茶馆,所以整个作品的概念跟“时空旅行”有关,在代际之间、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之间、在不同地理地点种种多种社会空间之间、在现代性和神秘事物之间、在传统和技术之间穿梭旅行。
这是你第一次到成都吗?能谈谈你对成都的印象吗?
2018 年初我第一次到成都,总共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发现还有好多东西没看。成都年轻人身上的能量和他们开放、好奇的态度,都预示着这将会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城市。这里的“蜀文化”和早期文明也很有意思,它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可能性。我认为,当地人之所以能够对“多元”和“差异”保持开放态度,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对历史和自觉和骄傲,以及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熟悉。这也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的好兆头。我相信这种开放也能够延伸到当地对科幻的态度上,连接到对另一个可能世界的想象当中。
谢谢你,黄汉明!

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展览现场,黄汉明在作品前

艺术家黄汉明(左)和说唱歌手三锤(右),摄影:桌子,图片提供:“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执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