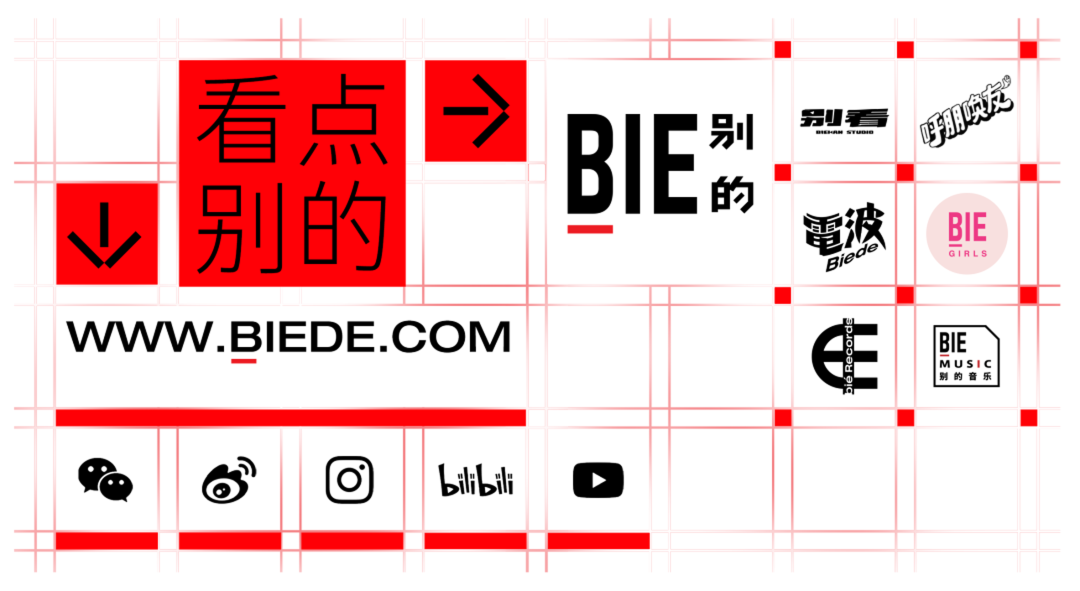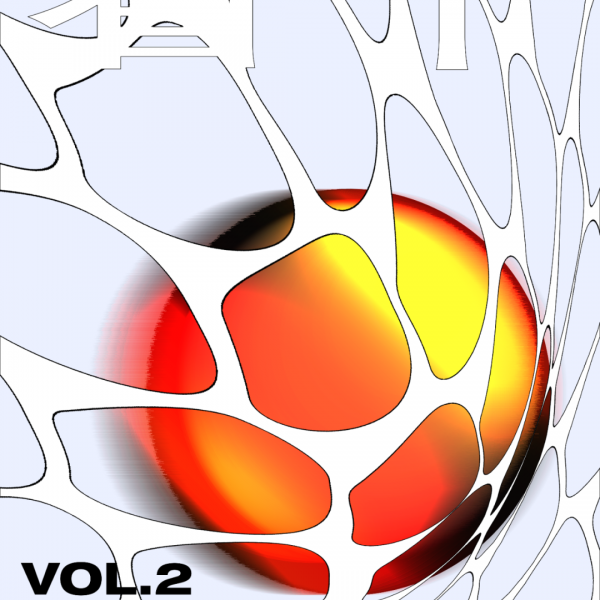阿紫的故事:越南新娘,何以为家?
别的女孩: 因生活所迫而选择外嫁(甚至有的是被贩卖、拐卖)的 “外籍新娘”,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台湾纪录片《阿紫》(2019)的主人公就是一位从越南远嫁台湾的 “外籍新娘”。阿紫的身上承担着两个地方的家庭,她终日为两个家而打拼,并自认为这就是她的使命所在。她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海边劳作的时候,彼时的她终于做回了自己,一个在漂泊之中依然努力散发生命热度的个体。

冬 旅 人
远处白色风车缓缓转动,几只水牛沿着道路悠闲地吃着草,村子的公车站牌旁边堆砌着小山似的蚵仔壳。这里没有 101 也没有文创园,是人们不太熟悉的台湾乡下,连地名都鲜少听到:云林。这个濒临台湾海峡、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县城以农业闻名,有台湾粮仓之称。阿紫一家也以种蒜头和稻米为生。
彼时,阿紫已经嫁来台湾六七年了,和阿龙育有两个女儿。虽然嘴上把越南人嫁女儿形容为 “比买一只猪还不值得”,阿龙心底里却很尊敬自己的老婆。他说阿紫选择嫁来台湾 “很有勇气”,因为 “被选上就必须无条件嫁给人家”,不知道嫁过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家里改善经济条件。

纪录片《阿紫》剧照
相较于那些嫁来没多久就帮老家盖了新房的外配,阿紫嫁得 “不算好”。家中经济来源主要靠农作物,每年的收成和蒜头的价格都不稳定。即便收成好了,阿紫想要寄钱给越南的家人也并不容易 —— 要丈夫同意,还要瞒着婆婆。
在台湾,娶外籍配偶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外籍女性通过乡亲介绍或中介组织嫁到台湾。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里的外籍配偶主要来自越南、柬埔寨、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农村。这些女性普遍因为家庭贫困而选择远嫁台湾,其结婚对象也多为因贫困或残疾等原因在台湾无法娶到老婆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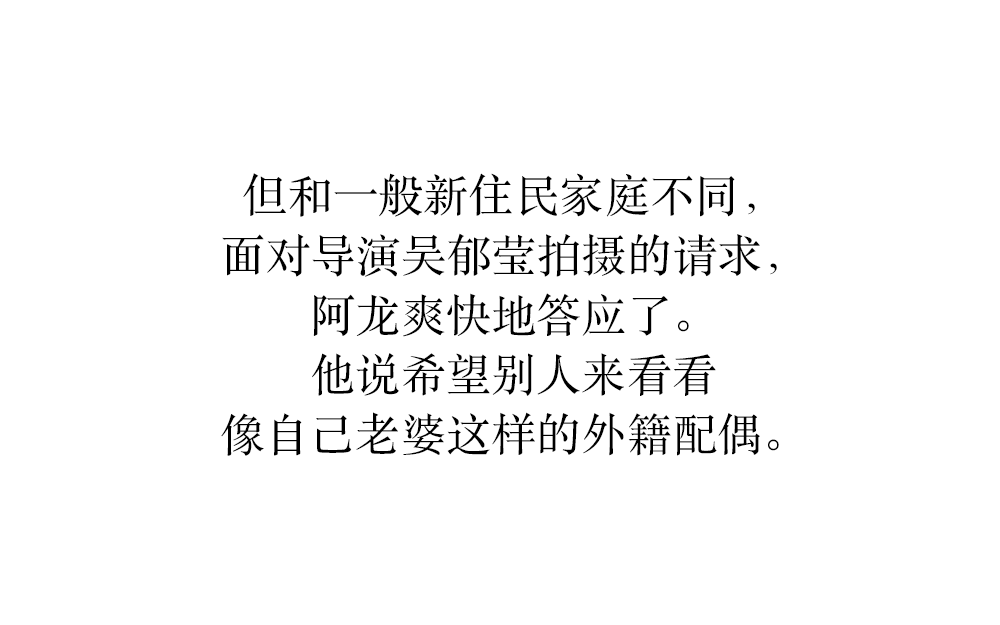
和阿紫结婚时,阿龙已经 45 岁了。因为右脚残疾,阿龙小学毕业就去外地学做裁缝,“裁缝只需要用手,脚不太重要”。学成之后,他在台北的高级店铺做师傅。那时,还是手工缝制西装兴盛的年代。阿龙回忆说做一套西装要十多个小时,一个月收入能有七八万台币,在台北市也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后来手工西装没落,被机器代替,阿龙丢掉了工作,才又回到老家乡下务农。

新住民上课情形。©天下资料
因为经济状况不好,以及小儿麻痹造成的右脚残疾,再加上近年来台湾农村适婚女性几乎都进城打工,阿龙一直没能成家。为了满足母亲传宗接代的要求,阿龙接受了跨国婚姻。
像阿龙这样跨国娶妻的新住民家庭,在台湾并不少见。根据台湾行政院的统计,截止到 2019 年,台湾外籍配偶高达 54.9 万人,其中越南籍为 10.7 万人。将阿紫与阿龙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产业区域化背景下持续凋敝的农村。与在台湾乡下娶不到老婆的 “阿龙们” 相似的是,生长于越南农村、家境拮据的 “阿紫们”,生活也并没有给予她们太多选择:要么进城打工,要么远嫁他乡。
阿紫的故乡在越南南部后江省乡下,这里的人们大多靠种植和捕捞维持生计。阿紫的爸爸捕鱼养鸭,勉强糊口,一家人挤在一间用铁皮搭起来的简陋房屋中。由于地处湄公河三角洲,每年 8 月到 11 月洪水泛滥,屋内连日积水;遭逢台风暴雨,更有随时倒塌的危险。
嫁来台湾前,阿紫在城里的咖啡馆打工,有一个很爱她的男友,原本可以顺其自然地结婚,平淡一生。但由于阿紫家实在困窘:大哥在城里打工,弟弟体弱陪在父母身边,两个姐姐早已出嫁,根据当地风俗,出嫁的女儿 “有钱也不能再拿回婆家”。村里的媒人屡次上门劝说,阿紫便瞒着男友去河内 “相亲”。

纪录片《阿紫》剧照
说是 “相亲”,其实真相残酷得多。这些来自越南农村各地的适龄女孩,在 “媒人们” 的劝诱下来到河内,等待着来自韩国、新加坡、台湾或大陆的男人的挑选。一旦被选中,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因为拒绝就意味着罚钱,而这些女孩子大多家境贫穷、甚至是向中介借钱来 “相亲”。
这些选择嫁到国外的女孩大多背负着改善家庭状况的重担。就像阿紫爸爸说的,“这里的人靠着把女儿嫁到国外,才过得下去……男人要娶越南女人很简单,只要他是外国人,就算他很穷也可以娶。” 事实上,娶外籍配偶的外国人主要是农村或劳工阶层男性,在其本国也往往是社会边缘者,不是经济欠佳,便是身体残疾。

当年新住民在新店市大丰国小上课的情形。©天下资料,邱剑英摄
台湾研究者黄晓娟指出,在此类商品化的跨国婚姻中,双方皆为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的男女,在资本国际化与劳动力自由化的过程中,藉由国际婚姻而谋求出路。但外国男子想要娶妻成功,往往也要花费不菲,根据 2000 年初的调研数据,娶妻者要支付中介方总共大约新台币四五十万,其中给到新娘家庭的聘金只占十分之一,但对于收入微薄的东南亚家庭,却实非小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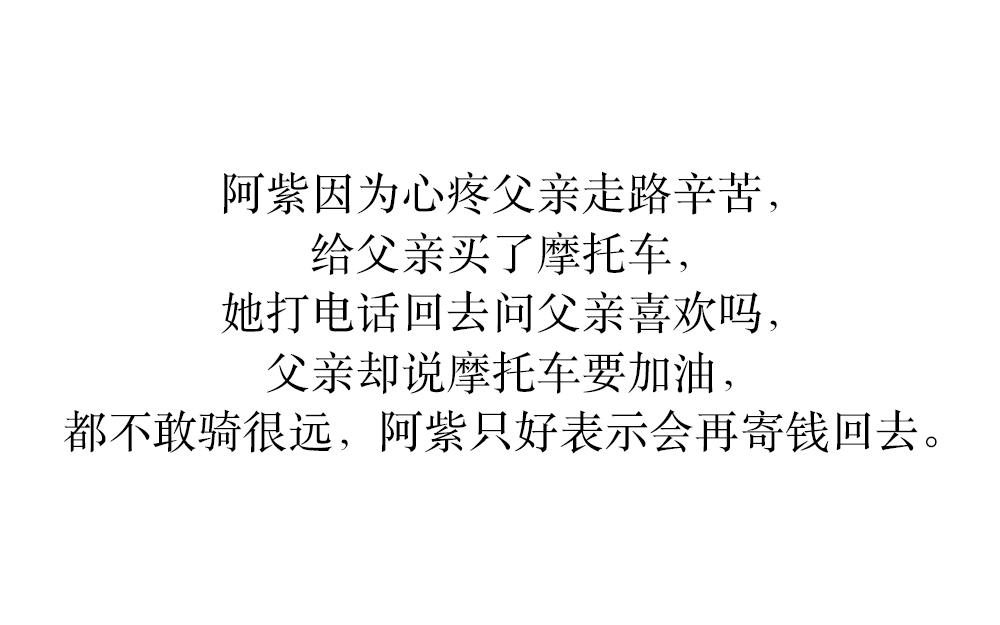
即便是嫁到台湾,外籍配偶们也依然要想尽办法,不断寄钱回家,补贴家用、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情节:阿紫因为心疼父亲走路辛苦,给父亲买了摩托车,她打电话回去问父亲喜欢吗,父亲却说摩托车要加油,都不敢骑很远。阿紫只好表示会再寄钱回去。
对于 “阿紫们” 来说,原生家庭就像是一个永远背负在身上的重担。或许因为这样的事情在越南太过寻常,在阿紫父亲看来,这就是阿紫的命:“这些女孩子嫁到国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她们的家庭牺牲。”
影片结尾的场景也颇富意味。走街串巷的媒人再次来到阿紫父母家中,如今坐在对面的是阿紫的侄女,十七岁的少女,亭亭玉立,面带青涩。阿紫的母亲和媒人寒暄,担心地问,如果没钱支付路费怎么办。
媒人微笑:“我可以借一些交通费和住宿费,等选上了以后,就得把钱还我。”
“假如没被选上呢?”
“那她要留在那里,借钱留到被选上为止。签了合约就不能离开的。” 媒人又补充道:“大部分外国男人都是很好的。假如你又漂亮又温柔,他们会更喜欢你。”
梳妆打扮好的女孩子定定地望着前面某处,仿佛等待着未知的命运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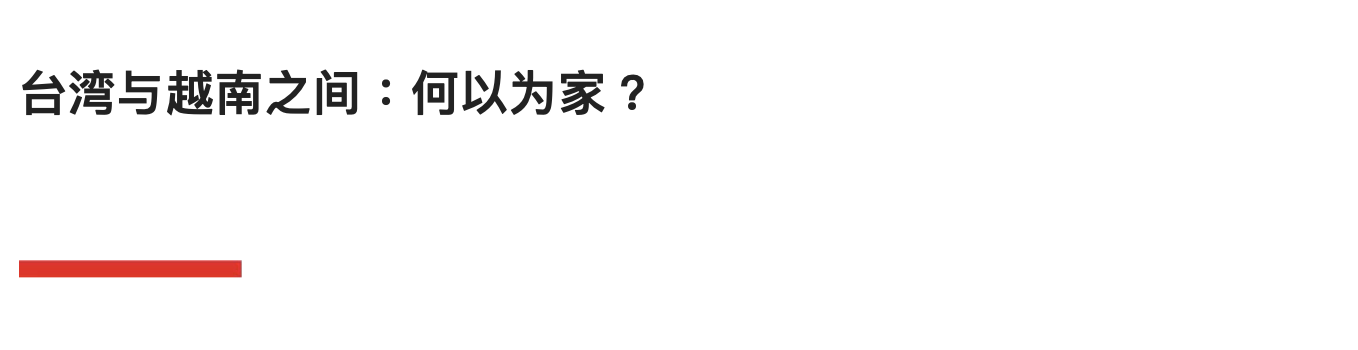
来台湾六七年后,阿紫终于帮家里盖了新房子。新房建成不久,阿紫带着两个女儿回越南探亲。在招待邻里的宴席上,阿紫笑得格外开心,也很骄傲。或许这就是支撑她在台湾孤独打拼下去的动力。
对于原生家庭而言,阿紫是不折不扣的 “A Good Daughter”(亦是本片的英文名),但对阿龙的母亲、阿紫的婆婆来说,阿紫却不是一个好媳妇。在阿龙母亲眼里,这个越南媳妇头脑不好,不会看人眼色,又不易管教。为了能寄钱回越南,阿紫常常早出晚归地打零工,无暇照顾两个小孩和老人。婆媳两人也常常因此产生口角,进而将阿龙也卷入其中。但阿龙一向极为孝顺,总是要求阿紫让步。影片中二人爆发了最激烈的一场争吵,阿紫抱怨:“不管做对做错,她都要骂我……我嫁给你太痛苦了”,继而嚎啕大哭。阿龙则抽着烟,眉头紧锁。

纪录片《阿紫》剧照
采蚵结束后跃入水中冲凉,是阿紫在台湾为数不多的欢乐时刻。或许那片海水让她想起故乡的河水,以及在河中嬉戏的过往时光。阿紫脸上浮现灿烂的笑容,如孩子般单纯而快乐。似乎唯有这样的时刻才能让她忘记工作的脏累、婆婆的苛责与丈夫的不理解。
时隔多年,阿紫回首当初嫁来台湾的决定,并不后悔:“来这里好坏,我自己承担,我是舍不得我们家里的人受苦。” “在我家那边一辈子都不可能轻松,没地方赚钱,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嫁给一个自己选的越南人是很好,但是我看了很多,没钱是没用的。钱真的是太重要了。我家需要我养两个老人家。再怎么样,我也不要回来越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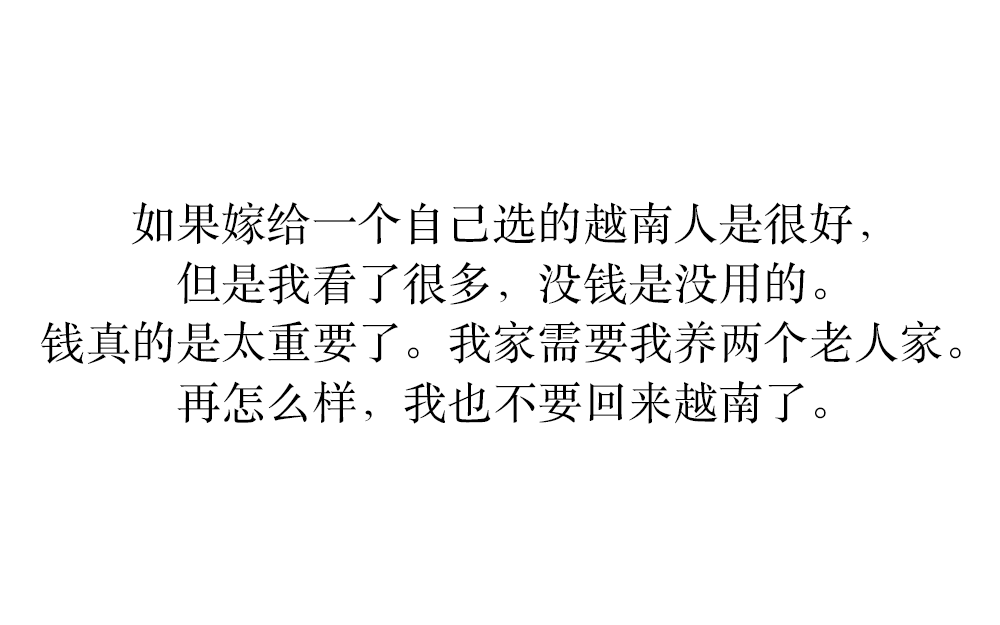
从越南回来,阿紫打算继续寄钱回家、帮大哥修房子,这个决定没有得到阿龙的支持。眼看着两个孩子逐渐长大,阿龙认为阿紫应该更多为孩子们的将来打算:“她赚钱主要还是为了她家里的人在付出。她没有以这边的家庭为主。”
一面是故乡家人的期待,一面是丈夫和婆婆的要求;一面是不会再回去的故乡,一面是无法完全融入的台湾。作为一名有主见与行动力的女性,她选择远嫁台湾,不顾婆婆与丈夫的反对,打工赚钱,接济越南家庭,但另一方面,她依然无法摆脱原生家庭对她做一个 “好女儿” 的要求。进退两难之间,阿紫孤独地打拼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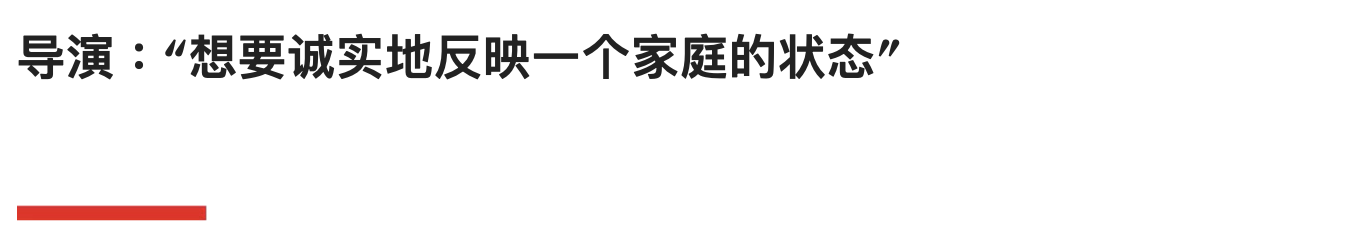
从越南回来,阿紫打算继续寄钱回家、帮大哥修房子,这个决定没有得到阿龙的支持。眼看着两个孩子逐渐长大,阿龙认为阿紫应该更多为孩子们的将来打算:“她赚钱主要还是为了她家里的人在付出。她没有以这边的家庭为主。”
一面是故乡家人的期待,一面是丈夫和婆婆的要求;一面是不会再回去的故乡,一面是无法完全融入的台湾。作为一名有主见与行动力的女性,她选择远嫁台湾,不顾婆婆与丈夫的反对,打工赚钱,接济越南家庭,但另一方面,她依然无法摆脱原生家庭对她做一个 “好女儿” 的要求。进退两难之间,阿紫孤独地打拼着。

如今,像阿紫这样的新住民群体在台湾的整体境况已有了很大改善,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保障他们的权益,一些自发组织的民间机构也为他们融入台湾社会与学习本地文化提供了各种支持。《阿紫》这样的纪录片亦为大众了解他们、为群体污名化做出了贡献。
阿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命运是如何被镶嵌在各自的时代处境之中,与全球资本、人员流动的不平等结构之中;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阿紫自身亦在此间主动作出了目标性的个体选择。这里有她无法决定的部分,也有她坚毅选择的部分 —— 只是附加在她身上的担子、她所勉力支撑的生活,的确是沉重而漫长的。
当被问到阿紫的近况时,导演吴郁莹这样说道:“就是生活。其实还是一样。越南还是很需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