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内向的人决定做一名旅行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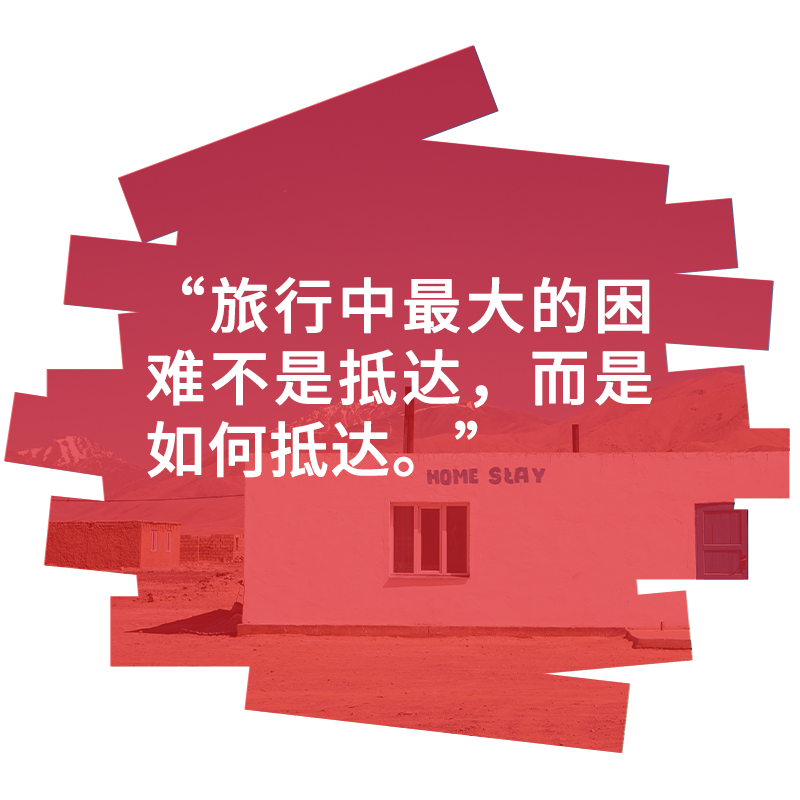

刘子超暴露出他是个地道北京人,不是通过口音(他的普通话毫无破绽),而是从他面不改色地踱出胡同里没有隔断的公共卫生间那一刻。
在我们的身后是冷秋下的白塔公园,公园里的鸭子船孤苦地停摆在湖边。国庆假期,北京的天气就如他在《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开篇中所写,“我离开柏林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阴沉得像一块陈旧的大理石。”
说起来有些难以解释,在所有的创造性工作中,人们唯独钟爱去追问一位作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的?”对于这个问题,诗人布考斯基有过一个经典回答,老爷子喷着烟一脸戏谑地对镜头说:Nobody ever realizes they're a writer. They only think they're a writer.

《午夜降临前抵达》插图

一个内向的记者
刘子超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当作家,那时他并未写出任何一本书。2016 年他辞掉工作,开始旅行与写作时,“旅行文学” 和 “刘子超” 对中文世界读者而言都还是陌生的,大家的名词舒适圈里仍是 “游记” 和 “旅行攻略”。
辞职以前,刘子超的职业是记者。如今再去搜索,还能找到一篇 2009 年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署名那栏写着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香港”。
他记得采访结束后,诗人北岛请他和另一位同事去吃饭。走在香港的街道上,北岛诚恳地问他,你这么不爱讲话,怎么做记者呀?提到这一茬时刘子超自己笑了起来,他说在北岛家里做采访,作为提问者的他时常让场面陷入沉默,“问着问着,就冷场了”。
刘子超的话的确很少,废话闲话近乎没有,聊天时,总会让人产生一种需要让场面别冷下去的义务意识。不说话的时候他安静地注视某个地方,当目光移向你时,你会清楚地感知到,他在观察你。善观察和爱喝酒,两把钥匙让他在旅途中总不会错过认识有趣的陌生人。
他曾反复分享《失落的卫星》里他所遇见的三个人:想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尔吉斯青年作家阿拜,他曾在聊天时向刘子超传授自己总结的诺奖诀窍;想要学习中文离开塔吉克斯坦的男孩 “幸运”,他们在大街上搭讪认识,幸运对他说 “我被困住了,哥”;还有在咸海边做生意挖虫卵的中国商人 “咸海王”,他打发孤独的方式是骑着摩托冲上不远的沙丘,吓唬那匹逗留在营地附近的母狼。他们各自代表中亚五国日常生活的某个切面,牵扯出一种不独属于自己的困境,那种拉扯感在他的眼里和笔下,能够隐喻世界和文明。

《失落的卫星》插图
刘子超的选择透出某种偏好。最初做记者时,他参与报道过一起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由于涉案人员涉及组织卖淫,牵涉被害人大多未成年,事件的前期报道是在暗访下进行的。刘子超在当地的线人是个名副其实的 “社会老大哥”,大哥熟练地带他来到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问那里的人,这儿有姑娘吗?睡眼惺忪的女孩被叫醒后踱到他俩面前,顶着看不出年龄的一张脸。
讲起这段经历时,他在那位大哥那里停顿了稍许。老大哥是在记者接触下主动站出来做联络人的,他或许也有与外面世界对话的诉求。当地的人事风物经由他穿针引线,在随后记者写下的报道中呈现出本来的面貌。最终稿件里自然是不会有老大哥这个人物存在,但真实的现场中,故事得以显现和推进,总是靠着不同时空中这个或那个老大哥。如果这样说来,从习水到中亚,刘子超所体验的、所注目的本质是相通的。只是这一次,老大哥们开始有了自己的面孔、名字和故事。

决定当作家之后
刘子超参与见证了严肃媒体黄金年代的尾声,表达者的笔杆子从硬朗走向疏松,他所在的南方集团旗下杂志《ACROSS穿越》到后来整刊被砍,编辑部散了,那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表达一些什么的时期逐渐过去,之后的故事属于之后。
那会儿他辞去广州的工作回到北京,将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全部提取出来,一共十几万,这便是他全职文学创作的启动资金。他想,人在何时都需要一个清晰的身份认知,“作家” 便是他此后对自己的认知与要求。
辞职后不久,有次他去医院看病填病历,职业那栏他填了 “作家”,机器吐出单子,他看到那一栏显示为 “未分类的其他职业”。
确立坐标和确认自己是在启程和写作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2012 年他搭乘火车和大巴一路从柏林向东,每到下榻处,便掏出随身的本子。他记下前往布拉格的车厢中令他不适的蒜蓉面包,布达佩斯的塞切尼温泉和古拉什,卢布尔雅那纵横的小巷,旅途结束于米兰旅馆的基安蒂红酒。这些笔记跟随他回到北京,回到年近二十八、单身辞职男性的生活轨迹中,陪他一同迷茫和沮丧,随后成为他的第一部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夏》章。这本叙写中欧的书分为夏、冬两个部分,被称为刘子超的 “出发之作”。


《午夜降临前抵达》插图
第一部作品出版时,刘子超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雀跃,他表现得很平静。仔细回忆起来,最近五年他都没有情绪太起伏的时刻。第一场读者见面会是在上海某个书店,活动结束后他收到一个巨大的匿名野兽派花篮。后来《失落的卫星》大火,他也曾找机会在某些场合提起这事,他有时会想,这样一个从那么早期就关注我的读者会在此刻的分享现场吗?
这谜题至今未解,过去几年他去到中欧,印度,东南亚,随后是广袤的中亚,每次旅程都以一部作品作结。旅行写作的初期,刘子超处在某种表达的困境里,那时他依然有许多观点想要借景抒发,不少自我诘问从风景和人物里冒头,那样一个时期过去之后,对旅行的见解没那么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本来就不太有的 ego 现在更小了”,他得以更自如地进入遥远的生活,抓住不同处境下的 “他们” 与 “我们” 的相似性,以中文表达浩繁的世界经验。
在万事停摆的 2020,《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对所有受困家中的读者而言成为天地间一剂慰藉和一扇窗。苏联解体后,中亚沦为全球化浪潮的边缘,又落入博弈大国间的夹缝,“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拉扯与裂痕状态总在吸引刘子超,他笔下的那片土地,再也不是作为地图上 “温带大陆性气候” 或 “ 200mm 等降水量线” 那样的整体而存在,那里有突厥人、波斯人、高加索人、乌兹别克人等不同种族的子民,有过去对我们而言神秘的斯坦们,和它们所代表的被世界遗落的生活方式。


《失落的卫星》插图
2014 年风靡一时的 “蚂蜂窝” 曾将他评为 “年度旅行家”,到 2021 年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时,刘子超凭作品《失落的卫星》获得 “年度青年作家” 荣誉。他曾引用作家保罗·鲍尔斯,在旅行文学作者中区分写东西的旅行者(a traveler who writes)和去旅行的作家(a writer who travels),他写,“前者兴之所至,后者则有更高的文学追求。我暗自希望自己成为后者。”2019 年 “全球真实故事奖” 评委会主席玛格丽特·斯普雷彻评价说:“《失落的卫星》可远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它是一部少见、非凡的文学作品。”

“旅行很少在我们认为的地方开始”
还在念中学时,刘子超参加过 “文艺青年的黄埔军校”——新概念作文大赛,他记得那会儿是第四届,他拿了全国二等奖,那一年的全国一等奖是郭敬明。他也在北岛创办的文学刊物《今天》上发表小说,那是公众号还未成为阅读习惯的近十年前。高中时,他就常常从学校传达室领回成叠的读者来信,他一一读过,从未提笔回复。如今读者的声音他也总会挨个看过,看过便过了。
“偶然交汇的流星” 是刘子超总爱提起的意象,或许这也是他最偏爱的交往距离。刘子超仍和他的中亚朋友们保持着一定联系。想要来中国的 “幸运” 如愿来到中国,在小城开餐馆的女孩依然开着餐馆,做短期旅游向导的倒是因为疫情不得不寻找别的差事养活自己。那些书里的人重新变得遥远,他们都像天空中曾经交汇的彗星,朝着各自方向继续前行。
活在框架感里的刘子超绕了一个圈,如今又开始做记者了。
这回是在拉萨,杂志社发来工作邀请,他负责的内容是 “与西藏的风土人情相关的一切”。今年五一假期,他从北京把车开了过去,生活出行变得便利起来。聊起去拉萨的初衷,自然是绕不开疫情。防疫政策下他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出国旅行了,他于是想,为什么不试着去一个新的地方重建生活呢,全然陌生的拉萨就这样成为选项,他欣然应下工作,只身来到拉萨。

刘子超在藏地
这次重建倒是令他觉得过于顺利了。一个人开启异地生活,从找房、安顿、认识当地人到重新建立起社交圈,一切都自然而快速地发生。出差的路上总能看到雪山,在日喀则市,珠穆朗玛就在眼前,一群演奏甲谐的当地人在他的镜头前缓慢起舞。他认识了一位从内地西藏班一路念书考出西藏的藏族诗人,那人后来回到西藏考取公务员,被分配到寺院中做驻寺官员,和院中喇嘛们终日相伴,他们偶尔也聊天。
2021 就快过去,刘子超又要出发了。他很早就定下环黑海的旅行计划,如今疫情趋于常态,各国签证政策陆续稳定,启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我问他,阿富汗内乱会对你的计划产生影响吗?他答,对于旅行者而言,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的局势或许比占领之前更加安全。处于拉锯状态的国家会在两套规则中摇摆,而现在框架逐步明朗,有了规则,也就没什么好害怕了。跨国旅行者需要面对的挑战是高于从前许多倍的时间成本,好在他并不缺时间。
他将自己的拉萨生活形容为一次对疫情的回避,那时他也处于一种轻微的迷茫。但是此刻面对分裂的世界和难以安放的由瘟疫生发的人类情绪,他觉得,处在时代中的作家应该选择面对。
聊天的最后我问他,以后你也会考虑去非洲吗?会考虑去南美吗?
他的回答很坚定,“会,会,一个一个都会去。”

《午夜降临前抵达》插图
“穿越波兰边境,进入塔特拉山,此地到处都是毛榉和冷杉。一个斯洛伐克人说,夜幕降临后,会有鹿群经过。”
这是他的出发之作《午夜降临前抵达》中被引用最广的一段文字,带着浓郁的亚寒带气息。脚步行至中亚,色彩由冷蓝转为枯黄。刘子超总是一个人背包行走在路上,包里是纸笔、相机与简单的换洗衣物,他说自己也是某种亚寒带人格,关于写作与出发,他告诉自己与世界,“保持耐心,享受孤独。”

全新编订版《午夜降临前抵达》现已由新经典文化出版









c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