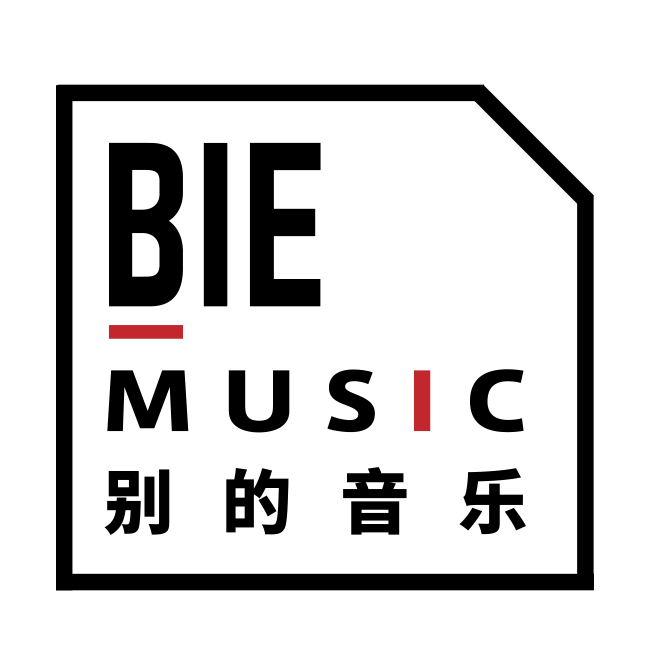打 2014 年底成立以来, “Boiled Hippo 煮河马” (后文,煮河马)这个 “三手” 名字就不时出没在北京各个场地的演出阵容中。当年主唱阿炳(abing)怀着对北京地下音乐氛围的向往从杭州搬到北京,之后就成了燥眠夜的常客。彼时的煮河马偏爱 post-punk 和 shoegaze ,深受 CAN 式的实验精神影响,属于北京后朋克乐队中的新生力量。2016 年前鼓手张云(现 “固体李逵” 鼓手)退出后,乐队一度中断活动,濒临解散。经历了成员变动和随之而来的停滞期,煮河马的音乐开始逐渐转向迷幻风格,和当时刚刚正式成立的 Space Fruity Records 一拍即合,2017 年在厂牌下发行了编号 SPR-01 的七寸黑胶。这部全长约 12 分钟的作品收录了《Mystery》和《River》两段“非正式录音”,略显潦草的即兴音频记录下了乐队整体风格从传统迷幻摇滚过渡到如今新迷幻音乐前的真实状态。吉他手 sd 弹起了贝斯,贝斯手张弓则 “客串” 了鼓手的角色,大篇幅的即兴和噪声氛围与成立之初的煮河马听起来截然不同。
煮河马的作品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似乎与阿炳的其他音乐计划相互呼应。无论是试图创造 “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般反叛糙砺质感的 “不在话下”,还是后来受到各类黑人音乐影响的 “睡狗”(Sleeping Dogs),无不在与各种音乐风格的固有局限唱着反调。随着新鼓手安迪的加入,煮河马的音乐开始更侧重于律动,在摇滚乐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胆的尝试,继续探索范式化摇滚框架之外的可能性。
煮河马即将在7月发行同名专辑《Boiled Hippo》,他们灵活多变的音乐实验也通过更加随意的创作方式和更加完整流畅的编排得到延续。最新发布的单曲《Fire》作为新专辑的先导单曲在保留迷幻氛围的同时弱化了传统迷幻摇滚带来的冲击力,在更绵长也更强调张弛有度的鼓点铺陈中,突出了贝斯、双吉他和人声声线的细腻质地以及音乐依托于旋律展开的内在叙事性。
Boiled Hippo - Fire
如今的煮河马显得比以往更从容,他们不断拥抱变化的进化姿态马上就可以在专辑中见分晓。我们提前和煮河马聊了聊,除了这张值得期待的新专辑,还有煮河马的 “前世今生”,阿炳和 Space Fruity Records 之间的缘分,以及同样在不断变化的北京独立音乐场景。
Q & A

左至右:吉他手 sd 、贝斯手 张弓 、鼓手 安迪、主唱/吉他手 abing
专辑中收录的都是近两年的新作品么?
abing: 基本上都是新作品,有两个歌会老一点。
张弓: 将近 4 年的吧,《Tower》是最早的,那个时候张云还在乐队的时候创作的,大概得是 2016 年初了。
从最开始的 “妄想的颜色” 到现在的煮河马,乐队的音乐有怎样的变化?
abing: 竟然还有人记得这个名字…… 变化挺大的,因为喜欢的东西也一直在变,以前更容易风格化吧,容易玩着玩着就掉进了某种风格的陷阱里,现在更随意点。
张弓:音乐风格从之前的后朋克、钉鞋的路子走出来了,曾经早些时候经历了一次解散边缘,后来被挽回了,想着大家一起玩点不一样的东西,于是就抛弃了之前后朋克钉鞋的路子。《Tower》应该就是那之后创作出来的第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里最早创作的歌了 —— 不过后来换了鼓手,跟最早的版本差别还是蛮大的。
成员上的变动有没有为乐队的创作带来新的变化?你会如何形容煮河马现在的音乐?
abing: 当然有,我们因为不同的原因更换过几次鼓手,鼓手的演奏很容易影响整个乐队的演奏。安迪的打法比较灵活,他加入之后我们的歌会偏向律动一些。
张弓:成员在变的一直是鼓手的角色,到如今经历了 5 任鼓手,其中我在没有鼓手的时候短暂的打了一小阵子鼓。对于煮河马这种在排练过程中创作的乐队来说,鼓手的变化基本上就是整个音乐风格的变化了。
专辑的创作以及录制过程中在听什么?
abing: Karl Hector & The Malcouns、CAN、Hailu Mergia。
张弓:创作周期很长,《Tower》算是最早的了,录制是 2019 年 8 月份,翻了下豆瓣,那个时候在听的是 King Gizzard & the Lizard Wizard 的 2019 年新专辑,就是那张激流金属。要是没这张专辑估计都不会回去重新去听金属乐,哈哈。
sd:那会在听 Dengue Fever,美国山寨的柬埔寨摇滚。其他原汁原味的东南亚迷幻也听了一些。
安迪:北村友香的游戏原声音乐。

“登革热” 乐队,2001 年成立于美国,主打 60、70 年代柬埔寨摇滚、流行乐风味
除了乐队的名字,煮河马的音乐有没有从文学或视觉类作品中获得启发?
abing: 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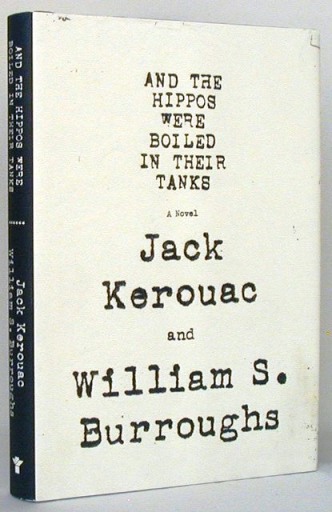
煮河马的名字来自威廉巴勒斯和凯鲁亚克合写的《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而书名据说来自威廉巴勒斯听到广播中主持人报道马戏团失火新闻时的大吼;这就是乐队名字被说 “三手” 的原因。
乐队的成员们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么?如何保证平时排练的时间?
abing: 有工作,我们都得工作养生活。安迪在做游戏,我和 sd 都是程序员,张弓在做医疗方面的产品。我们平时排练很少,一般都在周末,录音之前我们集中排练了一阵。
张弓:周末排一下,偶尔平时工作日晚上排一下,不过其实排练也不太好保证的,录音之后就暂停了。我这边换了工作并且生了娃,时间被压缩的很紧张。
阿炳的另一个音乐计划 Sleeping Dogs 的定位为 “不是摇滚乐队”。对你来说,与其他乐队的乐手一起创作不同风格的音乐是怎样一种体验?
abing: 能学到更多东西吧,毕竟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都不一样。而且我在 Sleeping Dogs 弹贝斯,之前一直是吉他手。弹贝斯能让我对节奏有很多新的理解。
在 XP 的燥眠夜时期有没有受到当时哪些乐队的影响?
abing: 乐队的话,那时候觉得 Alpine Decline、吹万、Run Run Run 很好。
当年在 XP 演出和后来在 fRUITYSPACE 或 SCHOOL 演出的氛围与体验有什么不同么?
abing: 这几个场地都不太一样啊,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偏好,所以人群也不一样。从演出感受上来说,去 fRUITYSPACE 演出的体验比较特别,因为有个随时投诉你的邻居和一堆马上要坏的设备,哈哈。
和 Space Fruity Records 是如何结缘的?2017年的 EP《Mystery/River》作为 Space Fruity Records 发行的第一张实体唱片,录制与发行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abing: 我应该是 16 年在“老 What”第一次见到翟哥,后来他邀请过我们演出,我也经常去水果店就熟悉了。17 年的那张 EP 说来挺逗,16 年我们前鼓手张云去了上海,我们进入了一个没得玩的阶段。我们偶尔会去排练室,贝斯手张弓打鼓,吉他手 sd 弹贝斯,然后录了一些很糙的录音,后来翟哥竟然觉得还不错,就发了出来。现在我是不会再翻回去听了哈哈。
张弓:就是某天下午三个人光膀子在排练室里的手机录音,被做成了黑胶唱片,听说还被送到纽约的一家店里去卖了。19 年初去了趟纽约,在 Printed Matter 还真的看到了这张唱片,觉得太假了。

《Mystery / River》是 Space Fruity Records 发行的第一张实体唱片(7" EP)
经常和煮河马一起演出的多数乐队成员都是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的乐手。煮河马作为相对较新的乐队有没有从他们身上受到什么启发?
abing: 我们都很喜欢 The Molds 和工工工。启发倒说不上,我们都不太一样,重要的是他们一直在玩吧。
近期有没有比较欣赏的年轻乐队?
abing: 2019 年能回想起来的新乐队的演出好像只有“阿部熏没有未来”和 BowAsWell。
据说海豚踢 (Dolphy Kick Bebop) 之前在 Space Fruity Records 发行磁带还是阿炳介绍的?两个乐队私下交集多么?
abing: 我是杭州人,和海豚踢的成员很早认识了,当时翟哥想多找一些乐队来做发行,我就想到了海豚踢和鸭听天。我很喜欢他们,那会儿很多北京的朋友也还不太了解这两支乐队,我就推荐给翟哥了。
现在杭州的音乐场景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过回到杭州或者去其他城市做音乐?在你看来,北京的音乐场景有什么独特之处?近几年这个场景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abing: 我现在对杭州的了解太少了…… 不过很明显浙江的很多乐队都进入了听众们的视野,感觉会比以前更热闹一些。回是回不去了,杭州的冬天太湿太冷了,我已经很习惯北京的天气了哈哈,而且现在也不会有为了做音乐去别的城市的冲动了,毕竟我的生活都在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觉得北京的音乐场景和天气挺像,干燥、粗糙、直接,而且玩什么的人都有,你总能找到点新鲜的。这几年种种原因,场地少了,办演出的成本和难度也越来越高,连排练室都少了。公共空间在缩小,参与者在减少,比较难形成一个个你所说的 “音乐场景” 了。
// 采访:Sandy
// 编辑:Ivan Hrozny

《Boiled Hippo》
编号:SPR-08
录制时间 : 2019 年 9 月
发行时间 : 2020 年 7 月 15 日
介质: 黑胶/CD/磁带/数字
出版 : 太空中果味(SpaceFruityRecords)
曲目:
01 Fire
02 Deep Water
03 Cold Memories
04 Golden Canyon
05 Shadow of My Day
06 Lost Men's Party
07 Tower
08 Future
打 2014 年底成立以来, “Boiled Hippo 煮河马” (后文,煮河马)这个 “三手” 名字就不时出没在北京各个场地的演出阵容中。当年主唱阿炳(abing)怀着对北京地下音乐氛围的向往从杭州搬到北京,之后就成了燥眠夜的常客。彼时的煮河马偏爱 post-punk 和 shoegaze ,深受 CAN 式的实验精神影响,属于北京后朋克乐队中的新生力量。2016 年前鼓手张云(现 “固体李逵” 鼓手)退出后,乐队一度中断活动,濒临解散。经历了成员变动和随之而来的停滞期,煮河马的音乐开始逐渐转向迷幻风格,和当时刚刚正式成立的 Space Fruity Records 一拍即合,2017 年在厂牌下发行了编号 SPR-01 的七寸黑胶。这部全长约 12 分钟的作品收录了《Mystery》和《River》两段“非正式录音”,略显潦草的即兴音频记录下了乐队整体风格从传统迷幻摇滚过渡到如今新迷幻音乐前的真实状态。吉他手 sd 弹起了贝斯,贝斯手张弓则 “客串” 了鼓手的角色,大篇幅的即兴和噪声氛围与成立之初的煮河马听起来截然不同。
煮河马的作品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似乎与阿炳的其他音乐计划相互呼应。无论是试图创造 “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般反叛糙砺质感的 “不在话下”,还是后来受到各类黑人音乐影响的 “睡狗”(Sleeping Dogs),无不在与各种音乐风格的固有局限唱着反调。随着新鼓手安迪的加入,煮河马的音乐开始更侧重于律动,在摇滚乐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胆的尝试,继续探索范式化摇滚框架之外的可能性。
煮河马即将在7月发行同名专辑《Boiled Hippo》,他们灵活多变的音乐实验也通过更加随意的创作方式和更加完整流畅的编排得到延续。最新发布的单曲《Fire》作为新专辑的先导单曲在保留迷幻氛围的同时弱化了传统迷幻摇滚带来的冲击力,在更绵长也更强调张弛有度的鼓点铺陈中,突出了贝斯、双吉他和人声声线的细腻质地以及音乐依托于旋律展开的内在叙事性。
Boiled Hippo - Fire
如今的煮河马显得比以往更从容,他们不断拥抱变化的进化姿态马上就可以在专辑中见分晓。我们提前和煮河马聊了聊,除了这张值得期待的新专辑,还有煮河马的 “前世今生”,阿炳和 Space Fruity Records 之间的缘分,以及同样在不断变化的北京独立音乐场景。
Q & A

左至右:吉他手 sd 、贝斯手 张弓 、鼓手 安迪、主唱/吉他手 abing
专辑中收录的都是近两年的新作品么?
abing: 基本上都是新作品,有两个歌会老一点。
张弓: 将近 4 年的吧,《Tower》是最早的,那个时候张云还在乐队的时候创作的,大概得是 2016 年初了。
从最开始的 “妄想的颜色” 到现在的煮河马,乐队的音乐有怎样的变化?
abing: 竟然还有人记得这个名字…… 变化挺大的,因为喜欢的东西也一直在变,以前更容易风格化吧,容易玩着玩着就掉进了某种风格的陷阱里,现在更随意点。
张弓:音乐风格从之前的后朋克、钉鞋的路子走出来了,曾经早些时候经历了一次解散边缘,后来被挽回了,想着大家一起玩点不一样的东西,于是就抛弃了之前后朋克钉鞋的路子。《Tower》应该就是那之后创作出来的第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里最早创作的歌了 —— 不过后来换了鼓手,跟最早的版本差别还是蛮大的。
成员上的变动有没有为乐队的创作带来新的变化?你会如何形容煮河马现在的音乐?
abing: 当然有,我们因为不同的原因更换过几次鼓手,鼓手的演奏很容易影响整个乐队的演奏。安迪的打法比较灵活,他加入之后我们的歌会偏向律动一些。
张弓:成员在变的一直是鼓手的角色,到如今经历了 5 任鼓手,其中我在没有鼓手的时候短暂的打了一小阵子鼓。对于煮河马这种在排练过程中创作的乐队来说,鼓手的变化基本上就是整个音乐风格的变化了。
专辑的创作以及录制过程中在听什么?
abing: Karl Hector & The Malcouns、CAN、Hailu Mergia。
张弓:创作周期很长,《Tower》算是最早的了,录制是 2019 年 8 月份,翻了下豆瓣,那个时候在听的是 King Gizzard & the Lizard Wizard 的 2019 年新专辑,就是那张激流金属。要是没这张专辑估计都不会回去重新去听金属乐,哈哈。
sd:那会在听 Dengue Fever,美国山寨的柬埔寨摇滚。其他原汁原味的东南亚迷幻也听了一些。
安迪:北村友香的游戏原声音乐。

“登革热” 乐队,2001 年成立于美国,主打 60、70 年代柬埔寨摇滚、流行乐风味
除了乐队的名字,煮河马的音乐有没有从文学或视觉类作品中获得启发?
abing: 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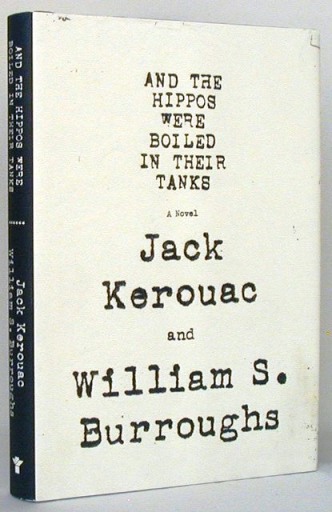
煮河马的名字来自威廉巴勒斯和凯鲁亚克合写的《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而书名据说来自威廉巴勒斯听到广播中主持人报道马戏团失火新闻时的大吼;这就是乐队名字被说 “三手” 的原因。
乐队的成员们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么?如何保证平时排练的时间?
abing: 有工作,我们都得工作养生活。安迪在做游戏,我和 sd 都是程序员,张弓在做医疗方面的产品。我们平时排练很少,一般都在周末,录音之前我们集中排练了一阵。
张弓:周末排一下,偶尔平时工作日晚上排一下,不过其实排练也不太好保证的,录音之后就暂停了。我这边换了工作并且生了娃,时间被压缩的很紧张。
阿炳的另一个音乐计划 Sleeping Dogs 的定位为 “不是摇滚乐队”。对你来说,与其他乐队的乐手一起创作不同风格的音乐是怎样一种体验?
abing: 能学到更多东西吧,毕竟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都不一样。而且我在 Sleeping Dogs 弹贝斯,之前一直是吉他手。弹贝斯能让我对节奏有很多新的理解。
在 XP 的燥眠夜时期有没有受到当时哪些乐队的影响?
abing: 乐队的话,那时候觉得 Alpine Decline、吹万、Run Run Run 很好。
当年在 XP 演出和后来在 fRUITYSPACE 或 SCHOOL 演出的氛围与体验有什么不同么?
abing: 这几个场地都不太一样啊,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偏好,所以人群也不一样。从演出感受上来说,去 fRUITYSPACE 演出的体验比较特别,因为有个随时投诉你的邻居和一堆马上要坏的设备,哈哈。
和 Space Fruity Records 是如何结缘的?2017年的 EP《Mystery/River》作为 Space Fruity Records 发行的第一张实体唱片,录制与发行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abing: 我应该是 16 年在“老 What”第一次见到翟哥,后来他邀请过我们演出,我也经常去水果店就熟悉了。17 年的那张 EP 说来挺逗,16 年我们前鼓手张云去了上海,我们进入了一个没得玩的阶段。我们偶尔会去排练室,贝斯手张弓打鼓,吉他手 sd 弹贝斯,然后录了一些很糙的录音,后来翟哥竟然觉得还不错,就发了出来。现在我是不会再翻回去听了哈哈。
张弓:就是某天下午三个人光膀子在排练室里的手机录音,被做成了黑胶唱片,听说还被送到纽约的一家店里去卖了。19 年初去了趟纽约,在 Printed Matter 还真的看到了这张唱片,觉得太假了。

《Mystery / River》是 Space Fruity Records 发行的第一张实体唱片(7" EP)
经常和煮河马一起演出的多数乐队成员都是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的乐手。煮河马作为相对较新的乐队有没有从他们身上受到什么启发?
abing: 我们都很喜欢 The Molds 和工工工。启发倒说不上,我们都不太一样,重要的是他们一直在玩吧。
近期有没有比较欣赏的年轻乐队?
abing: 2019 年能回想起来的新乐队的演出好像只有“阿部熏没有未来”和 BowAsWell。
据说海豚踢 (Dolphy Kick Bebop) 之前在 Space Fruity Records 发行磁带还是阿炳介绍的?两个乐队私下交集多么?
abing: 我是杭州人,和海豚踢的成员很早认识了,当时翟哥想多找一些乐队来做发行,我就想到了海豚踢和鸭听天。我很喜欢他们,那会儿很多北京的朋友也还不太了解这两支乐队,我就推荐给翟哥了。
现在杭州的音乐场景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过回到杭州或者去其他城市做音乐?在你看来,北京的音乐场景有什么独特之处?近几年这个场景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abing: 我现在对杭州的了解太少了…… 不过很明显浙江的很多乐队都进入了听众们的视野,感觉会比以前更热闹一些。回是回不去了,杭州的冬天太湿太冷了,我已经很习惯北京的天气了哈哈,而且现在也不会有为了做音乐去别的城市的冲动了,毕竟我的生活都在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觉得北京的音乐场景和天气挺像,干燥、粗糙、直接,而且玩什么的人都有,你总能找到点新鲜的。这几年种种原因,场地少了,办演出的成本和难度也越来越高,连排练室都少了。公共空间在缩小,参与者在减少,比较难形成一个个你所说的 “音乐场景” 了。
// 采访:Sandy
// 编辑:Ivan Hrozny

《Boiled Hippo》
编号:SPR-08
录制时间 : 2019 年 9 月
发行时间 : 2020 年 7 月 15 日
介质: 黑胶/CD/磁带/数字
出版 : 太空中果味(SpaceFruityRecords)
曲目:
01 Fire
02 Deep Water
03 Cold Memories
04 Golden Canyon
05 Shadow of My Day
06 Lost Men's Party
07 Tower
08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