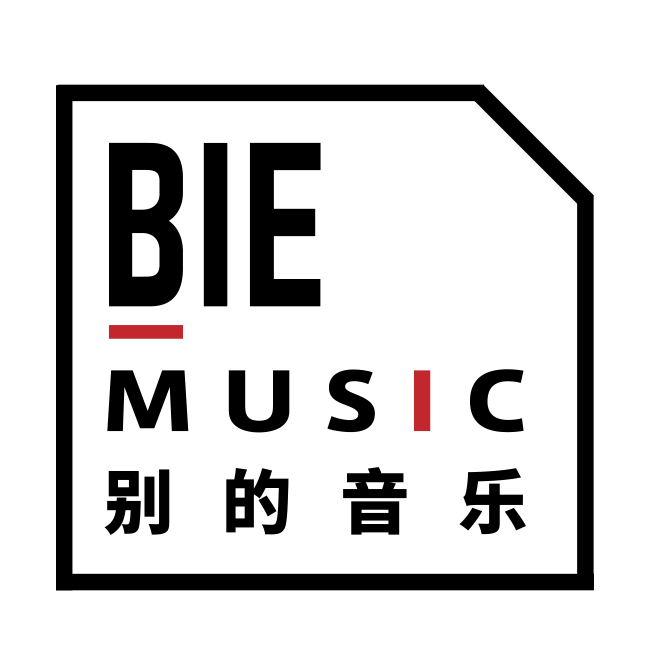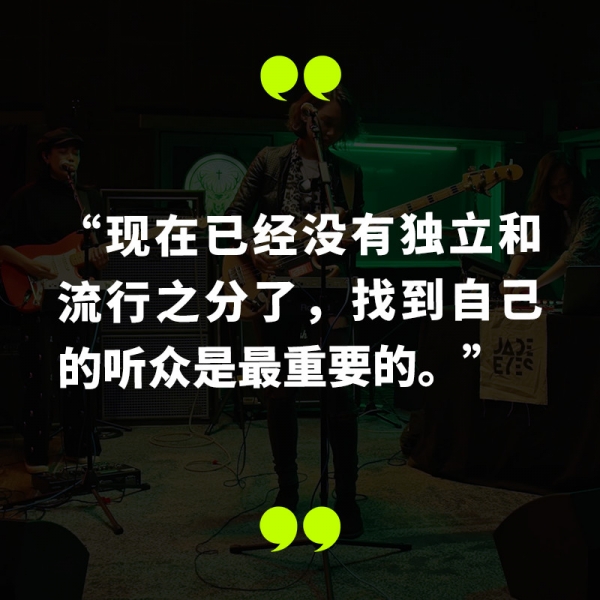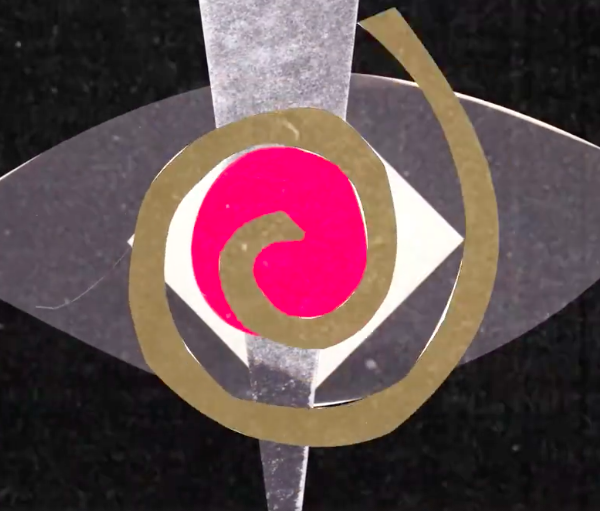2018年最让盯鞋迷兴奋的事,首当其冲是 Ride 来北京和上海演了两场,那是 Ride 的创始成员 Mark Gardener 第一次来中国。他在巡演城市短暂停留,看遍了城市景观,并没有满足他对中国的好奇和想象。
不到一年我们又相见了,不过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 Ride 的主唱和吉他手,而是制作人。他将为四支年轻乐队 —— 出海部、后来的岛屿、动物园钉子户、Pale Air —— 录制一张唱片合辑,此外,也将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进行三场小型个人巡演。我跟他泡了两天的录音棚,在工作的间隙随便聊了聊,发现他除了热爱韭菜鸡蛋馅饺子之外,他还爱吃片儿川。
制作人能为年轻乐队带来什么?
录音室在北京西三环一个小区居民楼的地下三层,旁边就是车库。走廊没灯,出海部的乐手们蹲在黑乎乎的走道里抽烟,只有烟头亮着。
他们有点累。前一天晚上录到半夜,Mark 的时差还没倒过来,按照伦敦时间在工作。大半夜把他送回酒店后,乐手们在录音棚沙发上将就了一宿,第二天早晨爬起来接着录。
四支都是国内摇滚乐队的新鲜血液,他们兴奋,紧张,也焦虑。Mark 觉得他们有点紧,“我希望他们能放松,并且享受其中”。好情绪是好音乐的催化剂,但所有的情绪都不失为创作的好材料,“他们能做出来好东西的,因为他们在乎。”
出海部的贝斯手是个姑娘,平常是个上班族,这天翘了班来录音,手机一直震动。她看了眼未读消息,“老板问我为什么没交方案。”她没回,把手机扔回沙发上,继续录一段贝斯。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回,Mark 此次中国之行的录音助理 Eric 说编得有些无聊。Mark 伸手在姑娘的琴弦上拨了起来,“我觉得前半段可以温柔些,后半段更加有律动感。”

Mark 演示了一段他理想中的 bassline
他不常 “干涉” 乐队的创作。国外制作人跟中国乐手之间因为对作品理解有矛盾,然后闹掰的事是有的,Snapline 那桩著名的 《Phenomena》 / 《Future Eyes》 “双张专辑”公案就是前车之鉴。但 Mark 觉得自己不会,他并不是个想要改变乐队创作思路的制作人。“你们开心我就快乐” —— 听起来好像有点儿不靠谱,但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表达得没那么明显而已。他指着墙上 The Beatles 的照片,“大家都喜欢 Beatles,但是没有 George Martin,Beatles 听起来也不会这么好。”
在 Ride 的乐队生涯之外,Mark 是一位混音师和制作人,十二年来他制作了80多首歌曲,也给很多乐队做了专辑。他对自己的制作水平很自信,出言不似平常般委婉:“大多数乐队听到我混的第一版就觉得非常满意了。”他会尝试理解乐手们在想什么,会做笔记,记下录制时的强弱处理,方便自己后期混音时能理解。对他来说,制作人的价值是如何让乐队的优势能更有光彩地呈现出来。
他尊重年轻乐队的音乐表达,“年轻人更敏感(sentimental),但成年人会关注到更大的话题”。他看着录音间隙在走廊里被烟雾围绕的年轻人们有些感慨,“我昨天问 Eric 年纪,他说他22岁,我比他的一倍还多。”他曾经也会因为进录音棚而紧张焦虑,常叼着烟;但年纪大了,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他会有更多的理解。
22岁的时候,他的 Ride 刚出了第二张全长专辑《Going Blank Again》。与同时期的乐队比起来,他们的吉他音色没有那种像刀划出来的尖锐 —— 他们正在逐渐构建起属于自己的风格。那时候的英国乐坛迫切地需要一些 “新东西”,很多不同的实验性元素都在乐手们的 jam 中产生。90年代初,英格兰的 shoegaze 场景猛然建立起来,作为重要参与者的 Ride 被打上了这标签,但当时他们对这词儿都有些摸不着头脑。“说实话,shoegaze,grunge,这些名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他说 Ride 其实特别简单,“四个年轻人在学校相遇,逃学一起做音乐”,声名大噪也是没想到的。他们签约 The Creation 厂牌,四个年轻人看起来风华正茂。但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都知道,Mark 出来单干,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置办起了自己的 Ox4 工作室。
吃着外卖送来的韭菜鸡蛋馅鸿毛饺子,蘸着醋,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现在崇尚素食主义,为了身体健康,也为了生态保护。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终于有些累了,小睡了一会儿,还打起了呼噜。
Ride 在2014年重组,他跟 Andy Bell“重修旧好”,这并不在他的预料范围之内。20年前 Ride 是 Mark Gardener 音乐生活的全部,但20年后,他有了自己音乐生涯,也有了家庭。“这些年我也跟很多乐队合作,我有了女儿,有我的伴侣。Ride 重组让我的生活再次繁忙了起来,但让我离开我的家庭挺难的。”

在 Mark 的个人巡演北京站,出海部是他的暖场乐队。上台前他们一起吃了个披萨
Ride 和工作室,哪个更重要?
离开了小区地下车库,第二天录音的乐队是后来的岛屿,录音棚是东四环的 Sync-Studio。棚时紧俏,下午还有别的安排,录制时间定在了早晨 6:00,年轻人们不出意外地赖了会儿床,开始得晚了些。
Eric —— 他也是缺省乐队的吉他手 —— 在跟乐手们商量怎么编比较 “得劲儿”,编了一会儿 Mark 来了,时差还是没倒过来,前一宿只睡了4小时。过了一遍目前录制的版本,他觉得长了。
这首8分多钟的迷幻摇滚叫《生零》,是乐手们练团的时候 jam 出来的。情绪的起承转合有,高潮的重金属叠加非常漂亮,但8分钟的时长还是导致整个节奏有些拖沓。“我觉得剪短一些会让这首歌更富于变化,在开头和结尾部分……”Mark 比划着。
Sync-Studio 的调音台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台 Solid State Logic,他在牛津的工作室里也有一台。他开始对着这台 SSL 滔滔不绝(即使昨天他已经在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轻松调频 DJ 方舟 的访谈中聊了好久他的 SSL),价格(包括二手价格),性能,甚至是哪些音乐人用它录制过唱片,他都能说出来,颇像沉迷音频工程技术无法自拔的装备党,“这个不论是录音还是混音都是最好的,产自牛津!”对家乡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末了还补充了句:“这是 Dr.Dre 的最爱。”

就是这台机器让他滔滔不绝
两年前他开始置办自己的工作室。他卖了一栋房子,还借了些贷款,工作室建在牛津的乡下,能看到流云的地方。他拿出手机来给我看工作室的照片,从沙发上的吊灯,到墙上的壁画,每一个物件他都能说上好一段儿来龙去脉,仿佛都是他的珍宝。
“Ride 和你的工作室,哪个对你更重要?”
他的回答虽比较委婉,但答案是显然的。
“两者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我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这是我的毕生所求。”
The Animalhouse 短暂的成立又解散后,他去法国跟 Molly's 呆了2年;后来又去印度呆了6个月,学了 hot yoga。不知道当年他离开英国的时候是否心灰意冷,但他笑着回来了。回来后他做了挺多专辑,虽然它们没有成为引起极大反响的“热门作品”,但这些造就了现在的他:没有迫切,让生活里的变动自然发生。“这一秒这样过去,下一秒发生的事情我无法估计。”
他没有期待过 Ride 的重组,但他说这确实是个“强大的团队”(原话是:Strong Unit)。今年 Ride 会发一张新专辑。目前已经发布的两支单曲 “Future Love”和“Repetition”跟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老乐迷有些不习惯。Mark 笑说现在会被更多产生在世界各地的新兴音乐吸引,“音乐得朝前看”。
说起给这四支中国新生乐队做的合集,他希望乐队的作品能带着他们自己“环游世界”。大制作人或者厂牌的影响力或许能帮助新乐队的作品被推广,但他觉得,当一个乐队的作品能牛逼到让大家觉得“噢这值得被更多人听到”的时候,事儿也就成了。这是 Mark 对这四支年轻的中国乐队的期待。
乐队录制进入了收尾阶段。他拿自己5岁小女儿 Nancy 的照片给我看,说小姑娘已经开始慢慢懂事,知道爸爸满世界飞是为了要给家里挣钱,毕竟工作室花了他几乎全部的积蓄。他笑说自己用音乐赚的每分钱最后都献给了音乐。Nancy 爱去他的工作室里玩,当小霸王,在他的工作室里“耀武扬威”地喊 “It's my studio!”
下午三点多,北京的录制顺利杀青。这位睡眠不足的男人说自己想下午去蒸个桑拿,然后好好睡一觉 —— 虽然北京的天气已经热得像蒸了好几轮桑拿。隔天飞上海,那儿还有两个年轻乐队等着他。
2018年最让盯鞋迷兴奋的事,首当其冲是 Ride 来北京和上海演了两场,那是 Ride 的创始成员 Mark Gardener 第一次来中国。他在巡演城市短暂停留,看遍了城市景观,并没有满足他对中国的好奇和想象。
不到一年我们又相见了,不过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 Ride 的主唱和吉他手,而是制作人。他将为四支年轻乐队 —— 出海部、后来的岛屿、动物园钉子户、Pale Air —— 录制一张唱片合辑,此外,也将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进行三场小型个人巡演。我跟他泡了两天的录音棚,在工作的间隙随便聊了聊,发现他除了热爱韭菜鸡蛋馅饺子之外,他还爱吃片儿川。
制作人能为年轻乐队带来什么?
录音室在北京西三环一个小区居民楼的地下三层,旁边就是车库。走廊没灯,出海部的乐手们蹲在黑乎乎的走道里抽烟,只有烟头亮着。
他们有点累。前一天晚上录到半夜,Mark 的时差还没倒过来,按照伦敦时间在工作。大半夜把他送回酒店后,乐手们在录音棚沙发上将就了一宿,第二天早晨爬起来接着录。
四支都是国内摇滚乐队的新鲜血液,他们兴奋,紧张,也焦虑。Mark 觉得他们有点紧,“我希望他们能放松,并且享受其中”。好情绪是好音乐的催化剂,但所有的情绪都不失为创作的好材料,“他们能做出来好东西的,因为他们在乎。”
出海部的贝斯手是个姑娘,平常是个上班族,这天翘了班来录音,手机一直震动。她看了眼未读消息,“老板问我为什么没交方案。”她没回,把手机扔回沙发上,继续录一段贝斯。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回,Mark 此次中国之行的录音助理 Eric 说编得有些无聊。Mark 伸手在姑娘的琴弦上拨了起来,“我觉得前半段可以温柔些,后半段更加有律动感。”

Mark 演示了一段他理想中的 bassline
他不常 “干涉” 乐队的创作。国外制作人跟中国乐手之间因为对作品理解有矛盾,然后闹掰的事是有的,Snapline 那桩著名的 《Phenomena》 / 《Future Eyes》 “双张专辑”公案就是前车之鉴。但 Mark 觉得自己不会,他并不是个想要改变乐队创作思路的制作人。“你们开心我就快乐” —— 听起来好像有点儿不靠谱,但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表达得没那么明显而已。他指着墙上 The Beatles 的照片,“大家都喜欢 Beatles,但是没有 George Martin,Beatles 听起来也不会这么好。”
在 Ride 的乐队生涯之外,Mark 是一位混音师和制作人,十二年来他制作了80多首歌曲,也给很多乐队做了专辑。他对自己的制作水平很自信,出言不似平常般委婉:“大多数乐队听到我混的第一版就觉得非常满意了。”他会尝试理解乐手们在想什么,会做笔记,记下录制时的强弱处理,方便自己后期混音时能理解。对他来说,制作人的价值是如何让乐队的优势能更有光彩地呈现出来。
他尊重年轻乐队的音乐表达,“年轻人更敏感(sentimental),但成年人会关注到更大的话题”。他看着录音间隙在走廊里被烟雾围绕的年轻人们有些感慨,“我昨天问 Eric 年纪,他说他22岁,我比他的一倍还多。”他曾经也会因为进录音棚而紧张焦虑,常叼着烟;但年纪大了,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他会有更多的理解。
22岁的时候,他的 Ride 刚出了第二张全长专辑《Going Blank Again》。与同时期的乐队比起来,他们的吉他音色没有那种像刀划出来的尖锐 —— 他们正在逐渐构建起属于自己的风格。那时候的英国乐坛迫切地需要一些 “新东西”,很多不同的实验性元素都在乐手们的 jam 中产生。90年代初,英格兰的 shoegaze 场景猛然建立起来,作为重要参与者的 Ride 被打上了这标签,但当时他们对这词儿都有些摸不着头脑。“说实话,shoegaze,grunge,这些名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他说 Ride 其实特别简单,“四个年轻人在学校相遇,逃学一起做音乐”,声名大噪也是没想到的。他们签约 The Creation 厂牌,四个年轻人看起来风华正茂。但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都知道,Mark 出来单干,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置办起了自己的 Ox4 工作室。
吃着外卖送来的韭菜鸡蛋馅鸿毛饺子,蘸着醋,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现在崇尚素食主义,为了身体健康,也为了生态保护。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终于有些累了,小睡了一会儿,还打起了呼噜。
Ride 在2014年重组,他跟 Andy Bell“重修旧好”,这并不在他的预料范围之内。20年前 Ride 是 Mark Gardener 音乐生活的全部,但20年后,他有了自己音乐生涯,也有了家庭。“这些年我也跟很多乐队合作,我有了女儿,有我的伴侣。Ride 重组让我的生活再次繁忙了起来,但让我离开我的家庭挺难的。”

在 Mark 的个人巡演北京站,出海部是他的暖场乐队。上台前他们一起吃了个披萨
Ride 和工作室,哪个更重要?
离开了小区地下车库,第二天录音的乐队是后来的岛屿,录音棚是东四环的 Sync-Studio。棚时紧俏,下午还有别的安排,录制时间定在了早晨 6:00,年轻人们不出意外地赖了会儿床,开始得晚了些。
Eric —— 他也是缺省乐队的吉他手 —— 在跟乐手们商量怎么编比较 “得劲儿”,编了一会儿 Mark 来了,时差还是没倒过来,前一宿只睡了4小时。过了一遍目前录制的版本,他觉得长了。
这首8分多钟的迷幻摇滚叫《生零》,是乐手们练团的时候 jam 出来的。情绪的起承转合有,高潮的重金属叠加非常漂亮,但8分钟的时长还是导致整个节奏有些拖沓。“我觉得剪短一些会让这首歌更富于变化,在开头和结尾部分……”Mark 比划着。
Sync-Studio 的调音台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台 Solid State Logic,他在牛津的工作室里也有一台。他开始对着这台 SSL 滔滔不绝(即使昨天他已经在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轻松调频 DJ 方舟 的访谈中聊了好久他的 SSL),价格(包括二手价格),性能,甚至是哪些音乐人用它录制过唱片,他都能说出来,颇像沉迷音频工程技术无法自拔的装备党,“这个不论是录音还是混音都是最好的,产自牛津!”对家乡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末了还补充了句:“这是 Dr.Dre 的最爱。”

就是这台机器让他滔滔不绝
两年前他开始置办自己的工作室。他卖了一栋房子,还借了些贷款,工作室建在牛津的乡下,能看到流云的地方。他拿出手机来给我看工作室的照片,从沙发上的吊灯,到墙上的壁画,每一个物件他都能说上好一段儿来龙去脉,仿佛都是他的珍宝。
“Ride 和你的工作室,哪个对你更重要?”
他的回答虽比较委婉,但答案是显然的。
“两者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我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这是我的毕生所求。”
The Animalhouse 短暂的成立又解散后,他去法国跟 Molly's 呆了2年;后来又去印度呆了6个月,学了 hot yoga。不知道当年他离开英国的时候是否心灰意冷,但他笑着回来了。回来后他做了挺多专辑,虽然它们没有成为引起极大反响的“热门作品”,但这些造就了现在的他:没有迫切,让生活里的变动自然发生。“这一秒这样过去,下一秒发生的事情我无法估计。”
他没有期待过 Ride 的重组,但他说这确实是个“强大的团队”(原话是:Strong Unit)。今年 Ride 会发一张新专辑。目前已经发布的两支单曲 “Future Love”和“Repetition”跟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老乐迷有些不习惯。Mark 笑说现在会被更多产生在世界各地的新兴音乐吸引,“音乐得朝前看”。
说起给这四支中国新生乐队做的合集,他希望乐队的作品能带着他们自己“环游世界”。大制作人或者厂牌的影响力或许能帮助新乐队的作品被推广,但他觉得,当一个乐队的作品能牛逼到让大家觉得“噢这值得被更多人听到”的时候,事儿也就成了。这是 Mark 对这四支年轻的中国乐队的期待。
乐队录制进入了收尾阶段。他拿自己5岁小女儿 Nancy 的照片给我看,说小姑娘已经开始慢慢懂事,知道爸爸满世界飞是为了要给家里挣钱,毕竟工作室花了他几乎全部的积蓄。他笑说自己用音乐赚的每分钱最后都献给了音乐。Nancy 爱去他的工作室里玩,当小霸王,在他的工作室里“耀武扬威”地喊 “It's my studio!”
下午三点多,北京的录制顺利杀青。这位睡眠不足的男人说自己想下午去蒸个桑拿,然后好好睡一觉 —— 虽然北京的天气已经热得像蒸了好几轮桑拿。隔天飞上海,那儿还有两个年轻乐队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