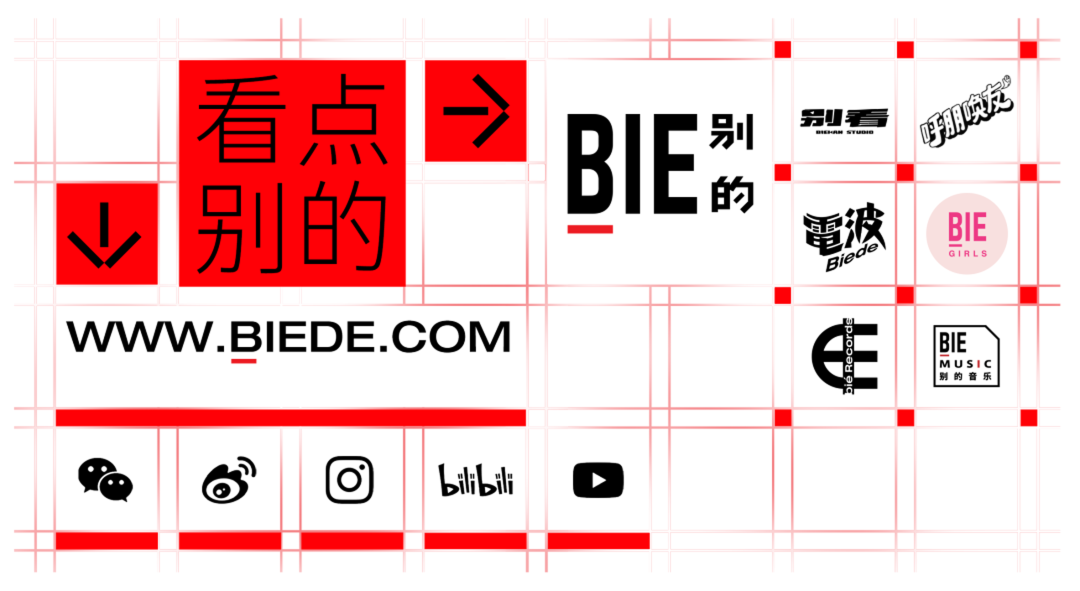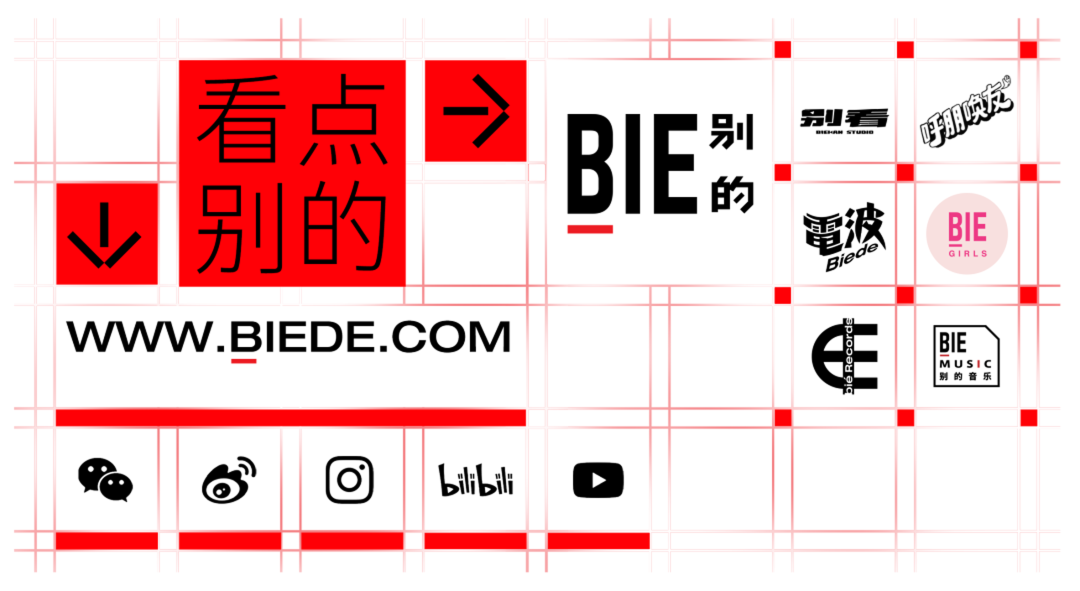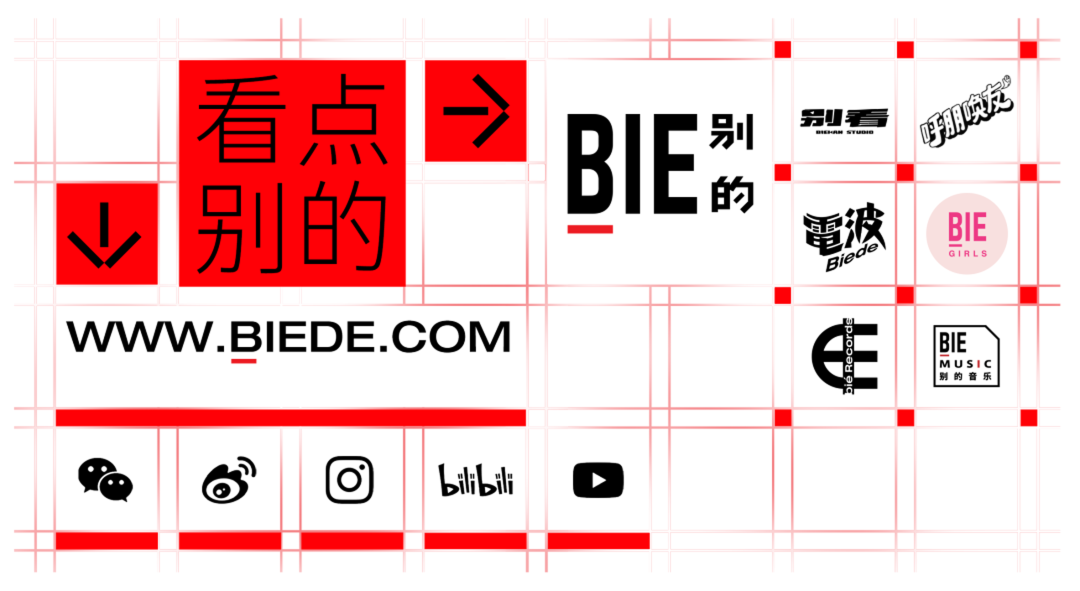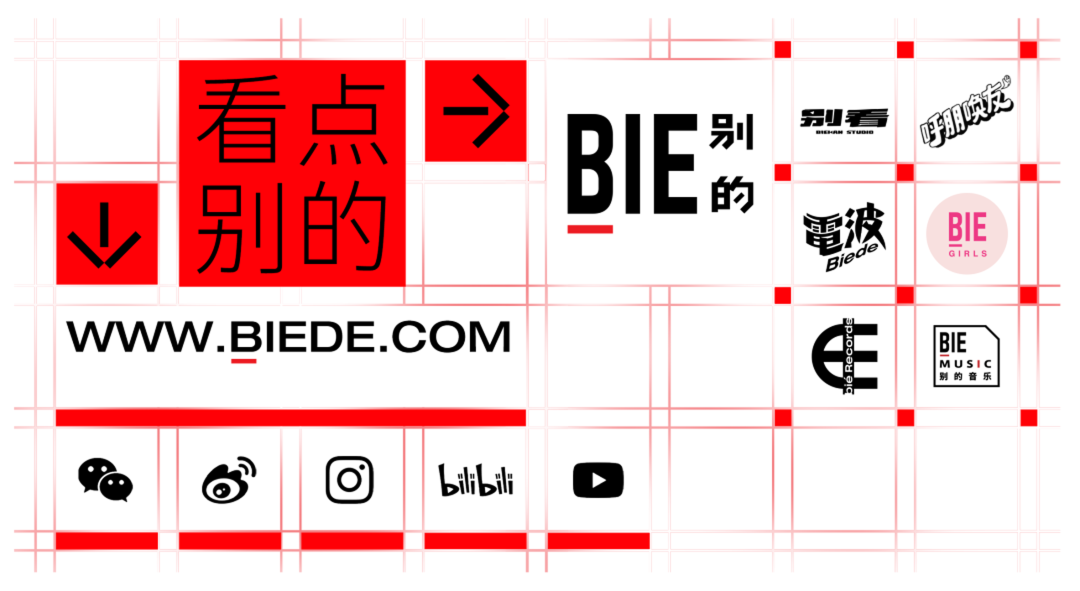BIE: 山羊皮在中国演出过很多次,可以分享你最印象深刻的一场吗?Mat: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在成都的演出。那天天气太糟糕了,雨一直下,一直下,演出看起来快要取消了,所有东西都泡在水里。而且我有个在学中文的侄女,四天前也来了。所以那天,整个乐队加上我侄女,我们在雨中开了几个小时的车,才到达演出现场,车差点进不去。雨水不停地从屋顶上哗啦啦流下来,我们还要打扫舞台上的水。但是,那些有点棘手的演出总是最棒的。歌迷们太好了,他们在雨中淋了一整天,拿着塑料布一样的东西盖在头上,又唱又跳。BIE: 我也经常参加那种音乐节,要记得带上雨衣。BIE: 山羊皮三十多年间经历了巅峰、低谷、起起伏伏,这些年你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吗?Mat: 天啊,这是个好问题。音乐行业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当我们刚成立时,一切都要看唱片,卖唱片能赚很多钱,现场演出会亏很多钱。后来我们解散了,再重组时,只过去了10年,一切都变了,没人再卖唱片了,突然间世界上冒出了一百万个音乐节。乐队必须多多考虑演出。一方面这对我们而言很艰难,因为卖唱片已经赚不到钱了。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全世界的人现在都听过我们乐队,因为你可以在Spotify、微博这样的地方了解到我们。想到突然间整个新一代的年轻人听过你们的音乐,真的很感动。我们去年还去了 “Xiami” 演出,一个离北京大约四个小时车程的度假胜地。Mat: 对,就是那里。我们想,演出是什么样的?应该没人认识山羊皮这个乐队吧?因为我们会和很多更年轻的乐队、中国乐队一起演出。然后我们登上了舞台,真的难以置信,那么多人都听过我们的歌,还跟着大合唱。作为音乐人,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尤其是当你在一个文化和语言不同的地方,人们依然能理解音乐中的情感,那是全世界最棒的感觉。虽然音乐行业已经改变了,但我的感受与31年前完全相同。站在舞台上,看到台下的人们跳舞、唱你的歌给你听,那种人与人的联结感非常美好,一点都没变。无论是在150人的酒吧,还是在70,000人的音乐节,一旦建立起了这种联系,我们就一直在一起。BIE: 谈到演出,我想起了三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在伦敦酒吧里的对话,我问他在哪里可以听到英伦摇滚,他很惊讶地说“你应该在1990年代遇到我。”他说在英国,英伦摇滚都是他们这些五六十岁的人听的。但在中国,仍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英摇。当我们聊到英伦摇滚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摇滚乐总是年轻的,是年轻人创作给年轻人听的。那么当你们演唱在二三十岁时创作的歌曲时,你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吗?你们在最近的专辑中加入了什么新的东西吗?Mat: 这是两个非常好的问题。比如《So Young》对很多中国歌迷来说意义重大,还有电影用它作配乐。当我们创作出这首歌、第一次唱的时候,我们还很年轻,现在我们已经不年轻了。但在这首歌的深处,它讲的是兴奋、激情,是人带着一种能量和愉悦进入这个世界。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你到了40岁、50岁而改变。这首歌虽然已经很老了,但它的内核并没有变,仍然能激发出我内心同样的亢奋。你还问到我们的创作方式有没有变化。其实 Brett 已经不再写什么年轻人去酒吧的事了。如果他还写那些东西,就有点离谱了。他现在经常聊家庭、聊做父亲的感受,比如成为父亲的恐惧,失去亲人的失落等等。如果你写的歌是蕴含真情实感的,那么它外部呈现出的样子并不重要,你要理解它的内核。我们去年发布了《She still leads me on》,是 Brett 写的关于母亲的歌,他母亲已经去世几十年了。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喜欢那首歌,原因各不相同。对他们而言,这首歌也可能是关于爱人、朋友或妻子的,但这些都不重要。在这首歌中,有爱、有失去,以及爱和失去的相融,大多数人都明白那种感觉。如果它打动了你,那就很好,这就是音乐的美妙。BIE: 没错。另外,当我们聊到山羊皮,第一印象经常是你们穿皮草和女式衬衫的照片,尤其是你和Brett。你们现在还喜欢这个造型吗?还是说那只是一种摇滚明星形象?Mat: 不不,其实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太穷了。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二手的。我们不会去设计师服装店买什么牌子货,我们都去那种二手店买。Mat: 那些衣服甚至都算不上古着吧。有人去世后,孩子们会把他们生前所有衣服都扔在那里,我们去的就是那种商店。所以我们基本就是穿着死人的衣服四处晃荡。我们喜欢打扮,如果那时候有点钱,我们可能会更聪明一些,买点漂亮衣服。但当时我们只是看起来像自己本来的样子 —— 没钱的年轻的工人阶级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