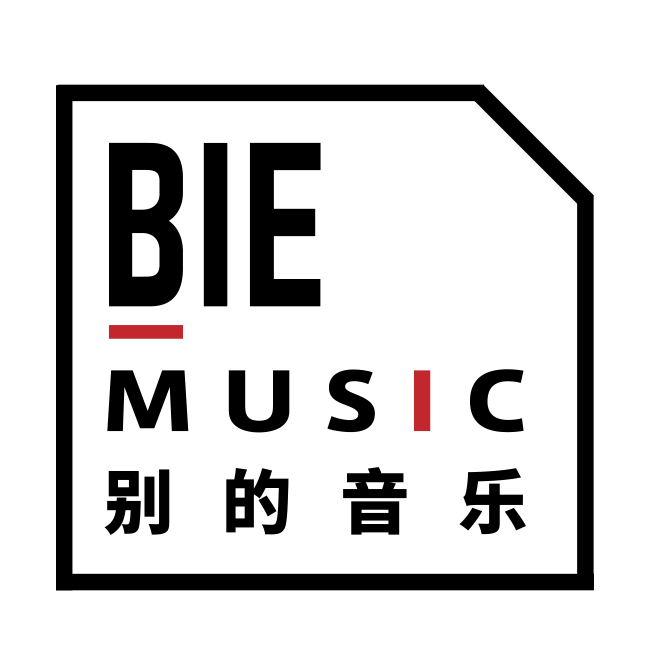我们把厂牌 2024 年首个发行的位置留给远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市的 numa gama,是因为她的思考将带每个人走得更广阔,也更深远。

MV: numa gama - Balloons (Logic)
巴西音乐人与中国厂牌的合作并不寻常。身处地球两端,中国和巴西,我们和 gama,自然有着很多差异——我们脚踏的土地,土地上附着的植被、楼宇甚至文明,似乎都有着不同颜色、气味和温度。我们体会不了巴西人从国家男子足球队处获得的愉悦,而巴西人也绝对参不透足球和股市怎么会是同一个难题;但是,主客之间的差异,恰恰是成全彼此的原点;当我们相互观察也回盼自己时,“幻象”脱颖而出,带着残存的现实肌理,为共情提供了可能。

摄影:@roma.romama
作为一位身体力行的跨媒介艺术家,gama 不光拥有着卓越的思想能力。她在做的,总是另辟蹊径,在“非规范”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时空中,进行一连串围绕“自我”和“幻象”的实验。身体化及概念化是她创作的并行方向;她抽象、幻化的对象,既是自己,也包括你、我的不同现实。而她创造的“幻象”,即身体、思想、表达方式和场景的集合,虽然复杂得难以解释,却像“痒”一样并不难感受——那是一种丰富而无法分门别类的体验,虽不完全来自某些相同的病灶和挣扎,却统一了不同人的渴望。这样的方式,让身在北京又或是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人们,都不难在错位中与 numa gama 的世界交叠。

numa gama 的第三张专辑,A Spectral Turn,即是这样的幻象。专辑的九首歌曲风格缤纷而协调,将听众带入一幅诡异的的声音景色:这是没人见过的冰冷亚热带世界,节奏缓慢燃烧,旋律线条错综复杂,天籁的声音同时掺杂着人与机械的特征。每首歌曲中,半透明的合成器音色浮游在抽象声响和故障音效之上,将一个个剪影持续晕染开来。gama 所造的幻象,弥合了所有人之间的不平等,糅合成一股理性的暖流,引领着听者穿越一道幽廊——错置其中的,是“过去的记忆” “当下的思想”以及“未来的破灭”。
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幽灵学”(Hauntology)以及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关于“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可能性的探究,是 gama 创造“幻象”的基础。
德里达的学说既是对“在场与缺席”(presence - absence)二分法的挑战,也是对“本体与主观性”(identity - subjectivity)的重新审视。历史不会终结,而只是化成“幽灵”;过去,作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总是影响并扰乱着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罗安清的研究主要以资本主义和受其影响的生态环境为背景,着重在“人与非人”(humans and non-humans)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揭示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和研究主体的关系时,她的观察体现了“非人类中心”(non-anthropocentric)视角的价值,同时为文明与生命在“资本主义末世”中构筑出潜在的、可持续的、更具社会公正的出路。
numa gama 在 A Spectral Turn 中编织的幻象,一幅声音的织锦,就这样穿梭在今天鬼魅般的末世景象中,探索着创造的自由与想象力的界限。为了召唤出这幅幻象,她有意将协商、改造社会环境的公共议题引入了个人创作欲望塑造的私密关系中,让两者呼应起来:numa gama 针对自己的人声进行重新设计,释放出了数字化的幽灵,并让这些幽灵游荡着,成为隐秘的缔造者,持续改造着我们的现实。

在第二首曲目 “Matter + Time” 中,她化身为赛博格,深入探索“后人类女性主义”(post-human feminism)的领域。在质地细密的环境音层和细微的 IDM 切分节奏中,gama 的歌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人与机器的混合态,以一种非线性的叙事方式,讲述着某个赛博格变性女人的曲折往事和她对获得平等与解放的憧憬。
在 A Spectral Turn 厚重主题的深处,“Cinza Verão” 和 “2k&Plateau” 这样的曲目,则唤起了寻求为环境大灾变复仇的幽灵。哀婉的旋律是濒危生态的挽歌,应和着受摧残的土地的呼喊。长长的延音震颤着,摆荡在无声和闪烁如鬼火的节奏两端。这些幻象中的幽灵,用无法消散的真实姿态,敦促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它们的消逝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接受它们的存在,意识到它们挥之不去的存在对于我们的意义,并由此接受系统性的变革,我们别无选择。
透过 A Spectral Turn 的幻象,我们得以对当下社会的肌理,以及寄宿于我们社会中的回忆性思想,展开法医取证式的调查。这不出于某种怀旧的情感,也并非在窥探未来,而是认清历史自身的目的和影响后,对历史的清算。Numa Gama 要让历史在每一个瞬间终结,好为“新的开始”让路,哪怕其中仍会有无数幽灵蜂拥而至。

摄影:@roma.rom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