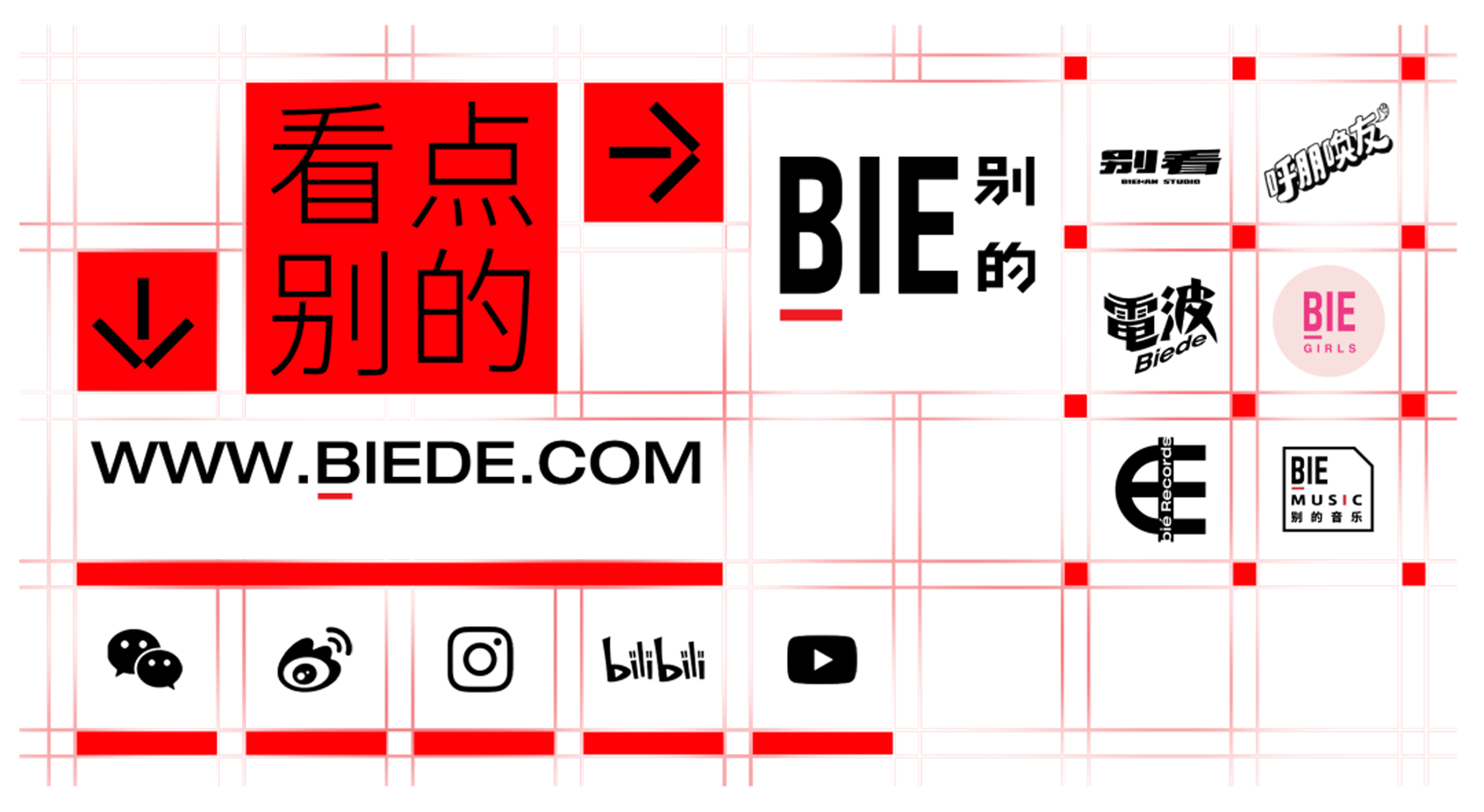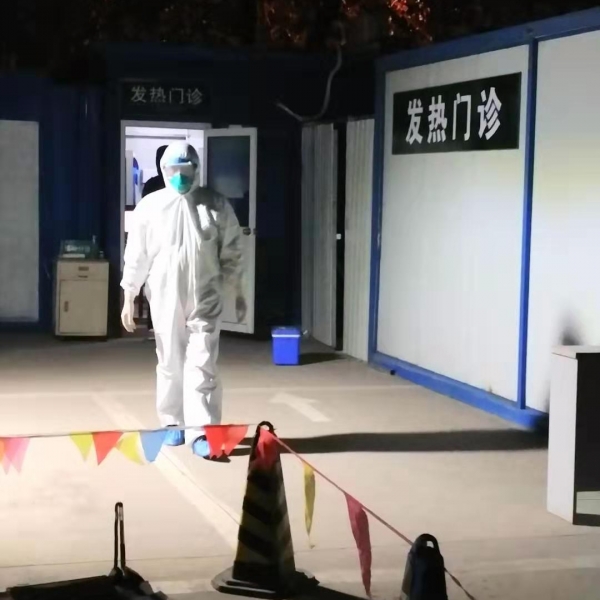新冠大流行下,在冬天的南方群居游牧的冲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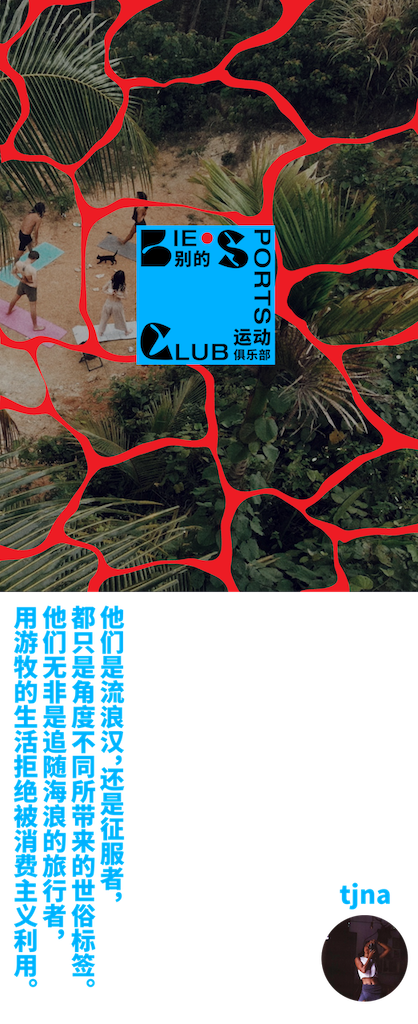
入冬了,随着北半球海水温度的下降,浪人们把冲浪板绑在车顶上,将已经洗到褪色变形的冲浪 T 恤换成长袖破洞帽衫,把厚湿衣塞入行囊,开始属于这个冬季的南下寻浪之旅。

2020 年,世界疫情大流行打断了我的间隔年。背包旅行回来后,我决定继续远离城市的生活,搬到惠州的海边去住。跟中国所有的海滨小城一样,这里只有在夏天的时候会有游客来往,平日,这里就是个睡眼惺忪的渔港小镇。年底,我和一起生活的浪人朋友们拍了第一部冲浪旅行纪录片《牧浪南巡》。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场乌托邦式的冲浪旅行。六个人凑齐几万块买了一辆大车,挤满所有人的行李和我们养的动物,车上绑着七八张冲浪板,所有的费用平摊。人生也难遇到几次这样的一拍即合。

《牧浪南巡》片段
"逐水草迁徙"是游牧生活的主要环节,没有哪一片草场的自然生态经得起长期放牧,因此当游牧民族天生就与移动性的生活相伴而行,因此换季之际,他们总会去下一个水草丰腴的地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总围绕着他们的牛羊,就像一个全身投入的浪人,生活节奏总是随浪况而变。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而居,冲浪人们所追求的“水草”,就是海浪。当十月冷空气开始南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迁徙,因为全年最好的浪在海南,我们一定要追到她。
所以我们给这场迁徙取了个这样的名字——“牧浪”。


浪人的“爱之夏”
.png)
我们也只是游牧浪人中的其中一群。很多浪人,其实都是第一次这么有仪式感地奔赴在去海南岛的路途。来自全国各地的浪人们,几乎都上路了,为的竟然是一个近乎形而上的目标:追寻海浪。大家还是头一次如此认真地去探索自己家乡几千公里的海岸线,享受平日常被忽略的海浪资源。
当世界在疯狂,大海依然保持着她的平静节奏。在大海中间,冲浪者必须抛开一切;在海里,任何的人类规则都只会大自然的力量被卷走,不值一提。不管世界如何纷扰,有了冲浪的世界,就是一个百毒不侵的世外桃源。
冲浪之后,人会开始对自由抱有更多的执着和幻想,最终你将变成一个更加浪漫的人。很多海边的浪人,其实都曾经过过在城市里打拼看不见远方的日子。爱上冲浪后,他们会不惜时间和金钱成本地来到海边度过每一个周末,最后甚至彻底“跳槽“成一名浪人。而这种自由,远远不仅是因为冲浪这项运动本身带给你的那种飞翔般的体感,更是因为冲浪本身所带有的文化属性。
不论是冲浪摇滚,冲浪电影、冲浪时尚还是那些知名的冲浪手和冲浪旅行故事,都传递着一样的反主流价值观,都是一扇扇打开你理解自由的窗口。这些图像、声音和口述所构建出来的冲浪世界乌托邦,实在太令人着迷了。每一个冲浪人,脑子里都会有过一个这样的自己——在一个无人浪好的小岛上面,每天用浪来填饱精神,用椰子来填饱肚子,不食人间烟火。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ead.”

Woodstock Traffic Jam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的大堵车。图片来源:Vintage Everyday
那首描绘 70 年代嬉皮们从美国各地涌向三藩市参加“爱之夏”的歌一直在我脑海里循环。
少年时期开始我就伴随着那个年代的摇滚乐和小说诗歌长大,这段牧浪旅程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中国的嬉皮士运动也要来了吗?那个 1967 年的夏天,有多达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名叫“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音乐会,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为“嬉皮士革命”,这些人们拒绝对现代主义和资本的顺从。

爱之夏音乐节。图片来源:Sutori

野蛮生长的嬉皮社群
.png)
在近半个月的旅途中,我们一路追着冷空气,风餐露宿在广东南岸的各个海滩上。到达琼州海峡的轮渡上时,我们还不太敢相信这场公路旅行就快到尾声了。
为了不用去租价格离谱的公寓,我们踏破铁鞋寻找合适的落脚地,期间一直扎营在当时仍是秘密浪点的南燕湾,继续风餐露宿的生活,来冲浪的朋友有时会给我们带些物资。12 月底的海南,晚上很冷,我们彻夜生火喝酒,听着日夜不息的海浪声。虽然连着好几天不能洗澡,但我当时觉得没有谁在海南比我们更幸福了,坐拥豪华一线海景和最好的海浪。
在西方冲浪,有个词叫做 Beach Bum(海滩流浪汉),用来形容成年呆在海边穷浪的人们。1950 年,美国知名月刊《LIFE MAGAZINE》第一次用了这个词。它提到了一群滑雪者,他们会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的雪地上度过冬天,然后在加州圣地亚哥度过夏天。他们在冬天是滑雪狂人,在夏天则是沙滩流浪汉。
“五月,太阳谷的雪一化,这些沙滩流浪汉(Beach Bum)们就开始向南迁徙。他们到父母家放下滑雪板,拿起他们鲜艳的 15 尺长的实木冲浪板,向海滩驱车而去。”杂志这样报道,“在海滩上,流浪汉们每时每刻都在冲浪、晒太阳、狂饮啤酒,和别的流浪汉们交朋友。他们在附近打工,做救生员、调酒师之类的工作,挣得钱只够填饱杯子、肚子和皮卡的油箱。”
至于他们是享乐主义的流浪汉,还是自然主义的征服者,都只是角度不同所带来的世俗标签。他们所做的,其实无非是心血来潮地旅行,带着新的海浪去发现,逃离消费主义的利用和现代生活的考验和磨难。
Beach Bum 的生活体验过后,这场心血来潮的梦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那就让它心血来潮到底吧。机缘巧合,我们无意间找到了一座地势略高的槟郎树农场。当大多数人都选择住在海景小区房里的时候,我们在闹市中找到了世外桃源。山坡上的风景,让我们第一次上山就不再想下来。
当我们给新的家园除草、修建、添置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时间下山去冲浪。我开始有点明白,这远不只是一场冲浪旅行,我们在做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实验。
不仅是冲浪的人,这一年的万宁,就像宇宙中心一样,它偏远又优美的热带海岛地理位置,让人想起泰国的帕岸岛、印尼的巴厘岛、菲律宾的锡亚高。疫情之下,有人开始形容海南是巴厘岛的平替。但其实每个海岛,都自然会聚集些喜欢游离在世俗生活之外的人们。
这里离热闹的地方很远,只要进了这条幽静的路的大铁门,上坡,就会来到一个只能听到鸟叫和牛鸣的地方。在这里呆一天,会有种“山中一日,人间一年”的感觉。
磁场相吸,我们“捡”回来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朋友。
Sasha 是一名来自波兰的旅行者,有一种典型的世界公民气质,和我在国外遇到的很多背包客有着相同的特征——一个背包,一头乱糟糟的长发,总是说不完的在世界各地流浪的故事。

波兰旅行者 Sasha
老胡是一位(知名)行为艺术家。平日里,他是一个喜欢打扑克和做饭的普通广东人。在日月湾的一个冲浪店,他突然认出我来,才意识到我们原来是多年前的故知,今年竟然在万宁重逢。

老胡
阿宗是我在 18 岁便因为摇滚乐现场认识的网友。曾在尼泊尔印度寻找修行的出口,今年的他来海南,第一次真正开始过上浪人生活。

阿宗
这里开始有我之前在尼泊尔、斯里兰卡、墨西哥等地呆过的“嬉皮社区”的味道了。这让我回到了前新冠世界,回到了我曾短暂停留过的那些社群。这个“槟郎山社区”,竟然是我们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没有名字,没有组织,没有规则,没有金钱交易,一切看起来都是“用爱发电”。有人每天为晚上的篝火砍柴,有人出钱买冰箱,有人做饭,有人买菜买粮食……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这个突然形成的社区做贡献。



50~70s 加州的公路旅行和背包客。图片来源:monterey herald

槟郎山的崩塌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