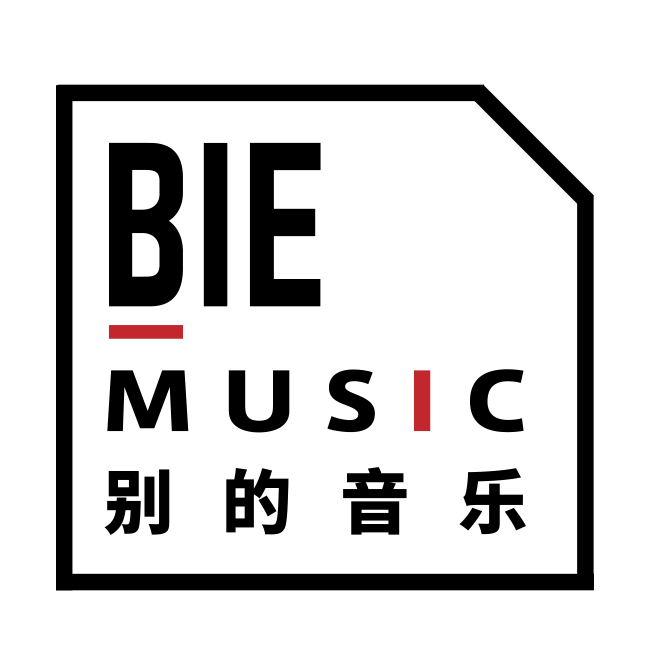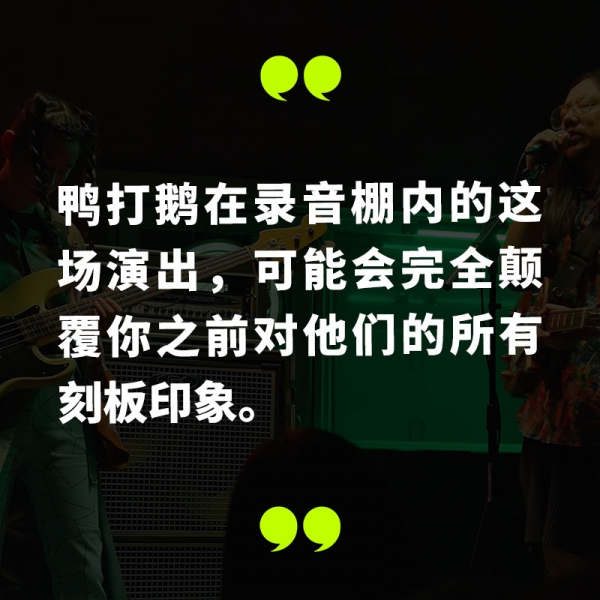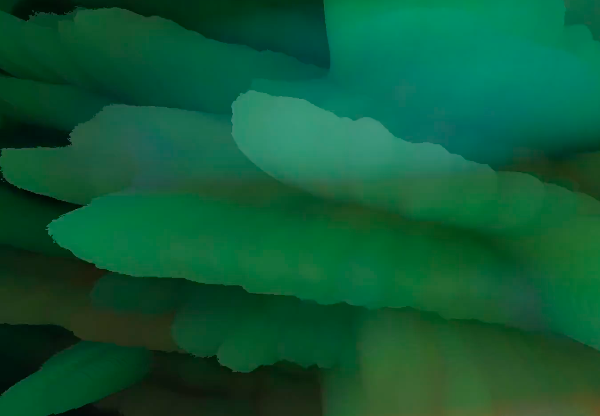Valentina Magaletti 近期巡演海报
5 月 27 日, bié Records 发行了打击乐手、多器乐演奏家 Valentina Magaletti 的全长专辑 A Queer Anthology of Drums。这张专辑是 Valentina 单人录制的即兴作品,诞生于一系列 “不为人知的失眠之夜”。如同把一块冰放在水里 —— 不需要歌声和语言,也无需强调任何策略 —— 一切的情绪、技巧,都融化在声波、频率与漫长的清醒梦里。


《A Queer Anthology of Drums 异鼓选》
黑胶唱片现货上架

Valentina Magaletti (以下简写为 M)
你在其他采访里提到过小时候听到 The Bangles 的 “Walk Like An Egyptian“ 的瞬间。那是你父母经常在家放的音乐类型吗?歌曲中的什么部分让你迷恋?
M:那个瞬间我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在电视上看到那首歌视频时的感受还记忆犹新:她们实在是太酷了!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曲调,而且鼓手棒极了!我的父母其实并不喜欢 The Bangles。
The Bangles - Walk Like an Egyptian
你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非常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职业鼓手,甚至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而搬到伦敦。对你来说,做这种 “人生选择” 或其他重大决定一直都这么容易吗?
VM: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总是知道做什么会让自己开心。在一个文化环境局促逼仄的地方(南意大利),想要给当全职音乐人的决定找合理的解释可一点都不容易。

Valentina Magaletti 伦敦家里的猫
你在录音、表演和采访中常常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做着那么多音乐项目,你现在还有时间教人打鼓吗?你是怎样在工作的重负下保持身心状态的?
M:因为经常出门在外,我现在没有很多时间教课了。我会尝试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活力;有时我也需要停下来休息几天,避免过度精疲力尽。
你教别人打鼓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教课会给你自己什么启发吗?
M:我在我伦敦的工作室教课。教学能让我保持自己打鼓技巧方面的训练,在平时我没什么时间练习。
你的课堂上男孩比女孩要多吗?有没有什么偏见会使女孩难以接触到架子鼓?
M:因为某些原因,我的学生全是女孩。我感觉男人害怕让女人做他们的老师。
你以前说过,Fugazi 乐队的打击乐编排有 “女性气质” “从来不是那么大男子气概的”,但同时你也指出过音乐是无性别的。这些讲法矛盾吗?
M:没有矛盾,性别概念与表现得 “女性化” “男性化” 无关。
这次专辑的标题点到了 “queer” 一词;你在专辑中的演奏也充满流动性,并且不太具备打击乐传统的 “阳刚” 刻板印象。你怎么定义这里的 “queer” 一词?
M:它代表的是 “包容的” 和 “不确定的”。
对于那些不熟悉非传统打击乐风格的听众,有没有什么建议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体验你的新专辑?
M:没有任何建议,仅仅需要把自己沉浸其中,然后聆听它。
你是怎么给即兴作品命名的?
M:没有一个具体的命名方式。命名实在取决于太多因素了。有时候我会受音乐本身启发,而另一些时候,音乐可能会引发一些特定的关联或情景。
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纯器乐的,写歌词或者唱歌对你来说会带来压力吗?
M:我不擅舞文弄墨。我更喜欢以频率和节奏的形式表达自己。
这次《异鼓选》的 bié Records 版本有一首之前没收录的曲目 “She/Her/Gone”。它和原来那几首是同一组即兴作品吗?为什么这首最初在 Takuroku 的数字版里没有收录?
M:这首歌的构思和录制晚于原来那些为 Cafe OTO 制作的曲目。它是在东伦敦的一个工作室录制的;而原来的那些是封城期间在我家录的。第一次封城的时候,我找了很多田野录音、还有在别处收集的声音混在一起。
对于你这样技艺精湛的音乐人而言,这张专辑的制作有什么挑战或困难吗?
M:我不认为这张专辑里有任何特殊的技巧,我只是用声波叙述我当时正在想的事情罢了。
制作专辑的过程是对你 “不为人知的失眠之夜” 的治疗吗?你认为音乐对制作者和听众来说算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吗?
M:我在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深受失眠困扰。我不认为做音乐帮我入眠,但它帮我外化了我内心的情绪。
佐杜洛夫斯基的电影曾让你在做 Vanishing Twin 乐队时收获一些灵感;你也想过制作塔罗牌 —— 神秘主义、神秘学、超现实主义对这张专辑,或者更广泛地说,对你的创作策略有什么影响?
VM:我没有任何策略。每天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能这点增强了我的创造力。我唯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做清醒梦。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我想去的地点......



佐杜洛夫斯基电影截图
你是如何进行即兴演奏的,有没有什么准备?
M:我会预先为鼓乐演奏准备大概的音乐框架,这能帮助我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专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经常不知道到底演了多久(大笑)!

Valentina Magaletti 的数字拼贴画作品
你收集画,自己也很喜欢画画。你觉得绘画与音乐的相通之处是什么?有没有试过给自己画封面?
M:有啊,我画过很多,比如 Vanishing Twin 的第一张封面就是我画的。

Vanishing Twin 的第一张专辑 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 封面
你也是个很知名的唱片收藏家。你听得最多的唱片是哪张?最珍贵的又是哪张?有没有哪张是你一直很想得到、但又没办法得到的?
M:有太多专辑我想要收藏黑胶的专辑了,要不我把我在 Discogs 上的 “想要” 清单发你吧。我一直都会听很多音乐,最近在听 Gaia Tones、Laila Sakini、Joanne Robertson、Kallist Kult ......


Valentina Magaletti 的部分唱片收藏
唱片之外,你还有哪些收藏?你提到过剪报、海报、照片、解剖学书、面具、现代艺术品……
M:我现在不在家,我会发给你的。


Valentina Magaletti 的部分收藏品
在你的生命中,你是否经历过完全与音乐无关、或者你不再思考关于音乐的事情的时刻?假如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某些原因,音乐不再是你的选择,你会去做什么?
VM: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太想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猜,我会感到被噤声,所以会去找另一种有效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现场演出中音乐人和观众之间的联结是很宝贵的,你表演的时候会关注舞台下在发生什么吗?如果会,观众的能量会影响你的表现吗?
VM:绝对会。对我来说一场演出全部的意义就在于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能量交流了。

Valentina Magaletti 演出
你对融入 “有传统元素” 的新音乐有什么看法么?对于传统的打击乐器 —— 比如意大利的 Triccaballacca*、中国大鼓、印尼甘美兰等等,你有未来运用它们的想法吗?
M:我不太熟悉 Triccaballacca,但我会试试看,每种打击乐器我都挺好奇的。
(*南意大利的传统打击乐器。)
什么样的音乐或者声音最让你着迷?
M:我没有一个最喜欢的类型,很难描述或者谈论这个......有人说“谈论音乐就像用舞蹈来表现建筑”,我非常赞成。
M:联系我们,我们会想办法让你成为一个鼓手的。最重要的是,现在就去行动!就是现在!

//采访、翻译:Ivan Hrozny、初夏
//编辑:Ivan Hroz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