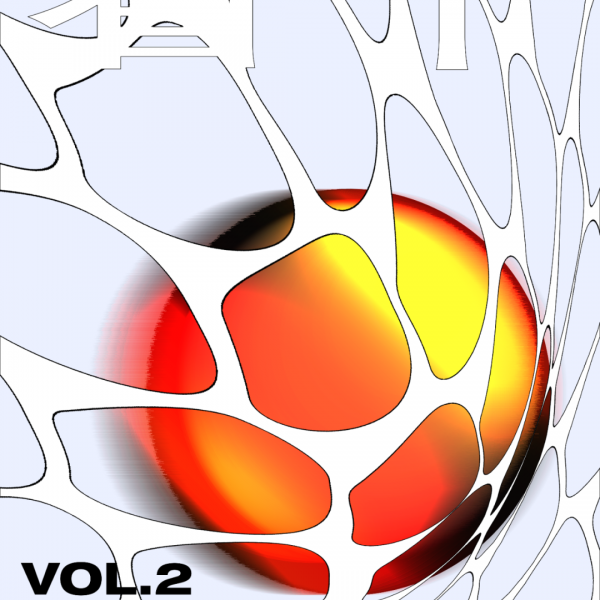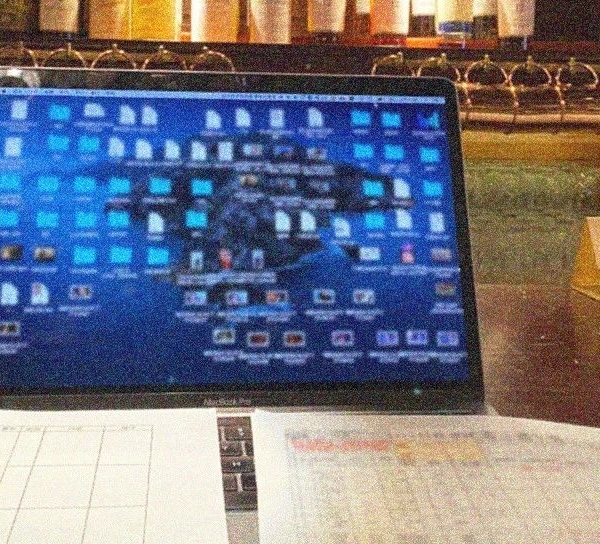当我们在平遥影展谈起 “电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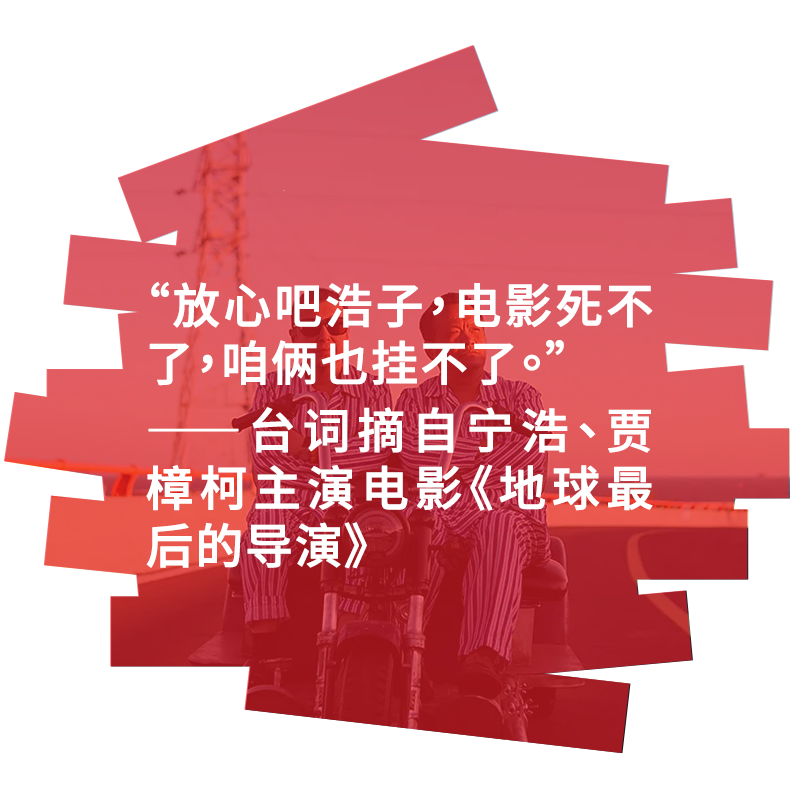


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 10 月 19 日闭幕。从平遥古城回来后没几天,我和一位同样从事影像创作的朋友聊天,聊到 “电影感” 这个词。
她说,真稀奇,我还以为只有广告导演的 treatment 和客户的 brief 里会出现“拍出电影感”,没想到圈外用词也开始在圈内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她说的倒也没错。在山西平遥电影宫的那几天,“电影感” 属实是我听到最多次的词汇。在无数次路过观众、粉丝、电影人和产业嘉宾,穿行在他们流溢出的只言片语中时,我时不时就会困惑地问自己,到底什么是 “电影感”?他们在谈论的 “电影感” 又是什么?
本着不懂就问的优良传统,我向身在平遥的各路人马抛出这一困惑。

“忘掉它是一个电影”
在藏龙单元入围影片《再见,乐园》的新闻发布会上,导演王尔卓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我之前拍过一个类似风格的短片,拍完那个短片的时候,有一些人喜欢,也有一些人不是很喜欢,不是很喜欢的观众会告诉我你这个片子没有电影感。有一天有一个我特别看重的老师,他告诉我他喜欢我的电影,我特别激动,那会儿我还是个学生,我不知道说这样一位我非常看重的、非常厉害的老师为什么喜欢我的电影,我就直接去问那位老师。我说老师,您为什么会觉得我这个电影好?那个老师说因为我喜欢你的电影感”。
发布会的前一天深夜是《再见,乐园》的中国首映,在此之前不久,影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斩获新浪潮大奖。那天,小城之春放映厅前聚满等待开场的观众,气温不足 10℃,排队的人们隔着口罩呼出白气。
《再见,乐园》是从平遥影展 WIP 单元走出去的作品,早在 2019 年第三届平遥影展上,王尔卓就已凭此获得发展中电影计划最佳导演奖,创作历经三年后,成片在 10 月 16 日经影展官宣,成为藏龙单元最后一部入围影片。影片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了导演的外婆、女友与母亲三代女性的故事,呈现一个家庭的精神历程与跨越七十年的时代变迁。
凌晨一点半放映结束后,观众口碑走向剧烈两极化。电影人木卫二发微博称“本届 PYIFF 终于出现了一部背对观众的电影”,影评人陆支羽称作品为“非常动人而丰盈的三女性独白”,而在豆瓣短评页面,大量观众将影片喻为“PPT 电影”“配乐影像诗朗诵”……
发布会上的王尔卓安静、专注,他对现场的媒体说,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因为这其实就是他想拍的。他也想明白了,“其实你看一个电影最好的方式,是忘掉它是一个电影。”在随后“深焦DeepFocus”的专访中他再次提到,影片中画面与声音的关系恰恰是他花费精力、希望使得影片与众不同的地方。回答口碑争议时他说,“不管是看电影还是做电影,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体验。
“这部电影里没有很多戏剧性的部分,也没有表演,完全是透过画面和声音、画面和画面之间的东西来讲电影。这是我所理解的真正的电影感。”

创投板块的青年制片人何旋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平遥,平遥元年时她是工作人员,去年她是创投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的最佳影片《深空》的制片,今年则成为电影创投项目的制片人。她今年带来的两个项目都有收获,《附近的星辰》获得平遥创投·科慕人文精神奖,《寺街》则拿下平遥创投·陌陌青云剧本奖,在 10 月 18 日奖项揭晓后,她在朋友圈中写道,“(这)是创作的胜利。”
古城里人变多了,这是她对今年电影节最直观的感受。十月初山西遭遇强降雨,许多古建筑面临损毁,平遥古城城墙也有一段坍塌,古城内的旅游业受到不小冲击。而随着电影节开幕,天气逐渐放晴,外来游客又随之回升了些,其中不少是今年 “青年评审荣誉” 评审团成员王俊凯的粉丝。她们蓬勃明媚,通常成群出现,电影宫里时常能望见她们的身影。
回答 “电影感” 之前,何旋向我回忆自己第一次来平遥时的情景,那时她的工作是接待电影主创,为他们安排行程,那几天她看了很多片子,《骑士》《方形》《村戏》还有开幕片《芳华》,她总觉得那会儿离圈子和创作者没那么近,但离电影非常近。后来情况开始逐渐倒置,纯粹作为观看者的愉悦少了,过程中会去在意作品的完成度、故事的空间和与自己项目的异同,全情投入的观看也少了。
今年在现场,何旋只有最后那天得空观看了一场电影,片子成功将她抽离出紧绷的九天,打动了她。“片子和观众的关系其实有时候挺随机的”,她告诉我,“电影感这个东西我没有清晰的定义,我觉得只要是放在电影院里不违和的,不会让我产生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看这个东西’ 的想法,各种创作就都可以被尊重。”
随后她又补充,“但我是蛮好奇当观众提出这个概念时,他的依照是哪里来的。比如他从前是看的第五代导演的片子?或是戛纳的片子?或是漫威?支撑他判断的电影感来源会是什么?”
这是一个需要自己与自己的历史相较才能回答的问题,又或者更具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是,当观众提出 “有没有电影感” 这个概念时,他的出发点是否定、取消还是讨论。“文艺片、作者片的起点是自我表达,当导演从自我表达开始时,你就不能阻止别人以自我感受去评判你。”至于观众是否是自我体验大于好奇心、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是否因此受到影响,那或许是另一个话题了。

当说出 “为了华语电影” 的时候
平遥影展是一个于我而言观影体验极度舒适的地方。园区设施集中,电影宫内各区安排得当,想要看电影时能沉浸在电影中,想要闲晃悠时也总能不经意撞见些新鲜见闻。纪念品商店门口的躺椅上,成排的人戴着墨镜晒太阳,仔细辨认一轮,会找到熟悉的编剧、资深导演和青年演员;买一杯咖啡的工夫你可能就会踩到一位同行,寒暄几句便算认识了,之后你俩加入躺晒大军,为某位导演的 QA 分享争论不休;晚上在古城吃饭,桌子上的人越吃越多,大家聊起刚放映结束的新片观感,分享几句八卦见闻和采访计划,端起盛满汾酒的小杯子,“来干杯,为了华语电影!”
这里有很多相遇。今年口碑爆棚的软科幻题材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导演孔大山分享,他与影片的编剧王一通是在第一届平遥影展上认识的,彼时王一通的作品《杀猪匠》在 WIP 单元拿下制作中电影发展荣誉,给前来参与 “平遥一角” 的孔大山留下深刻印象。2015 年孔大山的短片作品《法制未来时》曾网络爆红,片中文艺片导演“背对观众沉迷自我表达以致闷死人被抓”的桥段至今仍被人笑谈及引用。在同样以伪纪录片手法拍摄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可以看到糅合两人才情的诸多闪光处,反讽与解构有之,浪漫与深刻有之。正如片中 “民科怪人” 唐志军指着没有信号的砖头电视对镜头说,“这不是普通的电视雪花点,这是宇宙爆炸的余晖。”

《宇宙探索编辑部》在 “平遥之夜” 拿下 “迷影选择荣誉”、“青年评审荣誉影片”、“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怡宝·观众票选荣誉” 等诸多荣誉。监制王红卫在台上代导演致谢时,提到几年前送给学生孔大山一双印有 “开机” 和 “杀青” 的影展衍生品袜子,毫无准备的孔大山在现场掀起裤脚,那双袜子正好穿在他的脚上。
在电影宫的公开休息区,我偶遇了一个朋友小塔,她和另一个女孩小蛙趁着周末一起赶来平遥看电影,两人都是在校大学生。小塔向我分享了一段她与电影宫门厅保安大哥的对话,当她问及 “平遥一角” 里在放什么时,保安回答 “放的都是些短视频”。


隶属影展教育板块的 “平遥一角” 邀请高校影视艺术专业教师及学生代表,精选优质学生创作于平遥影展进行短片放映与交流活动
总是会有这样一些边界模糊的瞬间,比如保安大哥说着 “短视频” 而黑压压的放映厅内人们站立着爆发出掌声;比如《永安镇故事集》中反复出现的台词 “嗐,为了华语电影”,再比如扮演导演的刘洋与扮演编剧的康春雷相互嘶吼,然后怔怔地说 “马拉多纳去世了”,我们观看、沉浸、思考至批评,随后不自觉被拖入扮演。走出电影宫,小塔望见街上一个穿着大人风衣跑动的可爱小孩,一边打开相机一边说,“这一幕真像电影”。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里曾讨论 “女人作为被观看对象” 的命题,他写道,“女性将自己一分为二,不断注视自己。女性把内在于她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看作构成女性身份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截然不同的因素。男人重行动,女人重外观。女性内在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是女性,因此她把自己作为对象:景观。”
有那么几个微妙的瞬间,虽说缺乏类比和关联性,当我们聊及电影与电影感,这段话总会在颅内滚动起来,就像平遥夜空上的跑马灯。

最有电影感的时刻
“所以你觉得最有电影感的时刻出现在哪儿?”我问了现场几个人。
小塔向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对话发生在她从高铁站乘车来古城的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告诉她,山西洪灾其实离我们很近,刚刚路过的某个村里养了 129 头猪,洪灾发生,淹死了 110 头。
我拿这两个数字去找古城里的客栈老板打听,老板姓邓,他听完告诉我,的确有这件事,本地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就在电影宫两公里外,叫道虎壁村,百度搜索一下,那里的王氏妇科全国闻名。我于是搭车去到村里。





道虎壁村的地势处在水库下游,半个月前连续暴雨,水库开闸泄洪,村里玉米地被尽数淹没,泡过水的稀泥地无法下脚,原有的拖拉机等小型农械也无法使用,还没来得及收的玉米枯死在地里。稀泥将原有的菜畦搅拌得不辨形状,大葱、胡萝卜、红薯与白菜苗被泡进泥里,为避免次生传染病,地里的作物几乎全数报废。
罗大姐家里的水井被淹了,生活用水中断了两天,还好一旁的公路仍可通车,救援用水才能持续运来,雨停后,院内积水用汽油泵抽了三天三夜才抽尽;





村里的房屋多是平房,一楼积水的水渍至今仍在。史大姐家里的养鸡场房梁被雨水压歪,天花板上出现裂缝,两万多斤饲料被泡发霉,靠近地面的两层鸡栏被洪水漫过,六七百只母鸡被冲跑,我去走访时,地上仍有死掉的小鸡等待处理,母鸡们仍然处在惊吓状态,原本每天都满满当当的鸡蛋槽里只有寥寥几颗蛋。
它们的确发生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现实沉寂地待在热烈讨论现实主义的所在两公里开外,说不好是谁不在意谁。
带着满脚黄泥回到电影宫后,我观看了由科长与宁浩导演主演的《地球最后的导演》特别放映。影展曾在此前宣布,这部短片将在第二天进行慈善放映,每张活动票设置最低捐赠额 300 元,募集善款将全部用于支援山西平遥抗洪救灾。

《地球最后的导演》剧照
放映厅外二楼平台上,三个保洁阿姨快要下班了,她们靠在扶手上望着楼下的影厅出口,那里已被王俊凯的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都举起某块屏幕做眼睛,朝着同一个方向耐心等待着。一个阿姨正要回答我问题时,另一个阿姨猛拍她的肩膀,指着我们身后一扇不起眼的、正在晃动的小门惊叫出来:“王俊凯!他从侧门跑啦!”一两分钟光景,楼下的人群迅速向我们这个方向汇聚并朝着大门口奔涌而去,秩序井然,果真像水流一般。那阿姨举着手机美滋滋地说,“啊哈今天让我看到明星了,小伙子真帅,怪不得演电影呢,下班~”

我问路上遇到的某位粉丝她所体验到的电影感,她从相机里调出自己与大门立牌处王俊凯的合影,前景有一辆黑色商务车驶过,车内有模糊的侧影。她说,拍完看到成片,感觉像电影一样。
何旋的记忆里,电影感来自于她所观看的影片《当我们仰望天空时看见什么》的映后环节,导演亚历山大·科贝里泽和他在作品里表现出的一样地皮,坚持以一个空镜头 “出镜” 分享自己的创作体验。他就那样持续讲了几分钟,何旋盯着画面中间模糊的椅子,旁边的暖气片,感觉那窗帘隐隐在动,“他和他的片子一样,让我有一种很抽离、又挺感动的感觉。”
影展闭幕后,我联系上王尔卓,希望能与他聊聊片子与他频频提及的 “电影感”。递上大纲后过了许久,王尔卓说,决定暂时不接受媒体采访了。我问他,如果只是单纯聊聊在影展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呢?他说,我只想聊电影本身的问题。
《再见,乐园》最终获得 “费穆荣誉·特别表扬”,授奖词写道,“导演用独特且自洽的电影语言,带我们走入其内心深处敏感的私人领域。冷静克制之中,却饱含作者对日常生活深沉的爱意。影片整体呈现出的锐度,让我们重新思考家庭,思考生命,同样也思考电影作为情感载体的更多可能。”
临走时平遥再度阴天,回程的列车上时不时看见被水冲断的树木和淹没的旱田。国道上,村民们忙着将金黄麦子或谷子平铺在地,任行驶的车辆碾过脱壳。
我依然想不明白什么是 “电影感”,是某个视听语言标准?某种意在言外?某种集体创作下的公共性?于是又问了一个影展上碰到的媒体朋友,你的平遥体验里,最有电影感的时刻是在现实里还是在电影里?他很快就发来语音,“可能是在现实里吧,但具体我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