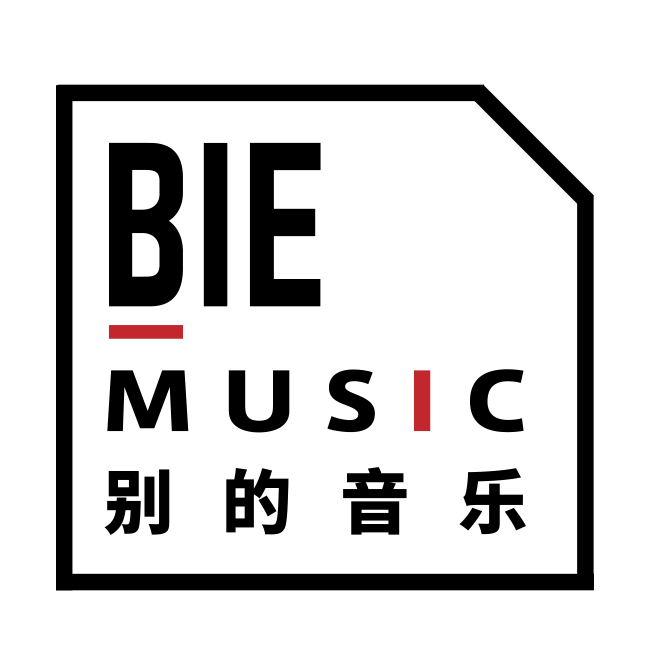下午五点,我来到米未传媒的办公室,去见正在为《乐队的夏天》试妆的刺猬乐队。这支成立于2005年的摇滚乐队走过了地下音乐的蓬勃年代,此次走上综艺节目也没丢失自己的攻击和侵略性。昨天第四期首播,他们把一首张杰的歌改编出了烟熏火燎的摇滚乐味道,之前的第三期,他们以最近一张专辑《生之响往》中的压轴金曲《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打动了许多观众。张亚东和高晓松在节目里评价,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仍有 “老摇滚” 的气质在:情绪化、有破坏性、满满的青春少年气。
来到试妆间的我终于第一次在台下见到了这三位终于在大众面前亮相的 “rock star”。抱着电脑的子健像个天天被吐槽的理工男,一个人蹲在那,光看见电脑上一堆码,黑底红字。他的确是个程序员,还曾以一己之力做过一个叫 “挖洞” 的社交平台 —— 给玩乐队的人和歌迷专门订制的社交网络,能发状态、能上传歌曲、互相关注、转发、评论,什么都行,功能齐全到不像是一个人的业余作品。
上了综艺节目之后,他辞了职,准备专心继续乐队的事儿。而鼓手石璐这时在一旁笑着和工作人员商量自己这身蛇皮夹克合不合适,贝斯手一帆弓着背打量,“能行”。我看着他俩,氛围挺像爸爸带着女儿逛商场的。
试妆结束后也到了饭点,纠结了一会,子健提议去一家名为 “大草原烤肉坊” 的饭店边吃边聊。“组导演推荐的,应该没跑儿。”
“甭理这帮人!”
“我那会儿是怎么天天跑北航排练的?真够远的。” 石璐回想起乐队刚成立的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真是劲头足。那个时候他们没签过公司,也不认识任何人,就带着这样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在 2006 年完成了第一张专辑《Happy Idle Kid》,后期混音和专辑封面打印全是 DIY。
不过 2006 年属于新裤子,《龙虎人丹》的新浪潮俘获了独立乐迷的耳朵,像刺猬这种不起眼的 “脏 grunge” 小乐队引不起什么风波,“那时候根本没我们什么事儿,还不是时候呢。” 子健说。直到后来一场致敬 Joy Division 的演出上,他们才遇见了哪吒、Snapline、Carsick Cars 这伙人,也就是后来的 “No Beijing” 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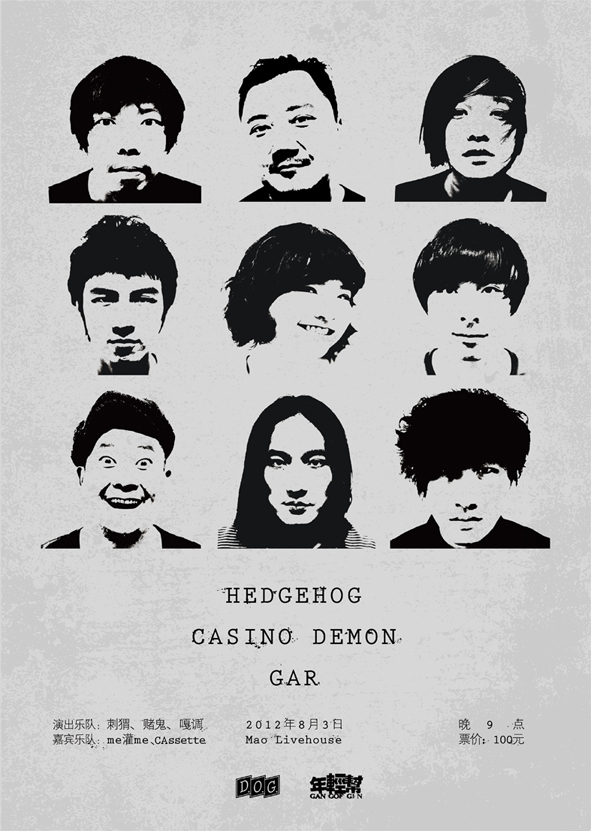
2012年刺猬在 MAO Livehouse 的演出海报
年轻灵魂的第一次碰撞总容易带有敌意,新裤子喜欢 Joy Division,这些人见面一开口也说自己喜欢,子健觉得这些人太装逼了。“甭理这帮人!” 子健跟她说。
Carsick Cars 和 Snapline 的成员李青回忆起那天,觉得石璐跟他们 “特不对付”。不过相似的人终归还是会凑在一起,那时他们有一堆乐手都住在连接北京安定门和德胜门的安德路一带,一帮人凑在 Golden Driver 乐队的吉他手杨子江家里,玩玩乐器,打打三国杀,又租下了安德路美廉美超市的地下仓库,改装成了这几支乐队合用的排练室,从 2010 年用到今年,直到两个月前才被迫离开。


2019年4月,孕育了 “No Beijing” 一代乐队的安德路排练室最后搬离前的样子。“那仓库全是尿味儿,子健还在里面放了床和冰箱。” 杨子江说。
那时候虽然穷,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反而年轻,“能量密度” 高,爱玩浪漫。石璐有一次在西单逛街,有个特喜欢的石头项链,不舍得买。都快忘了这事时,子健趁她不注意,从后面给石璐戴上了这条项链的时候,石璐哭了。
青春就这么回事,都差不多的纯真、狗血、折腾、悲伤,尽管每个人对同样的经历有着不同的解释,就像子健和石璐对他们曾经感情的淡然态度。那时作为情侣的两个人,受了周围乐队朋友的影响,做了一个和刺猬风格完全不同的乐队 “B-side Lovers”。这乐队只有他俩,但却更精确地表现出了他们情绪中负面的样子和自毁倾向。“B-side Lovers” 只短暂地存在了一阵,但你还能在豆瓣音乐人上找到他们仅存的两首歌 “Taxi Drivers” 和 “A Rock Way of Self-Destruction”。
北京奥运会前后,刺猬、后海大鲨鱼等另外几支乐队一起成为了匡威的中国代言,在商业品牌眼中,那些乐队是青年文化的中坚力量,代表着未来。以 D-22 酒吧为中心,整个场景已经呈现出一副让主流文化步步亦趋地服从与跟随的景象,最酷的孩子都听摇滚乐,80后一代朝气蓬勃。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场景不知不觉就消失了,快得像人们钱包鼓起来的速度。
就差了一点儿。现在的刺猬聊起曾经,觉得最巅峰的时刻也不能叫 “走起来了”,子健没因为他们最卖座的专辑《白日梦蓝》版权赚过一分钱,当时的 “蹿红” 也只是局限在一个属于北上广、外企白领与大学生的圈子里。“确实没红起来,当初要是真在大众面前红了,怎么现在坐地铁还没让人认出来?” 石璐笑说。
没杀死的摇滚明星
按 “出名要趁早” 的逻辑,已成立14年的刺猬年龄早已不合格。即使曾合拍,也总会走到打架的时候,2018 年他们就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石璐有了宝宝,乐队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日积月累地到了调和不了的地步。这样的极端条件下,石璐觉得实在没办法再和刺猬继续下去了,周围人再三劝阻,她依旧觉得 “没救”。“我录完新专辑就退”,与此同时,敏感的子健也因为失恋和身体原因状态很差,经常在微博上宣泄情绪,“鼓手撤了我也不玩儿了。”

眼看着刺猬就要死,贝斯手何一帆忍不住了。一帆向来话少,理性,性格也柔和,面对紧张状况时,却可以一针见血。临近散伙关头的一次巡演回去的航班上,一帆一屁股坐在石璐旁边,给她分析起了乐队聚散的利弊。
“给我画了一大饼。” 石璐这样形容一帆当时的劝阻,后又正经说:“他从来不会 ‘求’ 我,而是把好的坏的分析都扔给我,让我自己做决定。他的话能奏效,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时候她只是被感受蒙蔽了双眼,我需要做的就是将乐队这么多年来珍贵的东西再和她说一遍。” 一帆说起那时的策略。
乐队十几年的羁绊终于让他们没有说散就散,一帆的苦口婆心让石璐意识到,自己那些情绪还可以先放一放,让乐队继续下去才更重要。“如果撤了,再回来可能就十年以后了。十年都算短的,到时候谁知道什么样?你不可能说回就能回啊。” 石璐说。
如今的刺猬更像是经历磨难后的涅槃重生,生猛的三大件带着不被时光改变的少年感透过屏幕猛击你的耳膜。子健跟我说,在节目录制结束后乐队会发一张 mini 专辑,并进行新的一轮巡演 —— 谁说娱乐节目不能救摇滚乐?这不已经救起一个乐队了吗!
“这样的综艺早该有了”
说起《乐队的夏天》,很意外地,刺猬三个人都对这个节目赞赏有加。我问起乐队在录制期间是否有和节目组产生冲突的时候,一帆筷子停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真的没有。
乐队本身的个性就不允许权威来指指点点,也不可能见一个坐沙发戴胸牌的人就立刻鞠躬。这样一来,如何把这些不好伺候的人圈在一起并评个高低,的确是个难事儿。不过 “来都来了”,随着和团队交流的深入,刺猬也越录越上心,经常替节目组思考怎么才能把节目做得更好。
此前的米未显然不了解乐队文化,所以一开始刺猬没对他们期待太多,“工作认真负责就行了呗。” 但随着录制进行,他们发现包括马东在内的这些 “另一个圈儿” 的人很愿意了解乐队的事儿,都用心做了功课。尽管他们还是经常扔过来一些傻问题,不过 “不知者不怪,只要人家问了我们答了,就是一种正向传播”。节目组给每个乐队都安排一个跟组导演,石璐说自己一开始都 “懒得跟她聊天”,但节目拍到后来,石璐把任劳任怨又全情投入的跟组导演,当成了自己真正亲近的朋友。
不过令人不舒服的是,无论你本来准备怎么玩,只要进了场,就还是难逃综艺节目传播的规律。摇滚乐在当下,不仅和主流文化失去了联系,就连在亚文化中都愈见边缘,那种既凶猛又宽容、既激烈又自由的价值观如同史前遗物,被今天的人们视为怪兽。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的现场视频总转发量上万,但节目在歌曲前后呈现的石璐的单亲妈妈身份以及她与子健的前恋人关系,才成了观众对他们感兴趣的第一入口。对乐队来说,这种一地鸡毛式的八卦不会令人甘之如饴。石璐的态度淡然:“单亲妈妈的事让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坎,虽说不会完全释怀,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我挺感谢的,因为正是这些,才能让观众能看到如今这位更成熟顽强的鼓手。”
有些事既然发生了,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传播的 “物料”,大方说出来,反而能让大众接受她本来的样子。“反正我们不可能 ‘演’,也 ‘演’ 不了。摇滚乐最起码的态度就是面对自己。”

“总有人正年轻”
刺猬选择用《火车》做首次亮相,是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前情绪的最好写照。出过的八张专辑 ,每一张都代表了乐队走过的人生阶段,经过《噪音袭击世界》的躁动,《幻想波普星》的思考,如今的《生之响往》更像是他们三个人的视死如归。虽然子健曾经在 和 NOISEY 的对谈 里说过 “我觉得35岁就不会这么摇滚了”,但这张35岁前的专辑,仍然充满了刺猬式的硬派感伤。
“就当是铁窗泪吧!” 石璐说完大笑。
子健的情绪起伏经常会直接决定一张专辑的风格,写《生之响往》时,子健的状态特别不好,但正也是这种颓才逼出了《火车》这样在痛苦中甚至无法自洽的歌。杨子江说起和赵子健在2017年,他写《生之响往》时的一次相遇:“太丧了,我们在排练室碰到,他打了个招呼,就去自己排练室的床上躺着,喝啤酒,听 Nirvana —— 2017年啊,听 Nirvana。声音开特别大,我们排练的声都盖不住他放的歌。” “那时他说就住排练室的地下室,整个人的状态和梦游一样。”
在一起七年的前女友石璐形容子健是一个随时需要依靠的人,创造力极强,人却非常糙,时间一长,石璐觉得还是有点儿 “带不动了”,性格冲突让 “没头脑和不高兴” 的组合最终走向了生活上的解散。虽然如今她越来越不关心子健那些转瞬即逝的小情绪,但录音时看见《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的词,心还是狠狠揪了一下,不过,什么都没说。

刺猬已经不年轻了,他们对通过一档综艺再成名已经没有更多期待,不过《火车》那句词已经传遍大街,“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子健觉得,刺猬是有潜在商业价值的,“其实我们的旋律很能流行,大学生也喜欢,毕竟是从同一种挣扎里熬出来的。” 杨子江形容刺猬:“他们那种 ‘学生乐队’ 的气质一直都在,这也是子健的一种音乐天赋,他对于单音旋律的编排水平很少人能比得上。”
乐队需要的是个更大的平台,即使没有以前那样朝气蓬勃的独立音乐环境,但人们能因为娱乐带来的效应,对摇滚乐产生更大的兴趣和了解。虽然到最后也不一定和摇滚乐有什么真正的关系,但也许能挽救子健的经济状况 —— 这么多年过去,子健的经济状况依旧如同音乐一样青春。
采访结束,他看似轻松但蓄谋已久地抬头问了赤瞳音乐的工作人员:“这顿饭公司给报吗?” 饭钱报没报不知道,但第四期演完,刺猬乐队的微博爆了,张杰的粉丝大批赶来,质询赵子健节目里不屑的态度。可是谁在乎呢?他们没有搞懂,这里分明是另外一个世界啊。
下午五点,我来到米未传媒的办公室,去见正在为《乐队的夏天》试妆的刺猬乐队。这支成立于2005年的摇滚乐队走过了地下音乐的蓬勃年代,此次走上综艺节目也没丢失自己的攻击和侵略性。昨天第四期首播,他们把一首张杰的歌改编出了烟熏火燎的摇滚乐味道,之前的第三期,他们以最近一张专辑《生之响往》中的压轴金曲《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打动了许多观众。张亚东和高晓松在节目里评价,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仍有 “老摇滚” 的气质在:情绪化、有破坏性、满满的青春少年气。
来到试妆间的我终于第一次在台下见到了这三位终于在大众面前亮相的 “rock star”。抱着电脑的子健像个天天被吐槽的理工男,一个人蹲在那,光看见电脑上一堆码,黑底红字。他的确是个程序员,还曾以一己之力做过一个叫 “挖洞” 的社交平台 —— 给玩乐队的人和歌迷专门订制的社交网络,能发状态、能上传歌曲、互相关注、转发、评论,什么都行,功能齐全到不像是一个人的业余作品。
上了综艺节目之后,他辞了职,准备专心继续乐队的事儿。而鼓手石璐这时在一旁笑着和工作人员商量自己这身蛇皮夹克合不合适,贝斯手一帆弓着背打量,“能行”。我看着他俩,氛围挺像爸爸带着女儿逛商场的。
试妆结束后也到了饭点,纠结了一会,子健提议去一家名为 “大草原烤肉坊” 的饭店边吃边聊。“组导演推荐的,应该没跑儿。”
“甭理这帮人!”
“我那会儿是怎么天天跑北航排练的?真够远的。” 石璐回想起乐队刚成立的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真是劲头足。那个时候他们没签过公司,也不认识任何人,就带着这样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在 2006 年完成了第一张专辑《Happy Idle Kid》,后期混音和专辑封面打印全是 DIY。
不过 2006 年属于新裤子,《龙虎人丹》的新浪潮俘获了独立乐迷的耳朵,像刺猬这种不起眼的 “脏 grunge” 小乐队引不起什么风波,“那时候根本没我们什么事儿,还不是时候呢。” 子健说。直到后来一场致敬 Joy Division 的演出上,他们才遇见了哪吒、Snapline、Carsick Cars 这伙人,也就是后来的 “No Beijing” 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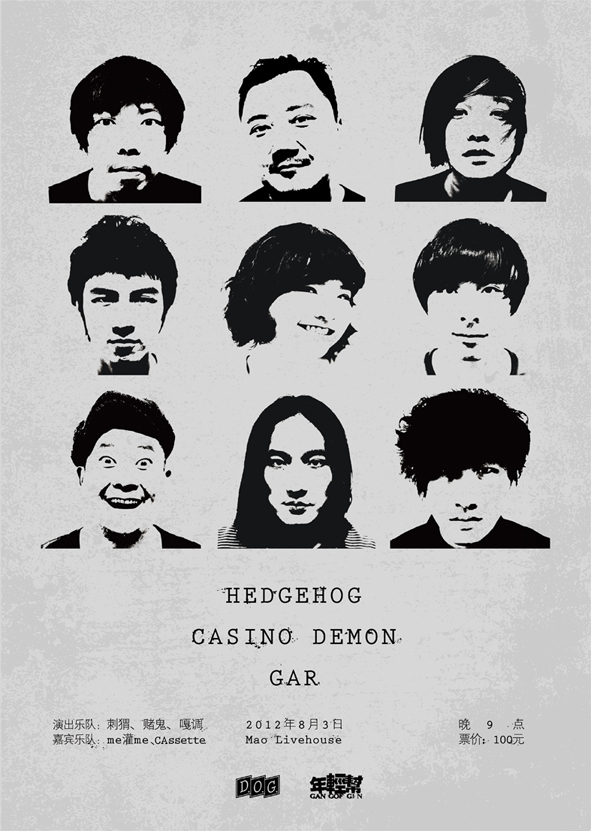
2012年刺猬在 MAO Livehouse 的演出海报
年轻灵魂的第一次碰撞总容易带有敌意,新裤子喜欢 Joy Division,这些人见面一开口也说自己喜欢,子健觉得这些人太装逼了。“甭理这帮人!” 子健跟她说。
Carsick Cars 和 Snapline 的成员李青回忆起那天,觉得石璐跟他们 “特不对付”。不过相似的人终归还是会凑在一起,那时他们有一堆乐手都住在连接北京安定门和德胜门的安德路一带,一帮人凑在 Golden Driver 乐队的吉他手杨子江家里,玩玩乐器,打打三国杀,又租下了安德路美廉美超市的地下仓库,改装成了这几支乐队合用的排练室,从 2010 年用到今年,直到两个月前才被迫离开。


2019年4月,孕育了 “No Beijing” 一代乐队的安德路排练室最后搬离前的样子。“那仓库全是尿味儿,子健还在里面放了床和冰箱。” 杨子江说。
那时候虽然穷,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反而年轻,“能量密度” 高,爱玩浪漫。石璐有一次在西单逛街,有个特喜欢的石头项链,不舍得买。都快忘了这事时,子健趁她不注意,从后面给石璐戴上了这条项链的时候,石璐哭了。
青春就这么回事,都差不多的纯真、狗血、折腾、悲伤,尽管每个人对同样的经历有着不同的解释,就像子健和石璐对他们曾经感情的淡然态度。那时作为情侣的两个人,受了周围乐队朋友的影响,做了一个和刺猬风格完全不同的乐队 “B-side Lovers”。这乐队只有他俩,但却更精确地表现出了他们情绪中负面的样子和自毁倾向。“B-side Lovers” 只短暂地存在了一阵,但你还能在豆瓣音乐人上找到他们仅存的两首歌 “Taxi Drivers” 和 “A Rock Way of Self-Destruction”。
北京奥运会前后,刺猬、后海大鲨鱼等另外几支乐队一起成为了匡威的中国代言,在商业品牌眼中,那些乐队是青年文化的中坚力量,代表着未来。以 D-22 酒吧为中心,整个场景已经呈现出一副让主流文化步步亦趋地服从与跟随的景象,最酷的孩子都听摇滚乐,80后一代朝气蓬勃。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场景不知不觉就消失了,快得像人们钱包鼓起来的速度。
就差了一点儿。现在的刺猬聊起曾经,觉得最巅峰的时刻也不能叫 “走起来了”,子健没因为他们最卖座的专辑《白日梦蓝》版权赚过一分钱,当时的 “蹿红” 也只是局限在一个属于北上广、外企白领与大学生的圈子里。“确实没红起来,当初要是真在大众面前红了,怎么现在坐地铁还没让人认出来?” 石璐笑说。
没杀死的摇滚明星
按 “出名要趁早” 的逻辑,已成立14年的刺猬年龄早已不合格。即使曾合拍,也总会走到打架的时候,2018 年他们就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石璐有了宝宝,乐队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日积月累地到了调和不了的地步。这样的极端条件下,石璐觉得实在没办法再和刺猬继续下去了,周围人再三劝阻,她依旧觉得 “没救”。“我录完新专辑就退”,与此同时,敏感的子健也因为失恋和身体原因状态很差,经常在微博上宣泄情绪,“鼓手撤了我也不玩儿了。”

眼看着刺猬就要死,贝斯手何一帆忍不住了。一帆向来话少,理性,性格也柔和,面对紧张状况时,却可以一针见血。临近散伙关头的一次巡演回去的航班上,一帆一屁股坐在石璐旁边,给她分析起了乐队聚散的利弊。
“给我画了一大饼。” 石璐这样形容一帆当时的劝阻,后又正经说:“他从来不会 ‘求’ 我,而是把好的坏的分析都扔给我,让我自己做决定。他的话能奏效,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时候她只是被感受蒙蔽了双眼,我需要做的就是将乐队这么多年来珍贵的东西再和她说一遍。” 一帆说起那时的策略。
乐队十几年的羁绊终于让他们没有说散就散,一帆的苦口婆心让石璐意识到,自己那些情绪还可以先放一放,让乐队继续下去才更重要。“如果撤了,再回来可能就十年以后了。十年都算短的,到时候谁知道什么样?你不可能说回就能回啊。” 石璐说。
如今的刺猬更像是经历磨难后的涅槃重生,生猛的三大件带着不被时光改变的少年感透过屏幕猛击你的耳膜。子健跟我说,在节目录制结束后乐队会发一张 mini 专辑,并进行新的一轮巡演 —— 谁说娱乐节目不能救摇滚乐?这不已经救起一个乐队了吗!
“这样的综艺早该有了”
说起《乐队的夏天》,很意外地,刺猬三个人都对这个节目赞赏有加。我问起乐队在录制期间是否有和节目组产生冲突的时候,一帆筷子停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真的没有。
乐队本身的个性就不允许权威来指指点点,也不可能见一个坐沙发戴胸牌的人就立刻鞠躬。这样一来,如何把这些不好伺候的人圈在一起并评个高低,的确是个难事儿。不过 “来都来了”,随着和团队交流的深入,刺猬也越录越上心,经常替节目组思考怎么才能把节目做得更好。
此前的米未显然不了解乐队文化,所以一开始刺猬没对他们期待太多,“工作认真负责就行了呗。” 但随着录制进行,他们发现包括马东在内的这些 “另一个圈儿” 的人很愿意了解乐队的事儿,都用心做了功课。尽管他们还是经常扔过来一些傻问题,不过 “不知者不怪,只要人家问了我们答了,就是一种正向传播”。节目组给每个乐队都安排一个跟组导演,石璐说自己一开始都 “懒得跟她聊天”,但节目拍到后来,石璐把任劳任怨又全情投入的跟组导演,当成了自己真正亲近的朋友。
不过令人不舒服的是,无论你本来准备怎么玩,只要进了场,就还是难逃综艺节目传播的规律。摇滚乐在当下,不仅和主流文化失去了联系,就连在亚文化中都愈见边缘,那种既凶猛又宽容、既激烈又自由的价值观如同史前遗物,被今天的人们视为怪兽。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的现场视频总转发量上万,但节目在歌曲前后呈现的石璐的单亲妈妈身份以及她与子健的前恋人关系,才成了观众对他们感兴趣的第一入口。对乐队来说,这种一地鸡毛式的八卦不会令人甘之如饴。石璐的态度淡然:“单亲妈妈的事让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坎,虽说不会完全释怀,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我挺感谢的,因为正是这些,才能让观众能看到如今这位更成熟顽强的鼓手。”
有些事既然发生了,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传播的 “物料”,大方说出来,反而能让大众接受她本来的样子。“反正我们不可能 ‘演’,也 ‘演’ 不了。摇滚乐最起码的态度就是面对自己。”

“总有人正年轻”
刺猬选择用《火车》做首次亮相,是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前情绪的最好写照。出过的八张专辑 ,每一张都代表了乐队走过的人生阶段,经过《噪音袭击世界》的躁动,《幻想波普星》的思考,如今的《生之响往》更像是他们三个人的视死如归。虽然子健曾经在 和 NOISEY 的对谈 里说过 “我觉得35岁就不会这么摇滚了”,但这张35岁前的专辑,仍然充满了刺猬式的硬派感伤。
“就当是铁窗泪吧!” 石璐说完大笑。
子健的情绪起伏经常会直接决定一张专辑的风格,写《生之响往》时,子健的状态特别不好,但正也是这种颓才逼出了《火车》这样在痛苦中甚至无法自洽的歌。杨子江说起和赵子健在2017年,他写《生之响往》时的一次相遇:“太丧了,我们在排练室碰到,他打了个招呼,就去自己排练室的床上躺着,喝啤酒,听 Nirvana —— 2017年啊,听 Nirvana。声音开特别大,我们排练的声都盖不住他放的歌。” “那时他说就住排练室的地下室,整个人的状态和梦游一样。”
在一起七年的前女友石璐形容子健是一个随时需要依靠的人,创造力极强,人却非常糙,时间一长,石璐觉得还是有点儿 “带不动了”,性格冲突让 “没头脑和不高兴” 的组合最终走向了生活上的解散。虽然如今她越来越不关心子健那些转瞬即逝的小情绪,但录音时看见《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的词,心还是狠狠揪了一下,不过,什么都没说。

刺猬已经不年轻了,他们对通过一档综艺再成名已经没有更多期待,不过《火车》那句词已经传遍大街,“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子健觉得,刺猬是有潜在商业价值的,“其实我们的旋律很能流行,大学生也喜欢,毕竟是从同一种挣扎里熬出来的。” 杨子江形容刺猬:“他们那种 ‘学生乐队’ 的气质一直都在,这也是子健的一种音乐天赋,他对于单音旋律的编排水平很少人能比得上。”
乐队需要的是个更大的平台,即使没有以前那样朝气蓬勃的独立音乐环境,但人们能因为娱乐带来的效应,对摇滚乐产生更大的兴趣和了解。虽然到最后也不一定和摇滚乐有什么真正的关系,但也许能挽救子健的经济状况 —— 这么多年过去,子健的经济状况依旧如同音乐一样青春。
采访结束,他看似轻松但蓄谋已久地抬头问了赤瞳音乐的工作人员:“这顿饭公司给报吗?” 饭钱报没报不知道,但第四期演完,刺猬乐队的微博爆了,张杰的粉丝大批赶来,质询赵子健节目里不屑的态度。可是谁在乎呢?他们没有搞懂,这里分明是另外一个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