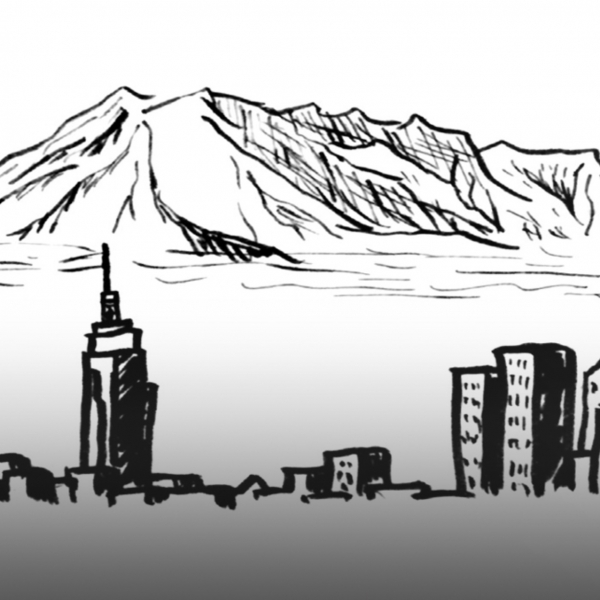重生之我不要再做 “迁徙式小镇做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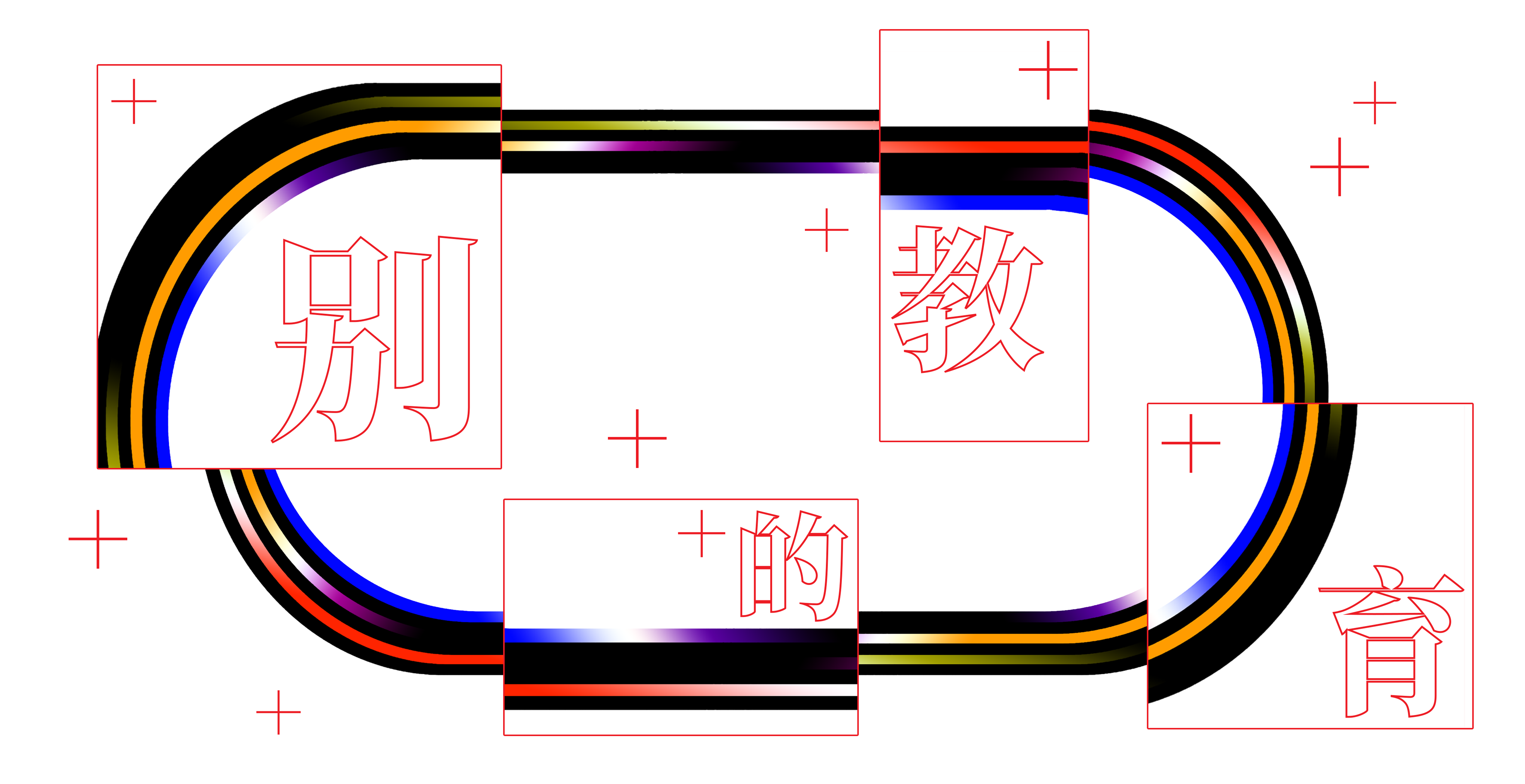
欢迎来到本周专题“别的教育”。在你所知的教育方式之外,讲讲我们如何试图学习这个复杂的世界。在本周的专题里,我们采访了一个体验了武校生活的女生,在国内上网课的留学生们,在多城市迁徙转校生活中长大的年轻人,一所新式教育的学校,以及教师子女们。祝大家新学期开学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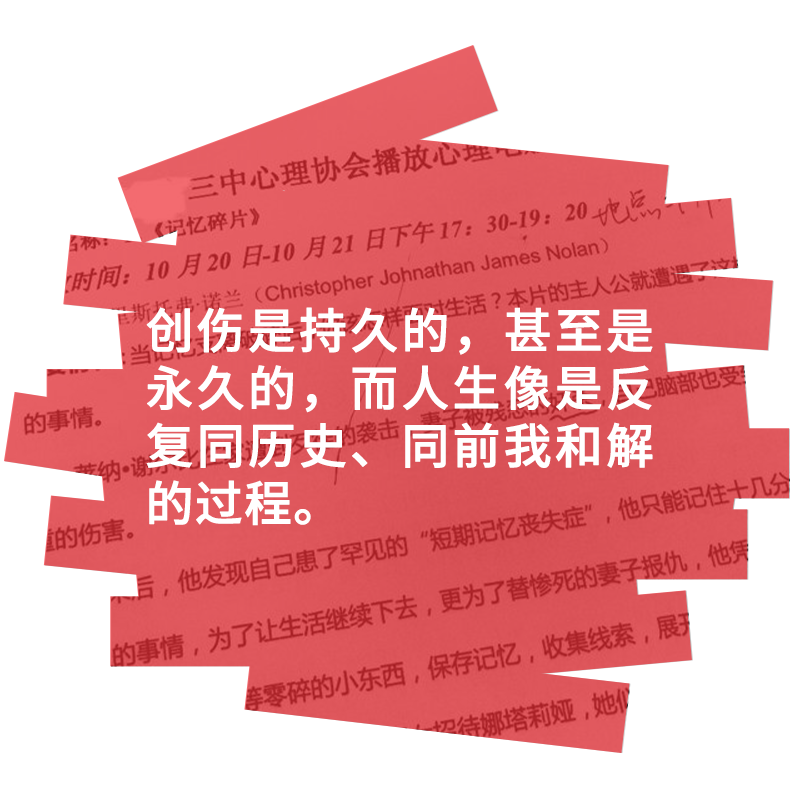

测试中可自由分配的点值共计 20 点,由玩家自行分配至颜值、智力、体质、家境四方面。我将 7 个点分配给了智力,7 个分配给了家境,4 个给了体质,只有 2 个给了颜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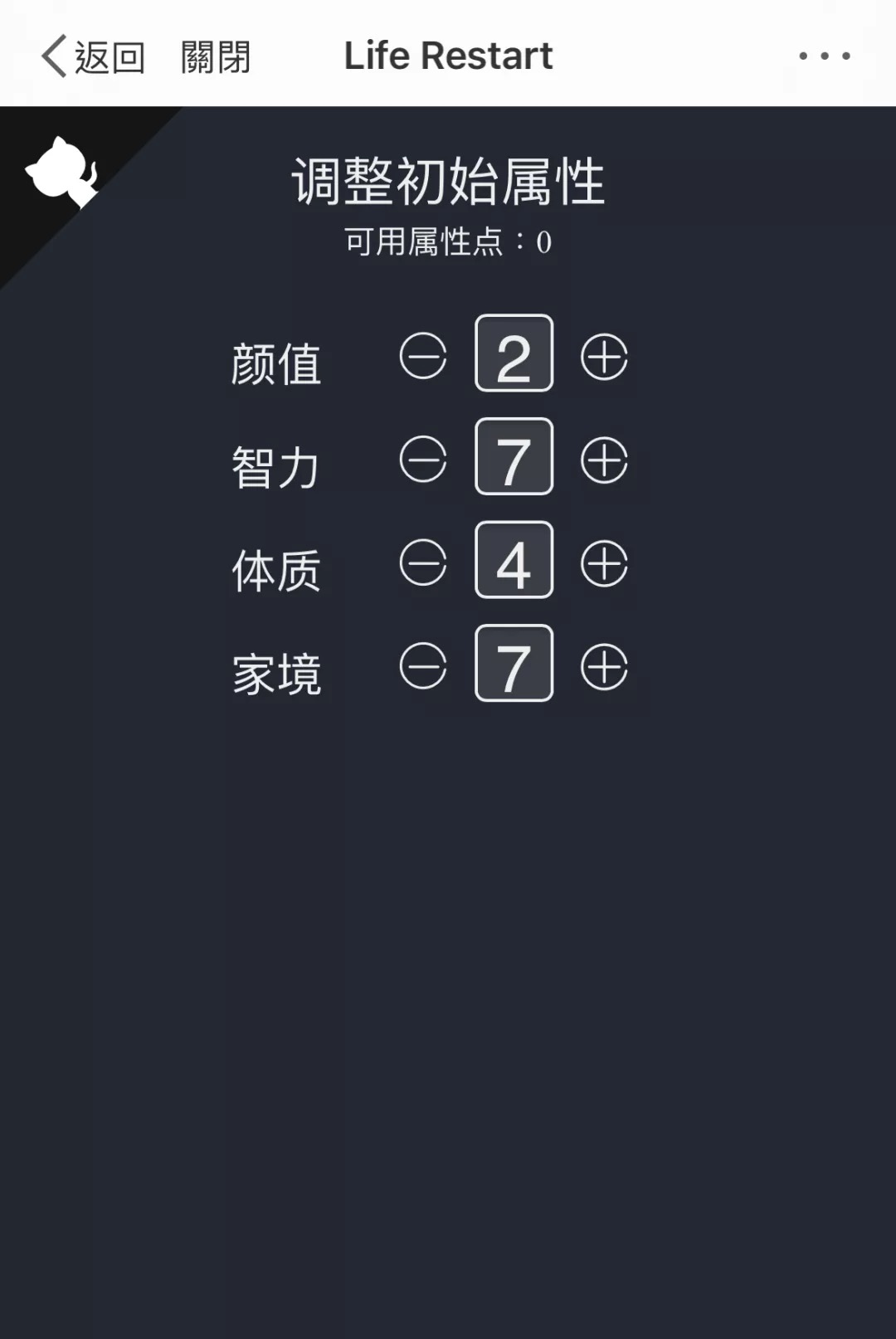
“人生重开模拟器”。我按照自己的真实重生愿望分配点数。
测试结果是一份重生编年史。简单概括我的:一个普通城市中产直男的无趣一生。另外,因为我的家境被评价为 9 分的 “非常优秀”,所以这个城市大概率还是上海或北京。
重生宇宙里的我未历经任何重大个人危机,小时候是市内三好学生,三十岁结婚做了个平凡丈夫,安稳地活到了 73 岁心脏病突发去世。读下来,感觉在读《斯通纳》之城市中产版。虽然寿命不算太长,但现实中的我能活到 37 岁都是难题,更别说 73 了,所以不设太高要求。
其中,重生编年史的前两条如下:“0 岁,你出生了;1 岁,你一直在城市里长大。”
看到第二条时,我便略有满足,感觉重生的我会比现我更幸福。是的,“好想出生就是城市中产”是非常腐朽的愿望,但我想它曾在不少“小镇做题家”的心中闪过。

人生迄今,有一半时间在外求学

我的迁徙求学始于 12 岁。在县城出生长大、度过了人生头 12 年的我,小学毕业后去到家乡所属的地级市念初中,从此开启了独自流落他乡的住校生活。
地级市距离我的家乡县城 140 公里,约两小时车程,人口规模 40 万左右,计程车起步价六块,开车十余分钟便能把市中心绕完,说是个县城也不会有人诧异——可能发达地区的小县都比这里更现代。因为距离较远、市区基础建设和县城相差不大,所以我们县的人对于这个地级市没有太多归属或依附感情,也较少有人主动搬至该市生活、工作,而更愿意迁至离家更近的也更发达的省会。但我还是跑进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小城里初中了,没办法,全市最好的教育资源都在这里。
那是全市最好的初中,我所在的是次重点班。一个班里共有 70 多人,数量惊悚,但那在教育资源紧缺的地区是常态。比起担心特大班的教学质量不佳,我们更担心 40 度的夏天、教室内那一锅酸腥的汗臭味。那味道,打开门窗通风一节课都不会消退。为什么不关门开空调?因为教室与宿舍都没有安装空调,这是五线小城的名牌学校。

这 70 多人中,约一半是本地人,另一半则和我一样,从其他县城独自来到城市求学。在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学生从初中阶段便开始异地求学是普遍现象。
从异地来的同学之中,又有半数以上的同学来自距此地较近的三个县城。他们很多在小学、幼儿园便是同学,初中就算跑到了新的城市求学也是以结伴形式移动,周末也会结伴坐车回家。而从我家乡来的仅我一人。本就带着离乡的不满情绪来上学,现在还发现自己是游离在各种已固定好的群体之外的“1”,我更认定自己是这个城市的过路人,度过未来三年后就要将此地甩在脑后,干干净净,不再回忆。
但人无法轻松做到选择性遗忘这些——宿舍内的孤立,犯下的过错,睡不着的夏夜、苦思自己为什么不在县城里那个有空调的学校念书。印象最深刻的,是连续三年不在家人身边度过的冬至,本地的同学都回家过节,我和同为外地来的同学去食堂吃了一顿普通的饭,最后回到教室等待人员复位的晚自习;还有每个周日,在家乡返回城里的大巴上看到的晚霞,它往我身后跑去,离我越来越远。
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师资、教学设备、学校管理等),家长会将孩子送往教育资源更雄厚的地区,方式有学校自主招生、政策、择校等。乡村孩子往县城走,县城孩子往城市走,普通城市的孩子往省会走,省会或一线的孩子有人留下,有人早早出国。近二三十年交通与社会环境的发展,以及民营学校的大量兴办,为迁徙式的异地求学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我的老爸出生于 70 年代初,是一名在四五线城市活跃的管理层人士,更是指导了我整个教育之路的导师。当我问到“将子女放到更好的城市、让他们独立成长”在他的朋友间是不是很流行,他用了三个“非常”告诉我,这在他的社交圈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深知小地方教育资源、教学环境的落后,所以具备一定能力、财力的家长,会尽力将孩子送往更好的地方求学。多数是在中学时期开始,也有的从小学阶段就行动。
教育资源、环境与孩子成才并没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家长自身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就算仅有 1% 的可能推动孩子成才,他们也会努力抓住,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地方。至于成功与否,还得看孩子自身。
我和老爸说,这听起来像是具有高风险的投资。他立刻温柔地反驳我,称那不是投资,为孩子的教育所付出的一切,都不能被施加“投资”这样冰冷的修辞。
学校老师也透视到小地方教育的局限。初三临近中考时,我的老师说了一句令我记忆深刻的话:“能出去就出去吧。”但其实那座小城的重点高中不算差,只是人们忍不住想象更好的客观条件带来的更多可能。正如我幻想自己是个一线城市中产直男就能消除现成的一半烦恼。
借老师的吉言,我走了出来,进入位于省会的省重点高中就读。在初中所在的五线小城,我只待了三年,还未得以熟悉一个城市的节奏与脉络,便要换到另一个没有我历史的城市展开新的生活。这次我还是独自一人。
那所高中的外地生源不多,90% 左右的学生从本地初中升入,不少同学在初中,甚至在小学、幼儿园时就已相识。
我的宿舍除我以外皆是本地学生。距高考一个月的时候,午休时间,舍友的家长经常带着准备给孩子的午饭出现在宿舍中。他们会贴心地准备多人份,所以每次我都能蹭到几口。有一次,几位舍友的家长同时探访,于是我这边蹭点饺子,那边蹭点米粉,再去蹭点小菜,一顿午饭就这样解决。
后来,我和爸妈随口提到“XX 妈妈做的饺子很好吃”。随口一提便引发了高考前的数天,我爸从 90 公里外的老家开车带了个保温盒过来,打开一看,是我最喜欢吃的咖喱牛腩。老爸说我妈刚做好、他就开车上高速送来了,叫我趁热吃。
家长给我带顿午餐,要上高速,要跨越 90 公里;而舍友的家长带顿饭来,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车程,几个路口。在那时候,高中三年萦绕在我心中的异乡人情感上升至最浓烈的点。
几天后高考结束,我迎来人生中最长的三个月暑假,终于得以和父母连续长时间相处。我与父母收拾宿舍内的物件,抹清在这个城市的三年印记只需一个多小时,时长等同于返家的车程。
如果要坚持“让孩子独自迁徙求学是一种风险不定的投资”这个类比,我爸妈的这笔投资显然是失败了。我没有如父母的期望,在重点高中里好好学习、最后考上 985 大学。在最后一次从学校返家的高速路上,我和爸妈坦白:其实我觉得自己辜负了一家的期望,或许烂人如我在哪里都一样,根本不必去好学校。坐在前座的他们却说,只要我在这里成长为了更好的人,并健康安全地长大,那就足够了。
也许他们也清楚,在那不安定的迁徙求学中,我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同时也失去了成长期中非常重要的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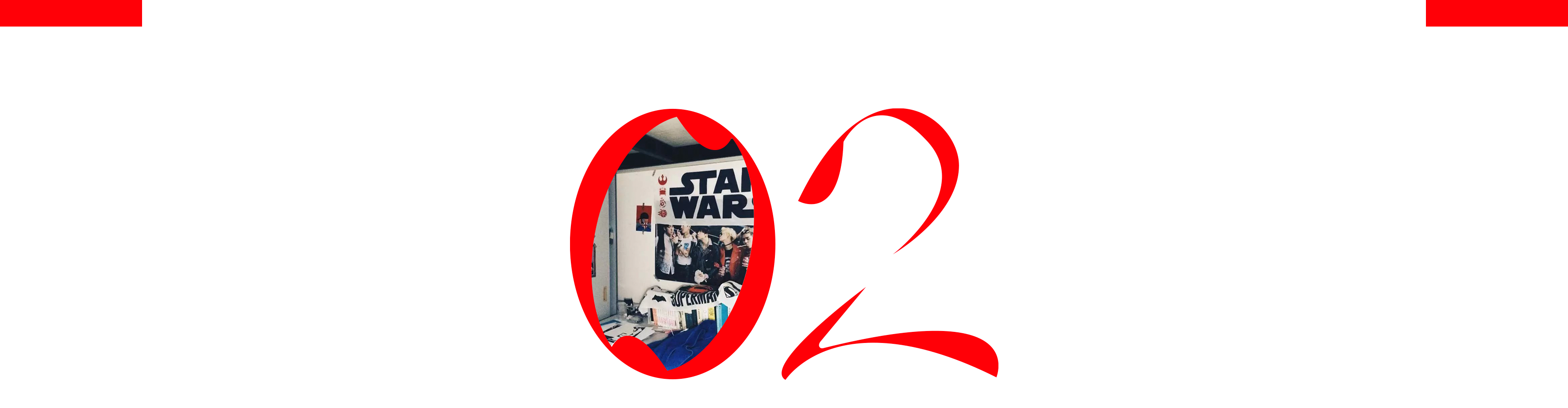
潇洒求学牧人的得与失


高三的宿舍。由于没有家长管束,桌上堆的是漫画和对应试作文无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那些没有机会迁徙的人


从高中的宿舍望出去,能看到游泳池、图书馆和田径场。游泳池旁的墙上都是学生的涂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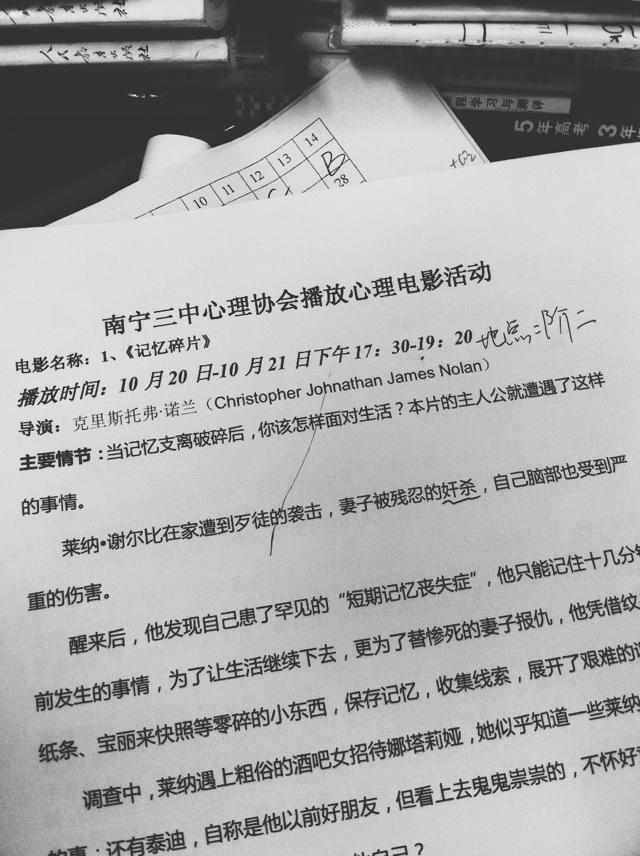
高中经常会有电影放映活动。虽然放的是诺兰,可能不够 fancy。
教育不仅是对成绩的塑造,更是对人的塑形——在那时,真切地感受到“素质教育”这个总被批评悬置已久而不实践的短语落了下来。而对于身边那些家里有小实验室、护照上的印章多到要换本的城市中产同学而言,这些不足为奇。他们在小学就已习惯了塑胶跑道。
到了大学,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在与本地同学回忆中小学往事时,我更强烈地感受到地区教育资源间的差距。是这样的差距与不均让我迁徙、游牧,让家庭在成长期中隐形、缺位,推着我的性格向内坍缩,直到压出无法在短时内平息的创伤。
我们不应将苦痛分级比较,因为不应因更强烈的痛的存在而忽视小伤。每一种都是致命的刀。但是,每当回顾求学经历中遇到的、来自不同家境的同龄人,我会想:那些连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的机会都没有的同龄人,他们所吞下的苦的程度,是我青春期缺爱的创伤所能概括的吗?
锅巴是我高中追星时认识的朋友,她从 2019 年开始在一个国家级贫困乡的小学支教。当地师资紧缺,往往依靠参与支教计划的老师才能完成授课,而且通常一师多职:要教语文,同时还要教美术、音乐。
去年夏天,我跟着她走进了那所学校,从县城中心开始驾车,要二十分钟、绕过十余个山间弯道、最后驶下一个坡,才能到达。学校唯一一幢教学楼的对面是村子的池塘,后面紧挨着村民的家。一切包围在大山之中,吞在里面。这儿没有跑道,只有两个排球场地,那也是全村的公共活动场所。

锅巴支教的小学旁的池塘,与学校里唯一一幢教学楼相对。到了雨季,池塘的水会漫上来。旁边就是村民的家。

我们都在学习与前我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