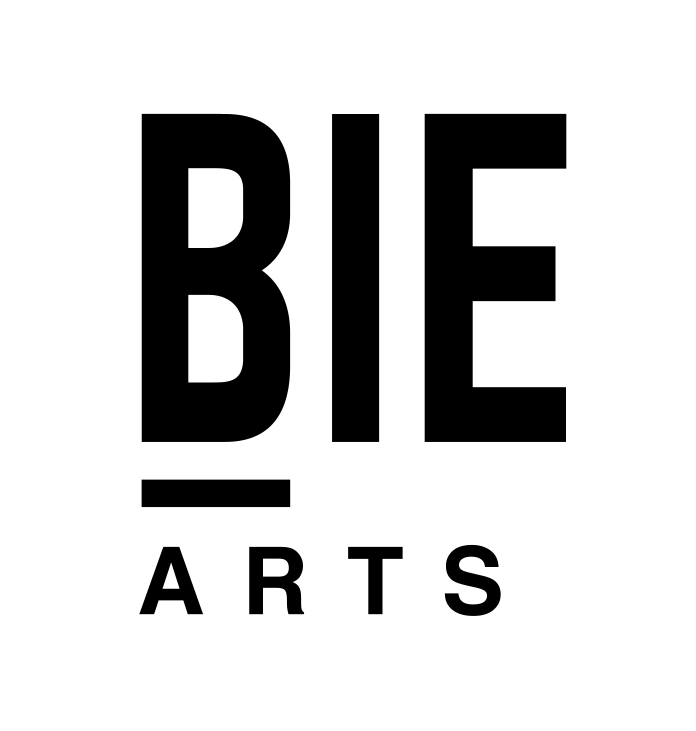在野生都会中寻找宁芙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在希腊神话中,自然幻化的精灵——宁芙经常以年轻貌美的少女形象出没于山林、原野、泉水、大海,她们羞于见人,不时地化身为树、水和山,只有不停追逐、探寻方能得见其貌。她们对应于大自然的基本元素,象征着最为本质的根源。
当“野生大都会”的展览海报映入眼帘,你可能感觉迷茫并兴奋,疑惑中充满好奇。野生象征着原始、自然、野蛮,而都会代表着人工、有序、规制,这两个原本互相对立的图景,却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倏然生出一种暧昧不清、蠢蠢欲动的联系——哦不,转念一想,水泥钢筋结构背后的那层不可见但更真实的“网络”不就是一个“野生大都会”吗?在少数人惊心建立起来的互联网秩序中,来自民间的力量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展览现场按照一种社交网络的逻辑被建立起来,信息丰富、过剩、破碎,随机拼接但又浑然一体。走进其中,发现整个展览空间就像刚刚在朋友圈刷屏的一张张照片,平铺直叙,与手机上的观看融为一体。展览本身像一种扁平化的观看对象,让人联想起《小红帽》绘本里一层层的灌木丛林。然而,就像处处是诱惑的网络大都会一样,你在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同时,可能跟五光十色背后的本质擦肩而过;在这场展览中,15位艺术家的创作光怪陆离,它们所呈现的问题却是多维而深层的。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胡安·塞巴斯蒂安·佩拉兹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哥伦比亚籍艺术家胡安·塞巴斯蒂安·佩拉兹(Juan Sebastián Peláez)的“无头人”系列的创作,可以回溯到他 12 岁时回到家乡哥伦比亚的经历。在美国迈阿密长大的他惊讶地发现,现实中的哥伦比亚有车有高楼,完全不同于自己在电影和卡通里看到的哥伦比亚。而且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哥伦比亚人并无法跟动物说话。上学之后,他开始思考这种对于“他者”的观看,资本主义运作下的文化殖民对于身份认知的影响。这些“无头人”的形象来源于几百年前西方白人对拉丁美洲土著的描绘。艺术家则选取了同样来自拉丁美洲地区的明星,将他们的照片进行改换:人尽皆知的公众人物突然被“还原”成殖民者眼中奇特的当地人,以此暗示这种对“他者”的观看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而对立体人形的扁平化表现,则对应于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分享信息的形态,这些“他者”同时也成为了当代人们的消费对象。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胡安·塞巴斯蒂安·佩拉兹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与胡安相呼应,来自德国的艺术家安娜•乌登伯格(Anna Uddenberg)对现代文明的产物——头等舱座椅、咖啡桌、登山背包等这些象征着奢侈、舒适、安全的现成物进行再塑。作品中,这些物件原本的意义和功能被消解,这些熟悉的物件也即时化身成陌生的“他者”。安娜•乌登伯格也在作品中暗喻了女性作为他者被强制表现的状态。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陆平原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对于陆平原而言,“故事本身就是艺术品”,由于从小阅读《奥秘》杂志而在脑海中形成的各种奇谭一般的故事,被打印在大幅的泡沫板上,由两只大手拿起高高悬于展厅中央。与以往 A4纸的尺幅不同,故事的细节仿佛也被放大,置身作品前,恍然有种主角代入的感觉。自己的身体跟故事里中了蛇毒一般,动弹不得,幻觉和真实就在字里行间交错。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雅各比·萨特怀特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走出陆平原的故事,雅各比·萨特怀特(Jacolby Satterwhite)的作品《祝福大道》带来另一种真假交错。在现实中的城市空间以及 3D构建的幻想空间构成的背景中,他尽可能地让身体呈现各种不可思议的姿势与 3D构建的动画人形互动,同时也在城市中的咖啡馆等公共空间跳着象征着黑人文化的街舞,以此来讲述与黑人文化、美国的消费主义相关的主题,并用身体感知形成个人叙事。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乔希·斯博林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乔希•斯博林(Josh Sperling)的创作受到美国战后极简主义绘画的影响,他的创作模糊了绘画与雕塑、图像与物体之间的界限。他的作品首先使用平面设计软件生成数字化分层模型,然后通过高精度自动化切割机在胶合板上实际操作,确保实现手工无法达到的完美程度。作品对精确度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任何一个组件错误都可能毁了整件作品的最终呈现,可以说是规制的产物,而作品在精确计算后达到的效果却充满了张力和能量。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想要让我的作品更有机、更富有生命力,而不显得那么地精确计算”。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卡特娅•诺维兹科娃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当乔希将世间万物简化成形状的同时,爱沙尼亚艺术家卡特娅•诺维兹科娃(Katja Novitskova)则将网上采集的各种图像当作单纯“形状”进行拼贴,并将作品命名为“近似”。她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挖掘迥异的物体之间微妙的联系和相似性,以此为基础,使拼贴后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诡异而又奇妙的和谐。作品由此指涉数字图像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的接收、解构及重构的过程。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丁力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丁力的作品则是通过对油画颜料、喷漆、画笔与画框这些媒介材料的反复探索和重构,对架上绘画这一传统形式进行试验,最终将他的绘画表现融于对当下的思考和观察。他笔下的《阿姨》、《男青年》看似模糊,但却是你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一张张熟悉的脸,通过这些反复琢磨的线条和色彩,你甚至可以感知他们的情绪和处境,并进而延伸至当代人整体的处境。
徐震的《新-拉奥孔》和《新-赫拉克勒斯》则是更彻底的颠覆。拉奥孔和赫拉克勒斯的头部被放大,站立在海洋球池中,显得头重脚轻,原本的庄严和悲剧色彩被消解。他们看上去更像是面对如今的人工智能一筹莫展。

“他们看上去更像是面对如今的人工智能一筹莫展。”,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至此不难发现,艺术家们所做的大抵是通过创作对现状进行质疑、反对规制、甚至进行颠覆和破坏。或许可以用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的一段论述,说明“野生”与“都会”两者,在艺术家的创作之下,如何产生关联:
“野兽是从属于死亡的生命,同时也以死亡的执行者形态出现。在动物世界中,生命依据其自身法则,潜藏着不断捕食到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动物自身内部潜藏着反自然的核心本质,因此动物才得以从属于自然这个系统中。这种最深层的本质从植物转移到动物,生命才得以从秩序的空间脱离,再次成为野生之物。”
也就是说,如果将艺术家比喻为都会中的动物,那么相对于他而言,他必须潜藏着反都会这一自然的本质,方才能够具有野性。当然,这不仅仅是针对艺术家,我们每一个观者,都需要带着这样的潜质,才能够逃脱所谓的秩序空间,而具有“野性”。而在具有了野性之后,方才能发现丛林中隐身的那些“宁芙”。
“野生大都会”将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至 2020 年 2 月 2 日。
在下方查看更多展览现场图片:

图为陈冠希作品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在希腊神话中,自然幻化的精灵——宁芙经常以年轻貌美的少女形象出没于山林、原野、泉水、大海,她们羞于见人,不时地化身为树、水和山,只有不停追逐、探寻方能得见其貌。她们对应于大自然的基本元素,象征着最为本质的根源。
当“野生大都会”的展览海报映入眼帘,你可能感觉迷茫并兴奋,疑惑中充满好奇。野生象征着原始、自然、野蛮,而都会代表着人工、有序、规制,这两个原本互相对立的图景,却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倏然生出一种暧昧不清、蠢蠢欲动的联系——哦不,转念一想,水泥钢筋结构背后的那层不可见但更真实的“网络”不就是一个“野生大都会”吗?在少数人惊心建立起来的互联网秩序中,来自民间的力量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展览现场按照一种社交网络的逻辑被建立起来,信息丰富、过剩、破碎,随机拼接但又浑然一体。走进其中,发现整个展览空间就像刚刚在朋友圈刷屏的一张张照片,平铺直叙,与手机上的观看融为一体。展览本身像一种扁平化的观看对象,让人联想起《小红帽》绘本里一层层的灌木丛林。然而,就像处处是诱惑的网络大都会一样,你在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同时,可能跟五光十色背后的本质擦肩而过;在这场展览中,15位艺术家的创作光怪陆离,它们所呈现的问题却是多维而深层的。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胡安·塞巴斯蒂安·佩拉兹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哥伦比亚籍艺术家胡安·塞巴斯蒂安·佩拉兹(Juan Sebastián Peláez)的“无头人”系列的创作,可以回溯到他 12 岁时回到家乡哥伦比亚的经历。在美国迈阿密长大的他惊讶地发现,现实中的哥伦比亚有车有高楼,完全不同于自己在电影和卡通里看到的哥伦比亚。而且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哥伦比亚人并无法跟动物说话。上学之后,他开始思考这种对于“他者”的观看,资本主义运作下的文化殖民对于身份认知的影响。这些“无头人”的形象来源于几百年前西方白人对拉丁美洲土著的描绘。艺术家则选取了同样来自拉丁美洲地区的明星,将他们的照片进行改换:人尽皆知的公众人物突然被“还原”成殖民者眼中奇特的当地人,以此暗示这种对“他者”的观看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而对立体人形的扁平化表现,则对应于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分享信息的形态,这些“他者”同时也成为了当代人们的消费对象。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胡安·塞巴斯蒂安·佩拉兹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与胡安相呼应,来自德国的艺术家安娜•乌登伯格(Anna Uddenberg)对现代文明的产物——头等舱座椅、咖啡桌、登山背包等这些象征着奢侈、舒适、安全的现成物进行再塑。作品中,这些物件原本的意义和功能被消解,这些熟悉的物件也即时化身成陌生的“他者”。安娜•乌登伯格也在作品中暗喻了女性作为他者被强制表现的状态。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陆平原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对于陆平原而言,“故事本身就是艺术品”,由于从小阅读《奥秘》杂志而在脑海中形成的各种奇谭一般的故事,被打印在大幅的泡沫板上,由两只大手拿起高高悬于展厅中央。与以往 A4纸的尺幅不同,故事的细节仿佛也被放大,置身作品前,恍然有种主角代入的感觉。自己的身体跟故事里中了蛇毒一般,动弹不得,幻觉和真实就在字里行间交错。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雅各比·萨特怀特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走出陆平原的故事,雅各比·萨特怀特(Jacolby Satterwhite)的作品《祝福大道》带来另一种真假交错。在现实中的城市空间以及 3D构建的幻想空间构成的背景中,他尽可能地让身体呈现各种不可思议的姿势与 3D构建的动画人形互动,同时也在城市中的咖啡馆等公共空间跳着象征着黑人文化的街舞,以此来讲述与黑人文化、美国的消费主义相关的主题,并用身体感知形成个人叙事。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乔希·斯博林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乔希•斯博林(Josh Sperling)的创作受到美国战后极简主义绘画的影响,他的创作模糊了绘画与雕塑、图像与物体之间的界限。他的作品首先使用平面设计软件生成数字化分层模型,然后通过高精度自动化切割机在胶合板上实际操作,确保实现手工无法达到的完美程度。作品对精确度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任何一个组件错误都可能毁了整件作品的最终呈现,可以说是规制的产物,而作品在精确计算后达到的效果却充满了张力和能量。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想要让我的作品更有机、更富有生命力,而不显得那么地精确计算”。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卡特娅•诺维兹科娃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当乔希将世间万物简化成形状的同时,爱沙尼亚艺术家卡特娅•诺维兹科娃(Katja Novitskova)则将网上采集的各种图像当作单纯“形状”进行拼贴,并将作品命名为“近似”。她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挖掘迥异的物体之间微妙的联系和相似性,以此为基础,使拼贴后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诡异而又奇妙的和谐。作品由此指涉数字图像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的接收、解构及重构的过程。

“野生大都会”展览现场,丁力作品,宝龙美术馆,2019,上海
丁力的作品则是通过对油画颜料、喷漆、画笔与画框这些媒介材料的反复探索和重构,对架上绘画这一传统形式进行试验,最终将他的绘画表现融于对当下的思考和观察。他笔下的《阿姨》、《男青年》看似模糊,但却是你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一张张熟悉的脸,通过这些反复琢磨的线条和色彩,你甚至可以感知他们的情绪和处境,并进而延伸至当代人整体的处境。
徐震的《新-拉奥孔》和《新-赫拉克勒斯》则是更彻底的颠覆。拉奥孔和赫拉克勒斯的头部被放大,站立在海洋球池中,显得头重脚轻,原本的庄严和悲剧色彩被消解。他们看上去更像是面对如今的人工智能一筹莫展。

“他们看上去更像是面对如今的人工智能一筹莫展。”,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至此不难发现,艺术家们所做的大抵是通过创作对现状进行质疑、反对规制、甚至进行颠覆和破坏。或许可以用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的一段论述,说明“野生”与“都会”两者,在艺术家的创作之下,如何产生关联:
“野兽是从属于死亡的生命,同时也以死亡的执行者形态出现。在动物世界中,生命依据其自身法则,潜藏着不断捕食到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动物自身内部潜藏着反自然的核心本质,因此动物才得以从属于自然这个系统中。这种最深层的本质从植物转移到动物,生命才得以从秩序的空间脱离,再次成为野生之物。”
也就是说,如果将艺术家比喻为都会中的动物,那么相对于他而言,他必须潜藏着反都会这一自然的本质,方才能够具有野性。当然,这不仅仅是针对艺术家,我们每一个观者,都需要带着这样的潜质,才能够逃脱所谓的秩序空间,而具有“野性”。而在具有了野性之后,方才能发现丛林中隐身的那些“宁芙”。
“野生大都会”将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至 2020 年 2 月 2 日。
在下方查看更多展览现场图片:

图为陈冠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