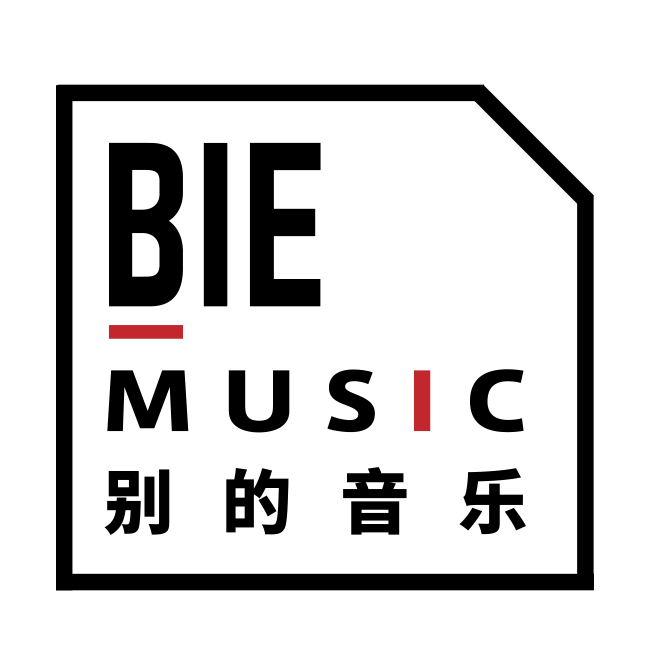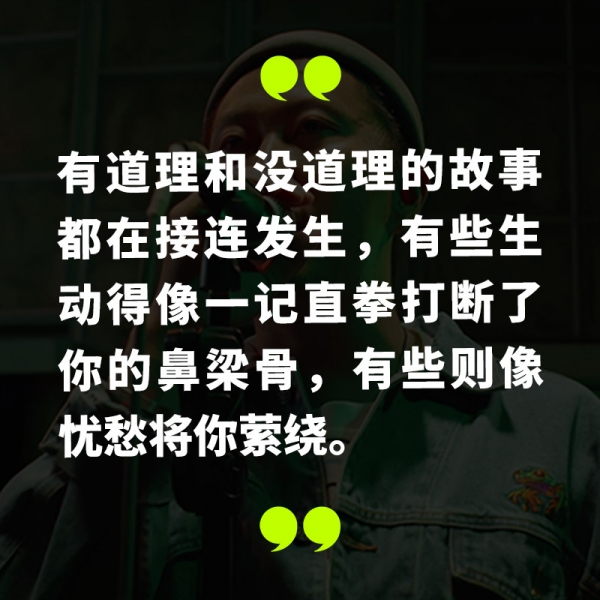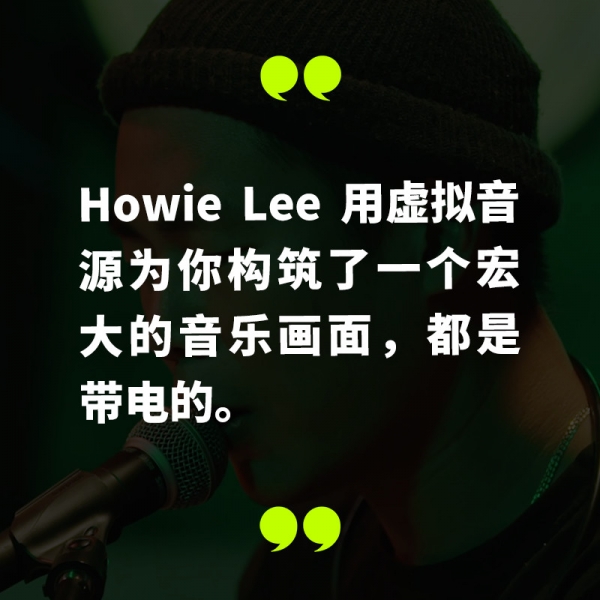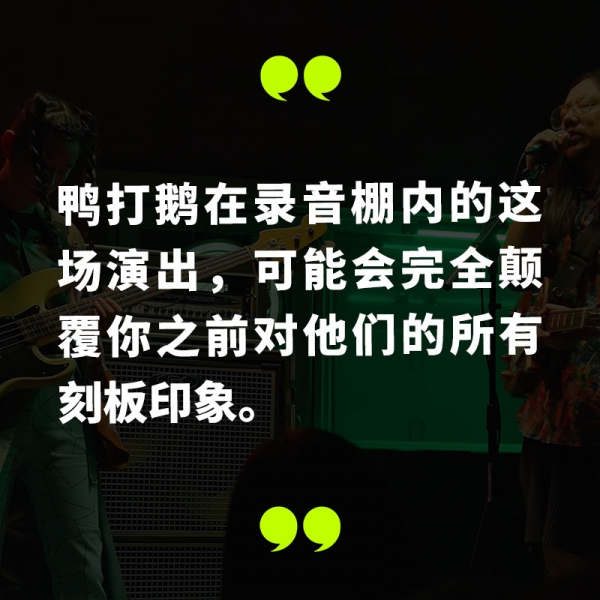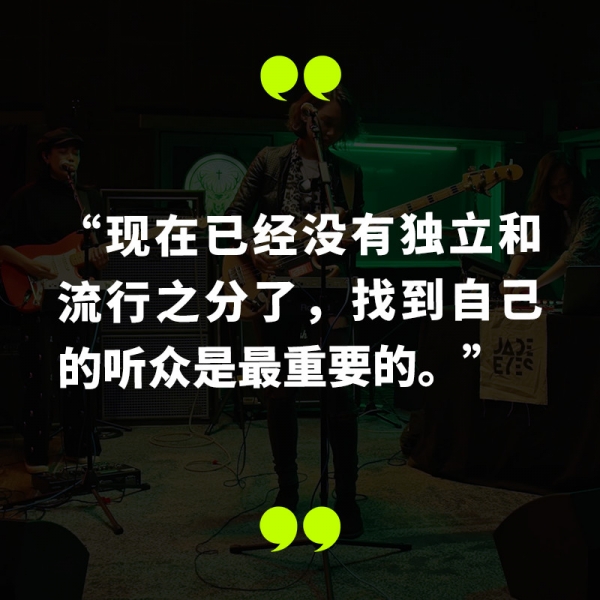排练完收工,乐队要给郑冬过生日。他在拉琴包,我推门进来,就听到话 “快三十岁的人了,不回家,每天呆在北京搞些不知道什么音乐。” 阿辉在收拾效果器,毛特装他的镲片,还顺着情节补了一句,“一天到晚不正经。”
“这话谁说的?” 我问,没听到上文,直接接入三个广西人的聊天框,无法准确进入情境。
沉默了两秒,郑冬背着吉他出门了,“我说的。”
“玩乐队” 也是 “玩建筑”
跟 2018 年的《人性建筑》比起来,Backspace 的新歌更加不再能用笼统苍白的 “后朋克” 定义 —— 这定义本身就挺傻的,而他们的新东西杂糅成分更多。就像冬天来朋友家煮顿火锅,各家带上特产食材,这桌囊括五湖四海。郑冬的吉他铺在中低频,音色更厚实,他的 riff 还带着德系酸性的味道,但人声部分的旋律感更强了,“好听啊,耳仔酥服”;阿辉的吉他则是亮眼的那一个,切分与骤停,能听出其中的布鲁斯味道。效果器被他用得很克制,一切适度,恰恰好。

这间排练室大点。图片来源于作者
阿辉本来话少,说一句退三步。他们最开始是个玩布鲁斯的乐队,阿辉那时候执着于技巧,投入于练琴,“听罗伯特约翰逊、滚石、猫王、泥水,这些老爷爷音乐,都是过时的东西,不酷。”《人性建筑》里两条吉他线相互配合,编得精彩,但已经不是阿辉如今的口味,“听着可能挺唬人的,但其实就是在炫技,绕来绕去的。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老感觉动机不纯”。过了那个时间段,他选择就简,“坂本龙一说,少既是多。”

吉他口味善变的 “金城武”(戏称),图片来源于作者
瓜瓜喜欢用更明亮的贝斯旋律,时而跳脱出来吸引耳朵。“我喜欢用 bassline 去和吉他鼓配合起来,貌离神合就很好玩了,而不是刻板意义上的贝斯就要铺低频。” 你觉得三条线在交错,没留下空档,显得饱满。毛特最近在钻研非洲节奏,重拍往后,切分和 Layback 被安插进他仍然干脆有力的鼓里 —— 这些不同的元素,共同组成了新的 Backspace。
郑冬在脑子里规划好了一套雏形概念:每首歌都用一种动物表达,写词和旋律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半确定的同心圆,不会偏移太远。但专辑名字还没想好,可能跟 “动物世界” 或者 “动物园” 有点关系。“人性建筑我倒是什么都不多想,见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写什么,” 郑冬说,“全给它打打散了,再新组合排列。和起建筑一个道理,先和稀泥再打钢筋龙骨。”
这也养成了他们不爱拿风格说事的脾性,“如果上来大家就觉得玩这风格那风格的我们就别建筑了,咱们可以玩泥沙,你堆一个堡垒,我挖个洞。” 别去定义,玩乐队而已。
“是个加快进度条的年轻乐队”
以一个乐队的时间轴来看 Backspace,他们走得不坎坷。2016 年夏天 Backspace 还是纯正的 “广西籍” 。郑冬先行北上,阿辉、大龙和毛特也随后来到北京。据说乐队名字来源于一段伤感且不了了之的旧日故事:那是一个用电脑网络聊天的远程爱情,郑冬欲言又止,在对话框里犹犹豫豫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几乎要按烂了那个 “Backspace” 键。故事真伪和细节,我也没能顺利向郑冬求证。
他们四个住在鼓楼西大街,这一小块北京中心的老城区不知收留了多少刚开始玩乐队的年轻人:无一例外,他们住的小房子也掉墙皮,甚至屋顶漏雨。阿辉被淋坏过一台电脑。周三、周四的晚上他们去 Temple 演出,虽然周中的时段不算好,但好在 Temple 总愿意给新乐队提供舞台。


鼓楼西大街出租屋生活。图片来源于受访对象
被 Michael 看到那天,他们的演出台下就三个人,他们来北京刚一年,恰是 2017 年夏天。
鼓楼西大街的房子后来没再住,换电脑的成本还不如拿去抵房租;Backspace 似乎就此乘上了加快的进度条:2018 年的夏天即发行了第一张全长专辑《人性建筑》,干净漂亮地完成了一轮全国巡演,这对一支新乐队来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经历,他们每个人都有些所得和遗憾,加上大龙得回家了,家里催得紧,瓜瓜成为新血加入之后,他们在排练室里打磨新东西。每个人都与之前不一样了,预计在明年春天录制的新专辑,或许会让你眼前一亮。

图片来源于作者
状温和的 “废物”
“来北京就是想当个 ‘废物’ 啊。” 这话的烈性可能跟生活中的他们有些违和,但如果要探讨摇滚乐态度的多种理解和呈现方式,Backspace 接近我认为的平衡状态。这四个人 “性格烈,状温和” ,在自己独立的判断和价值观里张弛有度,清醒地思考,谨慎地表达。时而真情流露,半开玩笑似的回怼一句 “腥臭!”,也没想跟渔夫结什么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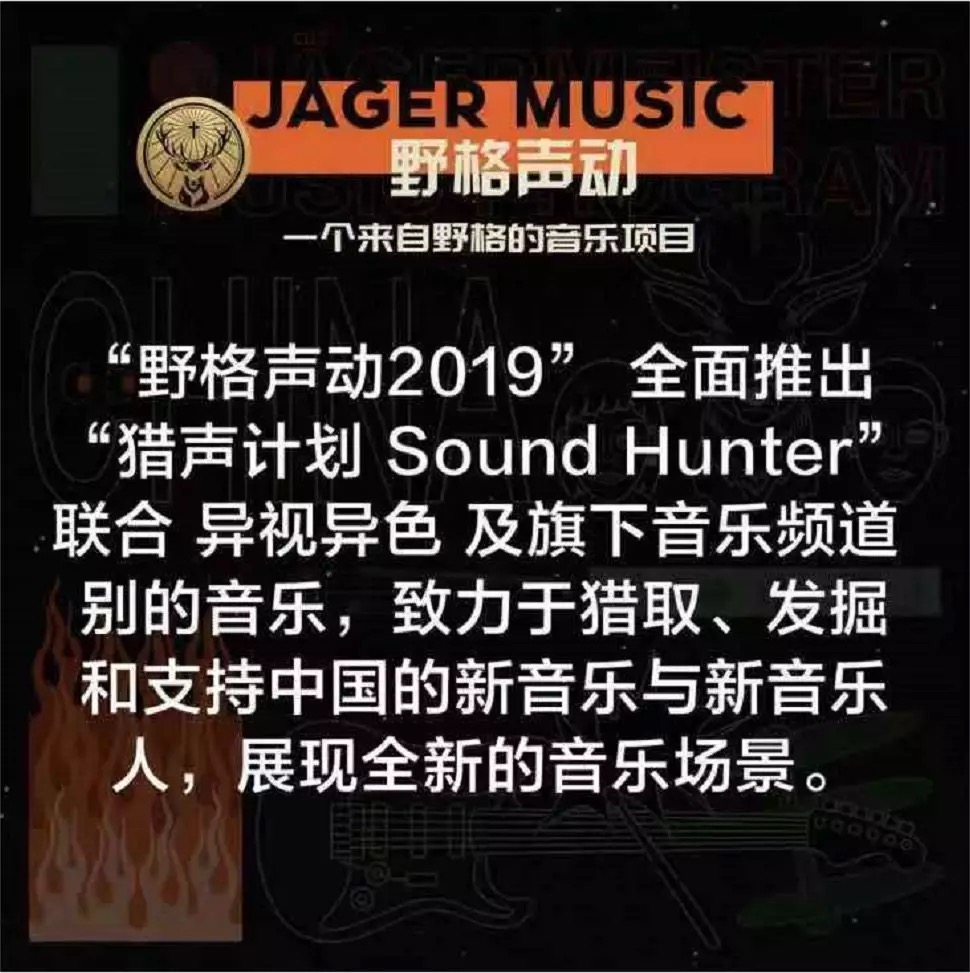
但这不巧是 “家长眼里的废物”,这顶臭帽子也能安在每一个不想循规蹈矩的人脑门上。没能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回乡 “成家立业”,房子车子和酒杯都满上,这帽子就能从天而降,成为近亲苦口婆心的对象,远方亲戚八卦里的谈资。广西仔们离开家乡,嘴里嚷着要做 “废物” ,顶着这帽子在北京认真地铺陈开自己的生活:工作,社交,玩音乐,融入北京。郑冬没想过离开,阿辉和毛特直言不讳自己的虚荣心,“得混出点名堂”。三个广西仔一边闷声听着手机那头声嘶力竭或喋喋不休,一边摸索在北京扎根 —— 随着年岁增长,压力与日俱增。
郑冬在排练房嚷嚷 “三十岁” 的时候我以为他们真到了而立之年这个焦虑点了,后来发现这三个 93 年出生的广西仔有点杞人忧天,他们实在离三十岁还有点距离,“还有三年多呢,急什么。”
“快了,快了。”
给郑冬庆生那晚上四个人挤在不大的厨房里忙活,进进出出的样子恍然有点像回到鼓楼西大街的出租屋,但又不一样了,这是新的 Backspace 和他们不断在刷新的生活。他们身处迎面而来的风里,一步步顶着风往前走,也不会忘了及时行乐:生活是杯好酒,得好喝易上头。
* 注:文章封面图来源于 @bbf3
排练完收工,乐队要给郑冬过生日。他在拉琴包,我推门进来,就听到话 “快三十岁的人了,不回家,每天呆在北京搞些不知道什么音乐。” 阿辉在收拾效果器,毛特装他的镲片,还顺着情节补了一句,“一天到晚不正经。”
“这话谁说的?” 我问,没听到上文,直接接入三个广西人的聊天框,无法准确进入情境。
沉默了两秒,郑冬背着吉他出门了,“我说的。”
“玩乐队” 也是 “玩建筑”
跟 2018 年的《人性建筑》比起来,Backspace 的新歌更加不再能用笼统苍白的 “后朋克” 定义 —— 这定义本身就挺傻的,而他们的新东西杂糅成分更多。就像冬天来朋友家煮顿火锅,各家带上特产食材,这桌囊括五湖四海。郑冬的吉他铺在中低频,音色更厚实,他的 riff 还带着德系酸性的味道,但人声部分的旋律感更强了,“好听啊,耳仔酥服”;阿辉的吉他则是亮眼的那一个,切分与骤停,能听出其中的布鲁斯味道。效果器被他用得很克制,一切适度,恰恰好。

这间排练室大点。图片来源于作者
阿辉本来话少,说一句退三步。他们最开始是个玩布鲁斯的乐队,阿辉那时候执着于技巧,投入于练琴,“听罗伯特约翰逊、滚石、猫王、泥水,这些老爷爷音乐,都是过时的东西,不酷。”《人性建筑》里两条吉他线相互配合,编得精彩,但已经不是阿辉如今的口味,“听着可能挺唬人的,但其实就是在炫技,绕来绕去的。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老感觉动机不纯”。过了那个时间段,他选择就简,“坂本龙一说,少既是多。”

吉他口味善变的 “金城武”(戏称),图片来源于作者
瓜瓜喜欢用更明亮的贝斯旋律,时而跳脱出来吸引耳朵。“我喜欢用 bassline 去和吉他鼓配合起来,貌离神合就很好玩了,而不是刻板意义上的贝斯就要铺低频。” 你觉得三条线在交错,没留下空档,显得饱满。毛特最近在钻研非洲节奏,重拍往后,切分和 Layback 被安插进他仍然干脆有力的鼓里 —— 这些不同的元素,共同组成了新的 Backspace。
郑冬在脑子里规划好了一套雏形概念:每首歌都用一种动物表达,写词和旋律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半确定的同心圆,不会偏移太远。但专辑名字还没想好,可能跟 “动物世界” 或者 “动物园” 有点关系。“人性建筑我倒是什么都不多想,见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写什么,” 郑冬说,“全给它打打散了,再新组合排列。和起建筑一个道理,先和稀泥再打钢筋龙骨。”
这也养成了他们不爱拿风格说事的脾性,“如果上来大家就觉得玩这风格那风格的我们就别建筑了,咱们可以玩泥沙,你堆一个堡垒,我挖个洞。” 别去定义,玩乐队而已。
“是个加快进度条的年轻乐队”
以一个乐队的时间轴来看 Backspace,他们走得不坎坷。2016 年夏天 Backspace 还是纯正的 “广西籍” 。郑冬先行北上,阿辉、大龙和毛特也随后来到北京。据说乐队名字来源于一段伤感且不了了之的旧日故事:那是一个用电脑网络聊天的远程爱情,郑冬欲言又止,在对话框里犹犹豫豫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几乎要按烂了那个 “Backspace” 键。故事真伪和细节,我也没能顺利向郑冬求证。
他们四个住在鼓楼西大街,这一小块北京中心的老城区不知收留了多少刚开始玩乐队的年轻人:无一例外,他们住的小房子也掉墙皮,甚至屋顶漏雨。阿辉被淋坏过一台电脑。周三、周四的晚上他们去 Temple 演出,虽然周中的时段不算好,但好在 Temple 总愿意给新乐队提供舞台。


鼓楼西大街出租屋生活。图片来源于受访对象
被 Michael 看到那天,他们的演出台下就三个人,他们来北京刚一年,恰是 2017 年夏天。
鼓楼西大街的房子后来没再住,换电脑的成本还不如拿去抵房租;Backspace 似乎就此乘上了加快的进度条:2018 年的夏天即发行了第一张全长专辑《人性建筑》,干净漂亮地完成了一轮全国巡演,这对一支新乐队来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经历,他们每个人都有些所得和遗憾,加上大龙得回家了,家里催得紧,瓜瓜成为新血加入之后,他们在排练室里打磨新东西。每个人都与之前不一样了,预计在明年春天录制的新专辑,或许会让你眼前一亮。

图片来源于作者
状温和的 “废物”
“来北京就是想当个 ‘废物’ 啊。” 这话的烈性可能跟生活中的他们有些违和,但如果要探讨摇滚乐态度的多种理解和呈现方式,Backspace 接近我认为的平衡状态。这四个人 “性格烈,状温和” ,在自己独立的判断和价值观里张弛有度,清醒地思考,谨慎地表达。时而真情流露,半开玩笑似的回怼一句 “腥臭!”,也没想跟渔夫结什么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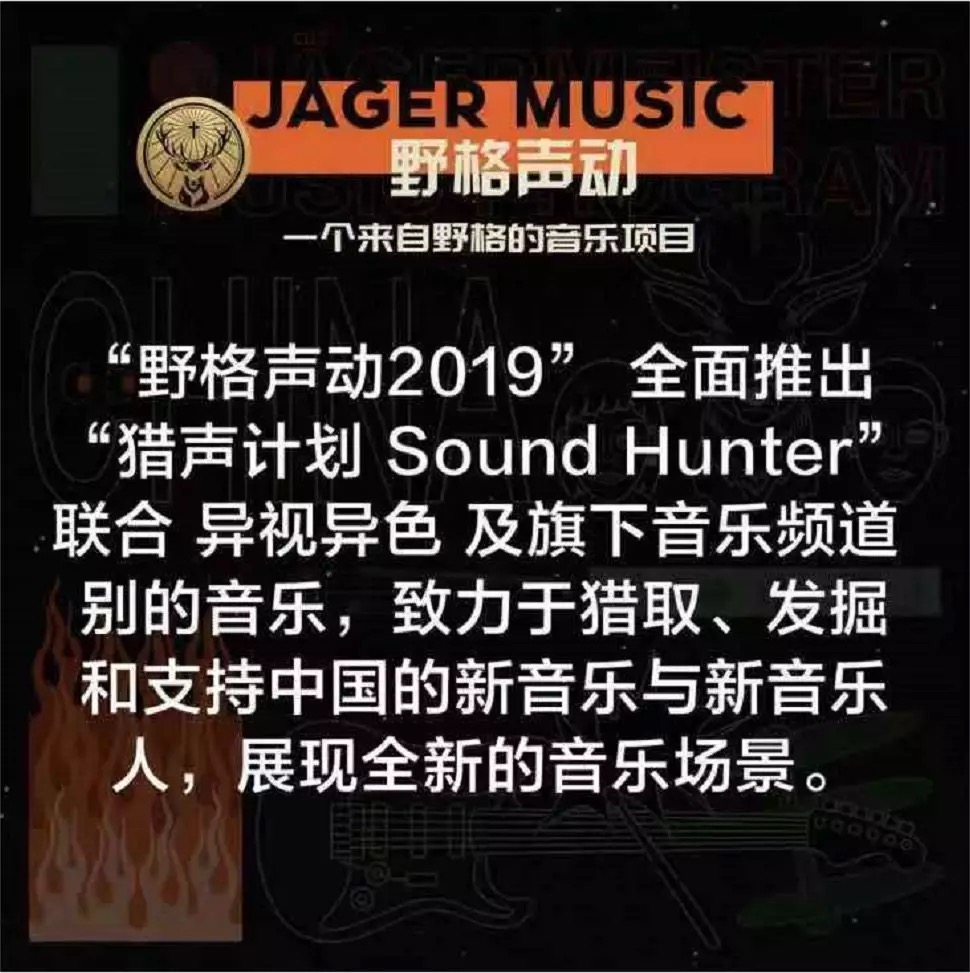
但这不巧是 “家长眼里的废物”,这顶臭帽子也能安在每一个不想循规蹈矩的人脑门上。没能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回乡 “成家立业”,房子车子和酒杯都满上,这帽子就能从天而降,成为近亲苦口婆心的对象,远方亲戚八卦里的谈资。广西仔们离开家乡,嘴里嚷着要做 “废物” ,顶着这帽子在北京认真地铺陈开自己的生活:工作,社交,玩音乐,融入北京。郑冬没想过离开,阿辉和毛特直言不讳自己的虚荣心,“得混出点名堂”。三个广西仔一边闷声听着手机那头声嘶力竭或喋喋不休,一边摸索在北京扎根 —— 随着年岁增长,压力与日俱增。
郑冬在排练房嚷嚷 “三十岁” 的时候我以为他们真到了而立之年这个焦虑点了,后来发现这三个 93 年出生的广西仔有点杞人忧天,他们实在离三十岁还有点距离,“还有三年多呢,急什么。”
“快了,快了。”
给郑冬庆生那晚上四个人挤在不大的厨房里忙活,进进出出的样子恍然有点像回到鼓楼西大街的出租屋,但又不一样了,这是新的 Backspace 和他们不断在刷新的生活。他们身处迎面而来的风里,一步步顶着风往前走,也不会忘了及时行乐:生活是杯好酒,得好喝易上头。
* 注:文章封面图来源于 @bbf3